“青艺”60年
作者:孟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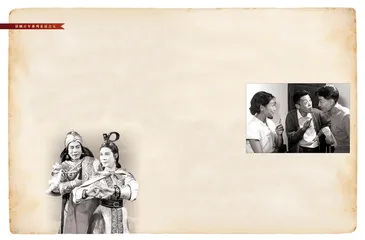
( 吴雪(左)与郑振瑶合作的《文成公主》 演员们正在排练《抓壮丁》 )
“青艺”在新中国戏剧界最为悠久,1941年它还叫延安青艺,由苏区和部队的文艺团体合并而成。其间多次变动,1949年跟随“四野”进关,同年4月16日正式成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以下简称青艺),归中共中央青年部管辖,比共和国的成立时间还早。第一任院长廖承志,身兼多职,尽管也经常到剧院来看看,实际事务还是由副院长吴雪处理。吴雪是第二任院长,17年来一直掌控着青艺的工作。
青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国家级剧院,提出的口号是把国统区艺术家团结在一起。它有政策上的巨大优势,可以在全国任意挑选演员,赵丹、白杨、张瑞芳、金山、顾而已……这些大明星过去都在私营剧团,在“欢迎参加青艺”的口号下,像流沙一样聚向北京,当然,很快也如流沙四散。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那天,院长廖承志对大家说:“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吴雪与金山,这两位副院长,在青艺人口中是“两股力量”,“革命老骨头”与“上海帮”的较量。赵丹等人回了上海,金山一直留下来坚持“斗争”。金山是杜月笙的义子,后人称他为“话剧皇帝”。林克欢说:实际上被媒体白纸黑字称为“话剧皇帝”的只有石挥。金山的辉煌时代也是中国电影、话剧的黄金岁月,整体水平较高,“话剧皇帝”也是基于金山后来植根于舞台,而其他人主要精力在电影上。但是“皇帝”的称号不是白给的,从未接受过正规训练的金山无法用理论描述他的灵气,一片黑蓝色列宁装中,他梳着大背头、身材魁梧,异常潇洒,一群人中你先注意到的一定是他,这就是好演员。“施洋大律师”那段独白至今被奉为台词经典。他在“文革”后给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上课,举手投足的气派依旧令众人倾倒。
出身地主家庭的吴雪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干部,这类干部在文艺系统内“根红苗正”。给林克欢印象极深的是,团级以上干部可以配备勤务兵,吴雪还保留着军职,他的勤务兵每天“啪啪啪”地跑进跑出,带着手枪,给他端水。建院初期作为院长,吴雪有一辆小轿车,其他几个副院长共用另一辆,这可是上世纪50年代,要知道直到60年代,全北京才有2000多辆。当然金山夫妇也有特权,尽管金山在抗美援朝时犯过“生活错误”,被开除党籍、撤职,可孙维世还是总导演、副院长,他们住在一个独院里。
吴雪是“土八路”,却不是专业的门外汉。四川方言喜剧《抓壮丁》就是他自编、自导、自演,他是“李老双”——滑稽的丑角。他的表演活灵活现,因为他演的就是他父亲。这部戏后来被导演沈剡搬上银幕,久映不衰。吴雪和金山都不是表演的正统派,全靠自学。当时全中国唯有孙维世接受过斯坦尼体系的正规学习,她在莫斯科经过表演系、导演系训练,等于是当时的博士。刚解放时,青艺的学员大多从东北招收,是土八路队伍。孙维世来后,排的第一出戏是《保尔·柯察金》,金山和他当时的妻子张瑞芳分饰保尔与冬妮娅。29岁的孙维世教39岁的金山演戏,她不让演员做案头,而是让他们先看原著、对台词、加形体、代入角色。孙维世和金山夫妇住上下楼,金山总去找她说戏。在张瑞芳的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文字:“他们一起讨论剧本,一起散步,从宿舍到剧院,常常是他们俩同进同出,我反倒一个人独来独往。”
结局是张瑞芳离开青艺,金、孙联姻。孙维世给青艺带来了传诵至今的作品,《保尔·柯察金》中的歌词也是她填的:“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在那静静的小河旁,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这是我们心爱的故乡。”她带来了全新的艺术实践,从舞台布景到表演,都令观众耳目一新,台上甚至出现了保尔与冬妮娅接吻的场面,新奇震撼。之后,她又执导了《万尼亚舅舅》、《钦差大臣》、《叶尔绍夫兄弟》等。1956年她和欧阳予倩参与组建了中央实验话剧院。
在青艺,孙维世的艺术成就与她糟糕的人际关系同时并存。她排戏时并不骂人,不像吴雪,可是她有“红色格格”的头衔,说一不二。用林克欢的话说是“她有高雅的派头”,不好听的形容词就是“没有亲和力、傲慢”。她基本上只和她常用的演员交往,比如后来演过《篱笆、女人和狗》的演员田成仁,她的班底大多是中戏毕业,学过一点斯坦尼,另一部分来自上海人艺的学员馆。在文献记载里,孙维世被形容为“绝世美人”,但在青艺人的印象里,孙维世身材高大、五官醒目,却并非绝代佳人。
相形之下,金山更会为人处世,他和艺术骨干关系不佳,经常和吴雪拍桌子吵架,又因为没有实权,“怎么闹都闹不过吴雪”。不过他和工人倒是打成一片,出手大方。金山的月工资有200多元,是普通员工的好几倍,他常常带两条烟给工人师傅们抽,而且必定是处级干部才能抽上的“前门”。“文革”开始后,剧院成立了大联合5人小组,由小年轻+工人组成,林克欢就是管剧院的专案组成员之一,吴雪由于群众关系不好,职工们把已经上调文化部艺术局当局长的他揪了回来,最先批斗。
经历过延安整风的吴雪经验丰富,又很有喜剧天分,“文革”中,“他特乖地拿张凳子站上去,抖出一张报纸,上面早已写好三个大字:‘走资派’!”剧院毕竟是文化人,不会动手打人,只知道按脑袋,让他老实交代。吴雪总是把自己的问题说得比天还大,让群众瞠目结舌,不敢接茬。有一次群众怒吼:“你要把青艺领到哪里去?”吴雪答:“领到美国去。”“领到美国做什么?”吴雪说:“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金山哪见过这阵势,他的态度比吴雪强硬,对“生活腐化、叛徒、走资派”这些帽子一概不认。剧院由军宣队接管,一些中级军官组织批斗,“三高三名”(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名演员、名导演、名作家)统统被关到车库,半天劳动,半天写交代材料,还要扫地、刷碗。不久,金山被江青点名,涉及30年代的“叛徒案”,作为中央专案秘密审查。无论他或是在剧院的吴雪、舒强,都没有受太大的罪。相反,几乎没在剧院挨过斗的孙维世在1967年被抓进北京市看守所,全剧院只有保卫处长看到过她的尸体。
1966年初,青艺和实验话剧院第一次合并为“中国话剧团”,这次成立气氛很紧张,文艺界正在批判“四条汉子”。“文革”期间,导演都被打倒,演员自己排点儿活报剧、相声、快板、山东快书,偶尔也有《张思德》这样不需要导演的剧目。1970年,全剧院拉到高碑店农场种水稻。50年代曾经有文化列车,特制车厢的一边打开就是活动舞台,四处下工地演出,这时也乱套了。
“文革”平反后,吴雪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挂名青艺院长,金山只好去“中戏”做院长,他导了话剧《于无声处》,当时反响强烈,今天看,道德批判黑白分明,人物极端脸谱化。例如他让一个反派从圆桌的洞里伸出脑袋,寓意乌龟,这是原剧本没有的,和用“三公一母”的螃蟹比喻“四人帮”的手法差不多。青艺恢复秩序后第一部有影响的戏是《枫叶红了的时候》,而后是《转折》。《转折》的价值在于发现了王铁成的骨型酷似周恩来,这也是周恩来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舞台上。林克欢对王铁成说:“此后没人记住这戏的导演是谁,却一定记得你。”因为每次演出时,王铁成一出场,全体观众起立。
1982年,青艺考虑到和世界隔绝了这么久,知道欧美的动向,对港、台地区却一无所知。林克欢在香港大学碰到了一位台湾教授,得到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有台湾剧作家姚一苇的剧本《红鼻子》,于是青艺演出了这台剧目,引起海外强烈反响,以为中央对台政策有了新动向,其实完全是无意之举。
1987年,剧院实行了艺术总监制;1996年,又从党委负责制改为院长负责制。孙维世从苏联带来的表演体系和剧目使青艺的特色定在“外国戏”,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但是差额拨款又让剧院难以为继。为了引进明星,青艺和实验话剧院都大量吸收过北漂演员,给他们提供编制,条件是一年在剧院排练演出4个月。90年代电视剧价码已经提高,演员们不愿意在剧院浪费时间,文化部的规定又不允许裁人,演员们向剧院交些钱换取自由。青艺的演员姜文在和领导闹过几场后,双方在报上互相攻击,林克欢劝他选择离开。
2001年,青艺和实验话剧院再次合并。林克欢是合并的坚决反对者,可惜大势已去,他提出的条件是:不要裁员。果真没有裁,结果是国家话剧院带着400多人的臃肿机构艰难前行。 林克孙维世张瑞芳青艺剧院戏剧60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