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监局:司长的权力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蔡崇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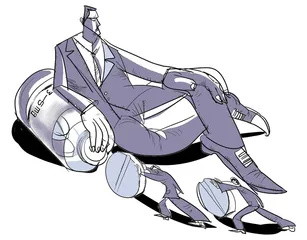
注册司司长:越来越绝对的权力
“以前我们的工作完全是规定框好的,就一个复查的工作流程,没有太多空间,谈不上能有什么巨大的开拓,就求个本职工作做好。”2月17日下午,目前在香港任职的、曹文庄前任,国家药监局注册司前司长张世臣在电话里对记者这么说。根据他的介绍,“1985年开始实施的《药品管理法》规定,新药审批在国家一级,仿制药品及保健药品的审批在省一级”。而当时的仿制药品未列入新药大都在地方审批,中国自己研发的新药数目从来就较少,所以国家药监局注册司在张世臣任职时候,权力确实仅在于一年批准100个项目左右的新药的复核工作。
注册司司长的职务管辖范围和权力在曹文庄任内有了一定改变。中国医药工业总公司原总工程师、中国化学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俞观文在医药系统工作近50年,他给记者分析了整个过程:“1996年4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对已经批准生产的药品进行清理整顿,在清理整顿期间暂停批准仿制已有批准文号的药品及保健药品。所以,药品审评从那时候开始已经是国家一级审评。”
“不过这个通知在实施时候遇到困难,当时之所以推出这个规定有个目的,此前由于仿制药品及保健药品的审批在省一级,各省都有较多药厂,甚至有些地方大部分县都有,有时候一个地方经济支柱就来自药厂,而药厂利润来自药品销售,所以出现一种受欢迎的药物,各药厂就齐拥而上。这些药绝大部分是仿制药,仿制药的审批权如果在地方,各省会因照顾地方经济大开绿灯。据2000年对全国进行调查,有15个省(区、市)在国办发14号文件下发后仍批准了710个药品。”俞观文说,“这就造成药品低水平重复生产,同品种竞相仿制,徘徊在低水平地抢时间和低价格上,获利模式是那种薄利低水平重复,根本没有药厂有精力和能力进行新药研发,长期下去中国药品根本上不去。”
改变是在2002年,喜欢写文章的曹文庄曾在2002年的总结中提到,“为了严格药品审批,确保人民用药安全有效,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29、31、33、39条明确了新药、仿制药品、进口药品都必须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取消了地方批药的权力”。而曹文庄也正是在这一年正式接任药监局注册司司长。

俞观文认为,之所以在这个改革时刻选择曹文庄,在于“当时大家普遍看好曹文庄。曹文庄1984年从黑龙江省商学院中药系毕业后进中国药学会工作,因为能写文章,做事认真一直受关注,1988年他调入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工作,任秘书。从一个副局长秘书到接任局长的秘书,后来任办公室主任、人事劳动司司长。1998年成立药监局后,他任药监局人事司司长、办公室主任,2002年任命他为注册司司长。应当说当时药监局对他有充分期望”。事实上,药监局在1998年从医药局到独立的部级单位改造重组后,包括对药品的生产、经营、流通等管辖权已经分割出去,最有价值的权力就在新药注册。“而这也是药监局作为监督部门一个起监督作用的重要手段。”俞观文说。
“当时曹文庄的任务应该很明确,就是通过对药品注册审批的管理,改变中国药品低水平恶性竞争,提高药厂科研能力,促进中国药业真正发展。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药品审批权集中上交到国家药监局注册司的同时,也紧接着出台的《药品管理法实施办法》,对新药的定义和审批流程重新梳理。这次梳理可以说也是为注册司更有力量去掌握局势。”俞观文说。

曹文庄在2003年6月曾经对《医药经济报》详细分析过按新规定国家药监督局注册司集中的权力是:“1.生产新药或者已有国家标准的药品,须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并发给批准文号,药品生产企业在取得药品批准文号后,方可生产该药品。2.研制新药,必须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定,如实报送研制方法、质量指标、药理及毒理试验结果等有关资料和样品,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后,方可进行临床试验。完成临床试验并通过审批的新药,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发给新药证书。3.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药学、医学和其他技术人员,对新药进行审评。”
“也就是说,一方面新药从准备申请审批到审批生产的全过程都要经过国家药监局注册司的批准,每个环节的标准都交给注册司。另一方面,即使是已经批准过的药,也要全部重新由国家药监局注册司审核,周期是5年一次,注册司可以在重新审核时候,重新掂量这种药是否有继续生产的必要。注册司的权力于是得到强化,比如说,福建、江苏生产同一类药品主要成分是一样的,但他们以前生产的标准由于是地方审批是不一样的,要定福建的标准那江苏的许多厂就要改造,这需要花费成本,需要改造时间,需要重新审核,而福建的厂就可以在竞争对手缺席的情况下扩大经营。再比如说,同一种药福建和江苏同时有厂提出申请,越早审批通过越早抢占市场,在注册司的工作流程下,谁能先审批通过谁就抢了先机。可以这么说,药监局强化注册司的权力是可以理解的,1998年改组后,药监局最大的权力本来就只在于新药注册,国家这样的调整就是寄希望通过新药注册监管医药行业,促使这个行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新药注册:药厂压力的寻租出口
与此同时,药厂的压力和不良竞争却越演越烈。“中国医药有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药厂太多,太小,庞大的美国市场上只有约200家流通企业,大的供应商不到10家;而中国有17000家流通企业、6700家生产企业。”中国医药企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专家委主任、北京康派特医药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磊对记者说。
“药厂多造成的问题在于,中小药厂为了求生存,会在低水平的药品上竞争激烈。举个数据,跨国制药公司科研开发费占销售额的15%~20%,销售利润率在20%左右;而我国医药企业因为科研开发费仅为销售额的1%,销售利润率只有7%~8%。而且中国所有药厂的产值加起来还不如美国一家大药厂,根本就没有办法竞争。”俞观文说。
2000年开始,国家药监局开始推行GMP。“所谓GMP说得通俗些,就是在药厂的规模和生产能力上提高门槛,GMP认证花费高昂,单个车间通过认证就需要800万~1500万的资本投入。这个举措当时想的是一石二鸟,关掉大量中小药厂,让大药厂更能赢利,有足够的资金投入科研、升级,另一个是保障药品安全。”李磊分析说。
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药厂绝不是通过提高门槛能关掉的。“我国的药厂分布有个背景,从1959年开始,按计划经济那种平均的原则,开始在各省分别建立作用类似的化学制药工业。1979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开始对药品需求增多,许多省又开始鼓励兴办药厂,而且许多药厂是地方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的,是地方经济命脉,关掉一个药厂意味着背后一个地方经济的亏损。”俞观文说
在那种背景下,很多地方选择的是,由政府出面向银行贷款让地方的药企得以改造。“所以最终推行GMP的结果是,全国7000多家药厂淘汰了将近1500家,可通过GMP认证之后的40%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但是GMP改造后由于对生产规模的强制要求,每家药厂生产能力扩大了3倍,产生的过剩产能达到2000多个亿。”李磊对记者说,“为顺利过关,很多企业是不惜血本,勒紧腰带凑集资金进行GMP改造。全国医药企业为通过GMP花费了1400亿元,大部分药企背上了巨额银行贷款,比如三九医药公司就向银行借有数百亿。”李磊表示,成倍的产能扩张、巨大的财务压力都需要扩大产品营销缓解,而在国内需求稳定和出口有限的情况下,市场原本出现的低效、低价竞争更加激烈。
“与此同时,从1997年起至2003年底,国家14次大幅度降低药品价格,工业利润不断削弱;而医用原料涨价和‘治超’导致的运输成本激增等各方面因素,也使得不少通过GMP认证的企业在市场上感觉步履维艰。而这时候,国家发改委为贯彻减轻群众负担对一些常用药给予硬性定价,逼得许多企业开始寻找出路。”李磊说。
当时很多药企不约而同打起了新药的主意。因为一方面国家为了鼓励新药研发,新药价格国家没有控制可以自由定价;另一方面新药因为生产的厂家少可能更好销售。“这本来是药监局所期望达到的效果,可在当时低水平竞争和产业底子本来落后情况下,中国药厂根本没有足够实力和国外药企在真正的新药上直接竞争。”而且以前的政策也让企业有了钻空子的机会,在审批权还没有统一上交到国家前,药监局为加大管理力度扩大自己审批监督范围,规定国内上市的药品定义为新药外,改变给药途径和增加适应症的这类严格意义上的仿制药按新药管理,到了2002年修改规定后这一条还是被保留了下来,“这给了仿制药可以当作新药审批的空间”。
时任药监局局长的郑筱萸在出席全国药品注册工作座谈会时曾指出过这种现象:“不具备研制新药能力的企业转向仿制寻找出路,而拟仿制申请要求简单,不需做技术工作,有的单位一次报来十几甚至二十几个拟仿制申请表,他们抱着批下来哪个做哪个的心理。”还有相当企业试图通过加个成分,注册个新药品,然后就转身变成定价高出十倍甚至百倍的新药牟利。比如人人皆知的阿司匹林,每片仅0.03元,不少医院已开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高价药“巴米尔”,每10片6.3元,其成分也就是单一的阿司匹林,而价格一下子涨了20倍。
这样几乎所有权力都集中到负责新药审批的注册司上。而新药审批在统一到注册司后大概有三个主要流程,一报给注册司底下的审评中心。审评中心负责审评材料提交的格式和方式,然后上交给注册司,注册司再从自己的专家团里组织相关专家论证,是否有批新药的必要,以及工艺上是否达到安全。如果不通过就打回,通过了就重新提交到注册司,注册司在专家研究的基础上审批是进入一级临床、二级临床、三级临床或者可以直接生产。如果要进入一级临床,就到各个地方药监局指定临床基地,通过了一级再返回到下一级,只有全部通过然后才能生产。
“由于临床基地大部分是在地方,所以药企和他们的关系一般比较好,最关键的把握还在于注册司组织的专家团以及它的审批意见,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新药也是同类竞争,你通不通过,以及以怎样的速度通过就关系重大了。比如同一个产品,甲是直接进入生产,乙是进入一级临床,等乙最终可以生产的时候,甲早就占据市场了。”李磊对记者分析说。而事实上即使按规定,新药审批也确实可以给企业方便的弹性,“一是暂时手续不全,争取提前通过,之后再一一补齐;二是产品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时,就把许多本应该依照不同时间段按部就班的手续全部办妥,待临床试验刚一通过,产品就能够立即推向市场。这中间,就给了一些单位运作的可能。”
对这种现象,当时郑筱萸还特别提出工作指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要继续下大力气采取措施予以控制。”而这就是刚上任的曹文庄面对的状况。
“标准”背后的隐晦空间
从2002年到2003年发生了什么?据中医药在线2004年2月20日的数据,200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7000多份,全年共审批新药注册申请6806份,比上年增加128.5%。其中,批准新药临床研究申请4222份,比上年增加346.3%;批准生产申请1351份,比上年增加66.4%。而这些申请大部分是2003年下半年通过的。
新药注册司失守的原因,按俞观文的分析是,“当时国家正掀起法治风,落实到药监局就是要以法治药。我记得当时郑筱萸局长在贯彻中央精神的时候解释过,所谓以法治药就是国家规定的就要严格执行,国家没规定的就要严格不执行”。而恰恰是这个精神抽去了新药注册的“挡箭牌”。
“有一个令人窘迫的事实,药监局审批新药依据的精神其实是没有写入法律的。从一开始的医药管理局到药监局,当时新药审批有个默认的规矩,就是一般同一种新药批准不超过3家。当时随着药厂的压力增加,时常有各地领导到处运作。等到了2003年下半年,大量药厂开始反弹。”俞观文说。所以就出现了一种情况,本来各省药厂没有具体的方向分工,生产的药品大部分类似,以前可以控制只给3家,到那时候,你要是批了一个就上百家甚至千家企业全部要批。
“失守的同时也造成了另一次同质竞争,结果最终还是在营销上竞争,而且这些药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强制定价,所以就出现了各种用回扣、折扣甚至不法的方式推销。在这种情况下,注册司对药厂的存亡兴衰也越加显得举足轻重,因为同质化,同类产品你让谁先过,谁就先赢利,后面等一大批都过了一起竞争的时候,营销成本肯定要提高,销售肯定要下降。”俞观文说。
“到了后来药企竞争开始非理性化,许多小药厂干脆砸锅卖铁就为了搞个新药,这样的生死关口,一个新药及审批的快速与否,关系到的是一个厂几千职工一个地方向银行的上百万贷款和这个地方靠药厂的纳税和经济拉动,它们拿出几万甚至几十万审批就不需要考虑了。”张光在哈尔滨一家药企新药注册部门工作,他告诉记者,“我们厂后来干脆请一个审批公司代理,在北京北海附近,有大批代理审批的人,我们用超过十万元的价格和他们签了一个协议,协议中写到,乙方(代理方)一定要保证新药审批通过,并且最好是尽快通过。有的甚至规定具体时间,按时间收费。”■
郝和平案:药监局官员落马的现实轨迹
2005年7月8日,在曹文庄被调查之前,药监局另一重要部门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经济问题被刑拘,根据俞观文的说法,“郝和平可以说是在利益关系下卷进去的一个典型”。
关于郝和平落马的原因,此前媒体披露的说法是“收受了跨国公司贿赂”,多个医药公司将扯进郝和平一案。
按照中国目前的相关规定,一类医械注册审批权在当地药监部门,二类在省级药监部门,三类医疗器械、跨国公司医疗器械注册审批权都在郝和平主管的医疗器械司。
作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最引发争议的在于起草力推《翻新再用医疗器械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1996年7月,原国家计委、卫生部就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二手医疗器械进口和使用,而这个《规定》则计划要全面开禁二手医疗器械市场。
此举招来本土厂商的集体反对。国内医疗器械市场总体份额中,国外企业大概占80%,国内企业占有20%。其中高端产品国外企业有着95%的市场占有率,中低端产品中外企业则各占50%。根据此前媒体报道,2005年6月19日,全国41家医疗器械单位联名上书称,一旦《规定》实施,因价格上存在差距,本土厂商连中低端市场现有格局也无法保住。一台国产中档CT机,终端用户价约在200万至250万元,而国内厂商卖国产货最高毛利大概30%,但是一台同类型国外品牌的二手CT机价格仅100万元。其利润最高可达10倍。有报道直接指出,郝在《规定》的制定过程存在违规操作。
郝和平还在新产品注册审批的控制上有很大争议。按规定,新的医疗器械上市必须要经药监部门审批,时间掌握在器械司上。一种新产品从接受企业申请到最终审核批准上市长的可以半年,短的就个把月。而国外热门医疗器械产品在中国每月销售额一般就可以达到2亿至3亿元。据《第一财经日报》引用一家医疗企业工作人员的说法:“申报医疗器械产品很多都通过代理公司。自己申报,审批资料被反复驳回的次数很多,而且大多时候过不了关。”“这些公司其中绝大部分是国家有关部门的人出来开办的,与审批部门有很硬的关系。”“企业自己申报,假如关系不过硬,20万元都打不住,而且同样材料,不同的人处理,被驳回的次数也很不一样。不过假如关系过硬,10万元也有可能。”而进口产品申报,较国内产品整个流程费用总额更高,弹性空间更大,“一般一个进口的新药或器械要花去10万美元报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