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怀念王选?
作者:陈赛(文 / 陈赛 尚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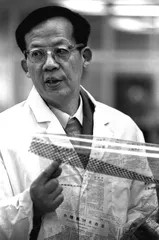 ( 1990年在工作室工作的王选
)
( 1990年在工作室工作的王选
)
洞察力怎么培养?
“一个在第一线上拼命干活,一个是大量看文献。”在一次接受央视“大家”采访时,王选沉思良久,说出答案。
作为他的学生,汤帜非常清楚导师的研究习惯——在任何一个项目开始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是了解清楚国外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动向。1987年,他初入师门,王选给他们上的第一门课“现代软件设计方法”是全英文授课,因为他认为搞计算机必须随时跟踪国外前沿动态,必须具备极强的英文阅读能力。“他本人从60年代开始坚持收听BBC对远东的英语广播,每天半小时,天天如此。那时候因为收听‘敌台’,‘文革’时候吃了不少苦头。”
中关村一直流行着一句话:“技术研发是青春饭,到30岁就做不动了。”
作为中关村先驱的王选却是在38岁那年才有机会投入他一生最疯狂的事业——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发,并在研发一线一直工作了没有一个休息日的18年。56岁那年,他自觉创作高峰已过,对于技术前沿的洞察力和敏感度已无法跟上年轻人,便坚决退出了研发一线,转而全力扶持年轻人。
 ( 2006年2月16日,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来到北京大学吊唁王选
)
( 2006年2月16日,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来到北京大学吊唁王选
)
王选一直秉持一个观点,“让年轻人自由选题,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才能激发创作的欲望”。有一年,他到施乐公司的研发中心参观,看到一间供讨论用的房间,没有沙发和椅子,地上铺着像席梦思一样的柔软材料,人坐下去就会随之变形,象征一种不拘一格的自由探讨精神。他很羡慕这样自由自在的开发环境,一直希望在方正研究院也创造一个充满想象力和激发自由创意的乐土。但是,这个心愿一直没有实现。“有一天,等公司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有更超前的研究部门成立的时候,也许能够实现他的这个心愿。”他的继任者说。
王选曾经多次在文中提到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认为此人聪明绝顶,虽然从未具体设计过一件产品,对技术和设计却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直觉,能预见未来市场的潮流和需求。他自认在商业天才方面不及乔布斯,而且他生平最遗憾就是未能给方正培养出具有技术背景的管理人才。但是多年来,他所说的“我们研究的技术必须是有用的,能够投入市场的”,在方正已经成为共识。

张旋龙回忆,王选最钦佩的企业家其实是英特尔的创始人安迪·葛洛夫,不仅因为他将一个企业做到这么大这么好,而且这么长时间坚持做一件事情。王选本人何尝不是一个极度坚持的人?他的口头禅是“坚持坚持再坚持”,这是丘吉尔在二战的时候说的。方正在日本市场受到挫折时,他在员工大会上讲,“坚持坚持再坚持”,他很有信心,只要坚持,方正一定可以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公司。
以王选的地位和威望,想来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但凡是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其实是最最随和的一个人。一位采访过他的记者说,王选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第一次见面就将家中电话号码告知的名人。他的学生说,“王老师是这样一个人,走在街上,绝对不会有人把他认出来,他太普通了”。
10年前,58岁的王选当选中国两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荣誉达到顶点,他却一直对名利看得很淡。他对一位采访他的记者说,“我年轻的时候搞科研,因为是无名小卒,说话没有分量,也拿不到经费。现在我老了,什么都不需要了,倒是给我这个荣誉那个荣誉,有什么用呢?年轻人搞科研,最需要的是经费”。即使今天,这样的现象恐怕仍没有多大改善。
王选去世后,很多人都感慨,“再也不会有第二个王选”。但是,王选在遗嘱里却说,“方正一定要有人能够超越王选”。■
“认识王选,是我的福气”
——专访方正集团方正控股主席张旋龙
“与他相交20年,我们相处一直很开心。他得病之后,我们心中知道他很辛苦,但总是希望他一直在那里。他不在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这两天,我一直睡不着觉,发愣。很想去灵堂,又不敢去。我已经去了两次。”
张旋龙在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面色疲惫,眼中尽是伤感。他目前的身份是方正控股的主席,与王选的关系极为特殊,曾经是王选打拼海外市场的最佳搭档,也是他退位后的第一任接班人。“就公司而言,他是我的老板,但我在心中一直将他看成父亲、师长一样的人物,更多时候,我们是战友、哥们儿。”
1985年,张旋龙去日本参加世博会,美国馆、日本馆里都是机器人、微电子,中国馆里都是些剪纸陶瓷,因为身边有日企职员陪同,他觉得“很没面子”,直到他看到一个有机玻璃箱里装着的汉字照排系统,心中大喜,“这才是中国的高科技啊”。第二年,他专程回大陆,通过当时的北大校长找到王选。他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王选时的样子:穿着短裤,一双貌似拖鞋的凉鞋,短袖白衬衣,土土的,对他这个香港来的油嘴滑舌的生意人非常冷淡。“我也觉得这个老头呆气得很,与他想象中的‘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相差甚远。”谈到此处,张旋龙大概想起了往事种种,长叹一声。
记者不禁想起他在一篇悼念文章里写的,“认识王选,是我的福气”。
三联生活周刊:王老师的去世,您最遗憾的是什么?
张旋龙:我最遗憾的是,他还没看到方正在日本市场有更大的作为之前就离开了。现在日本已经有300多家报纸使用我们的产品,但总体所占的比例不过3%~5%。他病了以后,我不大敢去打扰他,但他还是经常让我过去,问一些日本方正的事情。这也是他最后几年跟我谈论最多的话题。
三联生活周刊:您最初知道他的病情是什么时候?
张旋龙:2000年,我们刚从马来西亚回来,一切都好好的,有说有笑,谁知回国后检查身体,竟发现是肺癌,而且很严重。我听到后整个人都呆了,在电话里哭得不成样子,连话都说不出来,反倒是他一直安慰我。
三联生活周刊:王老师一向身体病弱,他有没有跟您谈起过死亡这个话题?
张旋龙:他说他不怕,2000年查出肺癌之后,他其实已经写好了遗嘱。他觉得他这辈子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自己,而且他真的没什么选择,人总要一死的。他越这么说,我越难过,蛮可怜的。我母亲就是癌症去世,死得很痛苦。他进行了很多次化疗,都很坚强,问他身体怎么样,总说没问题没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公事,你们还会谈什么?
张旋龙:他其实是个很风趣的人,知识面极广,什么话题都能谈。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个学者,大家都很敬重他,在方正,几乎没人敢跟他开玩笑,除了我。也可能是我的性格感染了他。前阵子,我女儿画画得到一等奖,参加联合国的一次画展,我就打电话向他炫耀,他笑我说,“这个遗传不是你的吧”。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说说,您知道的王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旋龙: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看人看事物的眼光很锐利。他身为学者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严谨,每说一句话都很慎重。在没看清楚之前,绝不表态;而一旦表态,必然是极肯定的。我常问,王老师,你这样累不累啊。他说,没办法,习惯了。所以,我们是很害怕给他写东西的,特别小心,怕挨骂。
他一直有一个奇怪的理论,“能吃才能干”。所以,他的饭量极大,而且吃饭时从不看人,只顾自己低头吃,吃完后就说,“好了,我先走了”。他也不喝酒,以前有人敬酒,他总是一只手挡在前面,一口回绝,“我不会喝”。后来能喝一点了,比如一小杯花雕,或者一杯红酒。说起来,喝酒我是他的老师。
他是非常节省的人,有一次,我陪他去美国见一个客户,他要住一个普通的酒店。我说,“王老师,您在美国见大客户,住这种地方,没戏的”。后来,我们定了五星级酒店,那个项目谈得很成功,他就感慨说:“还是你对,我们现在可以搬出去了吗?”
他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衣食住行干净简便即可。1999年的时候,我去他家,地面还都是泡沫胶的,我们在他家都要穿大衣的。生病之后,才搬到好一点的地方。他常说,一个人要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必然要失掉不少常人能够享受的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他开发激光照排系统的那18年里,一天也没有休息,没有寒暑假,没有春节,也没有星期天,才换来这样的成果,但他自己觉得很值得。
他很喜欢植物,喜欢绿色。他以前住在北大承泽园的时候,门前有一块小绿地,他很喜欢,常常谈起。其实,那只是小得可怜的一块绿地,我家后面是座山呢。后来他来香港,看到我家和后面那座山,说,“你家的确比较好”。他并不是喜欢豪华,只是喜欢绿色。
他也喜欢小动物,去年,他家附近有一只流浪猫与他感情很好,他每天都会去看那只流浪猫,后来那只猫不见了,他伤心了好一阵子。
他喜欢打太极拳,每天都要打半小时的太极拳。有一次,我陪他去日本见客户,从一家公司到一家公司,一路行程很紧。有一家公司楼下有片小树林,刚好还有点空闲时间,他就会站在那里打一会儿太极拳。
三联生活周刊:在外界看来,王选一直是一个温和的好人,您见过他发怒的时候吗?
张旋龙:很少发怒,但他是一个藏不住喜怒的人。1998年,为了尽快打入日本市场,方正很想招聘一批开发日文的员工,但一直没有招到。他很不高兴,跑去质问为什么,人事部告知说,招一个人花要5万块钱,专门解决北京户口问题。他当时气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说我现在就拿钱出来给他们,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激动。
三联生活周刊:您见过的,他最开心或者最兴奋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张旋龙:我拿到台湾《中央日报》的单子那次,他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一直说,“我要敬你酒”。在生活里,他很喜欢爬山,来香港的时候,我常常陪他绕着太平山走,他就很兴奋,话也多起来。
三联生活周刊:您最佩服王选什么?
张旋龙:他的眼光是我最佩服的。70年代他就开始谈自主创新的,自己研发,这些都是国内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提倡的。我们这些早期的IT业人都把王选看作民族英雄,那个时代,电视机、收音机的科技全都是进口的,只有印刷这一块的科技是自己的。他一直对我说,一定要靠自己,靠别人是没有用的。■
忘却的三总工时代
当王选突然辞世,我们记忆中的他只有了方正激光汉字照排技术和当代毕升的颂称。而在Google直接的搜索中,王选这个名字更瞩目的是对日军侵华细菌战诉讼的女王选。尽管原本就很低调的王选在2000年因病休养,实际上大家对于方正的王选并没有忘却,当2002年《南方周末》把年度人物给了对日军侵华细菌战诉讼的女王选时,并不了解她的人仍要疑问一下,哪个王选?
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著名企业,这是1993年前后谈论渐渐兴起的中关村故事时,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段子。王选、倪光南、王缉志,三位来自大学或者科学研究所体系的技术派总工,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依靠汉字激光照排、汉卡、打字机三项技术,成就了方正、联想、四通最初的崛起。而张玉峰找到王选、柳传志找到倪光南、万润南找到王缉志,几乎是所有描述中关村发展史的传记中都不得不提及的重要内容。
当还在《计算机世界》任职的记者刘韧出版《中关村问题》,蒋胜蓝因为撰写《联想与计算所的“婚变”》而引来联想压力的时候,20世纪最后几年对于中国信息产业界的探讨焦点,依旧关注于传统研究所体制下技术到底如何与市场相结合,技术派的总工如何推动技术企业的商业发展。这几乎成了90年代末互联网技术浪潮席卷之前,中关村如何变成硅谷的大辩论中最大的导火索性话题。当倪光南1996年被柳传志从联想总工位子上解职,王缉志很早就淡出四通一线,王选作为三位科学家总工之一,可以说赢得了最平滑的个人事业转型,推动方正成功上市,并且将一线管理让位给年轻一代,自己依旧能够关注在技术开发领域。而2000年后王选患病时,与他同一个时代的倪光南更近似中国信息界的开源推广者和布道士,而王缉志则在尝试推动电力上网项目之后,依旧穿着标志性的吊带裤过自己的养老生活。
“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不是科学家的企业”,这是1999年对于中关村技术创业元老频繁去职时最流行的评论,尽管包括当时刚刚兴起的CCTV2“对话”节目都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资本与知识、技术与市场的冲突,但流行在中关村文化中的“贸、工、技”思路,还是深深左右了中国信息产业的历史。而王选恰恰依靠早年牵头主持开发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令方正始终不敢放弃技术研发的要点。
王选曾经在1999年3月出版过一本《王选谈信息产业》,这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尽管定价只有16元,却字字真切地道出了第一代中关村技术先驱的看法。放眼国内外华人技术派领袖,只有现任Google中国统领的李开富还是一个热衷舞文弄墨的技术分子,王选恰恰前辈般一直保持自己北京大学很多年助教生涯的那种人文气息。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2005年6月12日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改变我生命的三个故事》中曾经透露,之所以苹果电脑始终保持优雅的字体和排版能力,很大程度得益于乔布斯在里德大学退学后旁听的书法美术课。而王选的开发汉字激光排版技术,也充满这种学习主义和长久的人文气息,就如同1998年开始任王选助理的丛中笑在传记《王选的世界》中引用的王选说法:“1988年后的几年间,我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看报栏,看里面的报纸哪些是铅排的,哪些是我们的激光照排系统排的。到1991年,我在上海交大看到交大的校报都是用我们的技术排的版,这以后我就不看报栏了——我知道不用看,用的都是我们的技术。这个过程真是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享受。法国作家莫泊桑有一个座右铭:一个献身于科学的人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最幸运的人,面对人们对知识带来财富这条增值方式的认可,技术派越来越赢得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关注。王选所代表的三位总工时代,更多依赖于通过解决汉字的计算机化门槛,而得到了最初的成功。在他们之后是金山的求伯君、早年编写UCDOS的鲍岳桥、杀毒软件走天下的王江民等一大批没有学院背景的民间技术派,软件编程成为这些第二代中关村人的技术法宝。而互联网在2000年之后的技术崛起,给那些并没有学院背景,也不需要混迹中关村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百度搜索蹿红的李彦宏,网易电子邮箱起家的丁磊,都不再需要挂靠中关村为背景,风险投资机制的引入和海外上市的模式,让第三代抓住技术机会的“总工”们可以不再戴中关村的帽子。而这距离1979年8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次披露王选成功研发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消息,过去了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