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延光:“那个总理成为旗帜和符号的年代”
作者:王鸿谅(文 / 王鸿谅)

1976年的选择
1976年1月9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被公布。贺延光在骑车的路上,听到街上的大喇叭广播里播发了这则消息,然后是满街的哀乐,“当时就掉眼泪了”,“就像是一种本能反应”。他甚至清楚记得一个细节,广播里关于总理的那些评价,只提到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并没有说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个时代人们心中最崇高的评价。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贺延光说,“这种敏感并不是人们天生的,是运动造成的”。
隔了30年再来看,贺延光说,“一方面是对于周总理的情感,一方面是对这个国家前途的忧虑”。
这种情绪爆发的临界点终于在4月1日到来。
三个月的时间里,贺延光的感觉是,他和周围许多人一样,更加敏感地捕捉到了更多的细节,并有了愤怒的猜测——江青等人的攻击目标开始转向了周总理,被压制的悼念和有意识的误导与歪曲,终于“把大家心里的火弄起来了”。那时候贺延光25岁,是原北京市崇文区工业局最年轻的党委委员,身兼崇文区化纤厂革委会副主任、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多重职务,是很被看好的“三结合”重点培养对象。但是贺延光选择了一种最激烈的表达,成了化纤厂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中那个“挑头”人。贺延光说,对他而言,这种选择是性格的必然。他领着人上街买花和松枝,扎好花圈,4月1日上午与80多人一起到天安门广场,那时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已经布满了花圈,贺延光和同事们抬着花圈,经过半个多小时,才靠近纪念碑。贺延光回忆说:“你无法想象,那一天的天安门广场是怎样的情景,当我们开始唱《国际歌》的时候,人群里有多少声音在跟我们一起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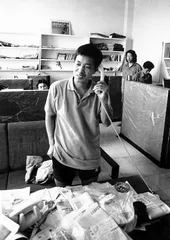
那一天贺延光还偷偷带了相机,记录下当时场面。讽刺的是,整个“四五”活动期间,用镜头记录下历史的,都是非专业的摄影爱好者们,禁令之下,专职摄影记者们缺席了。
4月1日晚上,贺延光发现他们的悼词被人撕掉了。4月2日上午,他把悼词工整地抄成大字,和别人一起用纱布裱糊好,再用透明塑料布罩起来,当天下午再次送到天安门广场。4月3日上午,工业局召开紧急会议,传达所谓追查谣言的通知。刚传达完,贺延光站起来反驳:“《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算不算攻击中央首长,要不要追查?应该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站出来回答!我要求党委把我的意见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4月4日早晨,他又写了一张观点明晰针对江青等人的小字报,去广场张贴。所有的行为,贺延光现在记忆,都是很单纯的对这个国家天然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感。
( 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活动 )
激烈和义愤终于给他带来了麻烦,一个多月后,1976年5月6日,贺延光被投进了监狱。
入狱和平反
贺延光后来才知道,他的案子当时被北京市“高度重视”,那封“揭发”他的举报信上,有当时北京市前四把手的分别批示。他被认定“幕后有黑手”。
贺延光被列入重点审查和打击对象,由13个人的大牢房转入两个人的小牢房,4个多月里被审讯了49次。还有一个十来个人的工作组到化纤厂,深挖所谓“反革命”,以致400人的厂子里100多人受到株连。
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人们内心的单纯,即便是在监狱里也没有什么差别。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发布当天,贺延光记得清楚,与他同牢的那个犯了事的18岁“小流氓”狱友,一下子就号啕大哭起来,释放出来的情感,真诚得不容置疑。对贺延光来说,听到这个消息的反应是复杂的,“这跟自己当时的处境相关。我会马上想到将来谁来接班的问题,是否能够出狱,我的命运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变化的契机跟我的命运直接相关”。
变化的契机比贺延光预期的更早到来,入狱7个月后,他被释放了。可是出狱的时候,公安局给作的结论是:虽然反“四人帮”,但对毛主席发生怀疑和动摇,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理由”是,贺延光在周总理逝世时说过这样的话:“周总理比毛主席年轻,如果没有人迫害,总理不会去世这么早。那样的话,主席百年之后,有总理在,事情好办。”
等贺延光回到化纤厂,领导班子已经换成查他的“调查组”的人,给他的“见面礼”,是要按照每月13块5的标准扣除入狱期间的伙食费。1977年5月,依旧“留着尾巴”的贺延光调任北京手表壳厂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改变的契机直到第二年才到来。
个人命运和总理记忆
贺延光感叹,自己就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1951年出生的他,身上有着太多那个时代的烙印。隔了30年的漫长时光,再来看自己的1976年,其实也是再审视那个时代的缩影。
贺延光说,小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这些领袖都是一个形象,是没有区别的,国家即党,党即领袖。那时候所接受的教育,学校里的和家里的有相当的一致性。贺延光说:“说实话,直到上小学我才知道国民党指的不是一个人。”他还记得小时候大约就4岁多,在部队大院食堂吃饭,大人们开玩笑,鼓掌让他讲话,他搬了一个小板凳,站到上面喊了一句,“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大人们掌声一片。其实他根本不了解那些话的意思。再大一些,四五年级的时候,政治在身上已经有了更加潜移默化的反应,贺延光举例,有一次上课造句,要用“毕竟”这个词,他造的句子是“斯大林尽管有错误,毕竟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老师当成范例。他感叹,“其实那个年纪的孩子懂什么呢?还是一种条件反射”。那时候广播里天天放的是“九评”,因家庭的缘故,他父亲那个级别的军人可以读《参考消息》,几个朋友到家里来,谈论的话题就是这些,有时候几乎是整张报纸都读下来。
同样因家庭的缘故,1964年贺延光一家从内蒙古搬来北京。“文革”初期,15岁的贺延光也成了红卫兵,但却是“内心忐忑不安的红卫兵”,原因是“我的出身当然是红五类,但是那时候到后来‘血统论’愈演愈烈,红五类也要查三代,虽然父亲是革命者,但是我爷爷那辈却是地主”。这时候的贺延光,“第一次对周恩来个人有了强烈印象”。因为周恩来反对血统论,认为人不能选择出身,但是可以选择革命道路,贺延光说,“这时候的周恩来,作为被人们敬重的领袖之一,把我们这样的人从惊恐和尴尬中解脱出来”。
“那时候对周恩来的印象,他就是一个‘管家’,这好像也是人们的一种共识。而且大家对周恩来的印象都非常好,他的出访、风度翩翩的样子,会被人们津津乐道。”
贺延光在“文革”后期下乡,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面对林彪事件时,他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心里的爆炸事件”,“简直就是毛骨悚然”。“现在想起来,林彪事件,对许多人而言,意味着我们禁锢了很久的思想之门第一次被开启了。”这就像是一个裂痕期,“个人开始思考,疑惑开始产生并且到后来被用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了”。但那时候的周恩来,并没有被这样疑惑,他的形象,是一个稳定国内局势的执行者,大家认为周恩来只是执行者,不可能有人质疑他了。
1973年,贺延光回到北京,当邓小平被批,周总理又病重,大家是一种对这个国家前途走向的真实忧虑,“大家对于社会的不满,其实是从个人生活的无望开始,邓小平带来的是最直接的经济变化,跟每个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和最真实的生活细节捆绑在一起”,对于邓小平的攻击,引发的或许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的关于生存的一种本能。周恩来的去世,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而且周恩来忍辱负重、兢兢业业、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形象,坚持“良心底线”的形象,在这样的背景中也被无限量放大了。
贺延光说,他曾经是那样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和周围人一样,急切而自然地“把个人命运和领袖命运捆绑在一起”,这种捆绑是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惯势”。30年之后的贺延光,更乐于思考的问题是,“真正健康的方式是把希望寄托于一种制度,而不是特定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