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错过张北海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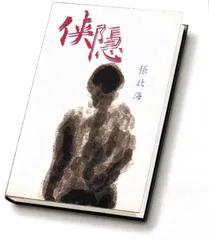
张北海完成他第一部长篇小说《侠隐》的时候,应该已经年过六十。这个书名有点诡异,多多少少预示了这部书在大陆市场的命运。2001年3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出《侠隐》大陆版,但转眼间这本书中大侠就隐没在图书江湖中。从当时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侠隐》,眼下无论图书零售店还是网上书城,《侠隐》已踪迹全无,连资料都查不到。说来惭愧,我这些年和书业沾点边,也自以为一直关心各类新书,但对张北海的《侠隐》几乎一无所知,直到一个月前,在香港的书肆中很偶然地拣到一本。
《侠隐》讲述一个复仇故事:抗战前夕,太行派掌门李天然,一位25岁的绝世高手,从美国回到北平,要了却一段灭门之仇杀妻之恨……故事并不特别重要,《侠隐》的精彩在于它是一部老北平的悼亡之作。抗战之前,“这是北平最好的时候”。作者靠回忆和想象,描画了一个动人的老百姓的老北平。
张北海1936年生于北京,后来去了台湾,再后来到了美国,是洛杉矶南加大比较文学硕士,叶嘉滢的学生,退休前在联合国当翻译。他是台湾演员张艾嘉的小叔叔,张艾嘉对友人戏称张北海是“全世界最后一个嬉皮士”。一本《侠隐》足够证明,张北海的襟怀、眼界、文字修养在当代华语作家中肯定第一流。
张北海写《侠隐》,全用收敛的白描手法,没有任何繁复的形容概括和内心独白。他笔下的老北平的街景是:“东四牌楼东北角搭着一座高高的警察亭子,可是里边那位交通警好像只管红绿灯,只管汽车电车,其他什么洋车马车,别说行人,连硬闯红灯的自行车,他都不理。偶尔挤不动了,他在上头用扩音喇叭喊一声,‘奔东的洋车快着点儿’!”
北京八百年都城,和政治缠绕得太紧。而张北海最热爱的北平十年(从1927到1936),正是皇城不再政治淡远的幕间休息年代,老百姓过日子的年代。张北海的北平故事里没有紫禁城。“别忘了这个日子……不管日本人什么时候给赶走,北平是再也回不来了……这个古都,这种日子,全要完了……一去不返,永远消失,再也没有了……”

两年前在北京听阿城聊过张北海——他好像没提《侠隐》。阿老是何等人物,能让他看上的作家怎么能错过。平心而论,从一个长篇着眼,《侠隐》的故事略显单调,人物不够复杂。但张北海的境界、见识、文章都叫人服气。对中国人文传统或者文人传统心存敬意的读者,可以不读二月河,不能错过张北海。
“不朽的白色巨塔”,这是日本新潮社为山崎丰子的名著《白色巨塔》(娄美莲、王华懋、王蕴洁、黄心宁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定下的宣传文案。“不朽”的赞语,《白色巨塔》当之无愧。这部小说问世于四十年前,四十年来,热卖巨浪浪浪相逐,从未退潮。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共有五个版本,收视率一版比一版高,最近一版在日本播出时据说创下32.1%的收视率记录,在小说背景地大阪高达45.7%。这部书的中译也已出过多种版本,每个版本的反应都不错。眼下,种种新出的“巨著”三个月后就乏人问津,一年后必定下架,面对一本畅销四十年的小说,你还找得出其他形容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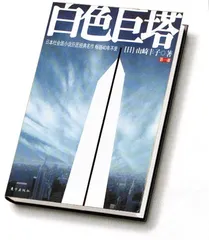
《白色巨塔》讲述大学医院权力倾轧,表现大学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斗。书中的正面人物说:“在这充满矛盾的现代社会里,还有胸怀理想的人,心中总期盼着,至少大学这个地方能本着人类的良知做事,我不认为现在的大学连这么小的要求都做不到。”这些话四十年后的中国人听着觉得亲切。看多了现在教育界、医疗界的故事,你会觉得《白色巨塔》写得还不够黑。这部小说里的人物,无论正面反面,都还有基本的道德底线,学术上特别用功,星期天人人都在苦读德文的医学书。而今天的中国大学,我知道的教授里一大半看“超级女声”的时间比读正经书的时间要多。虽然中国现实生活的资源比四十年前的日本要丰富,不过我仍然能断言,中国作家还是写不出《白色巨塔》,写不过山崎丰子。
山崎丰子并不是天赋特别好的作家,她说自己是“只会写小说的蠢蛋”。但她以勤奋、刻苦、用心保证了自己的成功。她住院的时候产生了写一部医院小说的想法,然后用了几年的工夫学习和搜集资料。她每次采访前都做好功课,“若要采访癌症手术,就得事先阅读专业书籍,将手术的步骤、周边的脏器等知识牢记在脑海里,否则一场采访也等于白做了”。最后出手,写到医院,医学界的读者以为作者是医生;写到诉讼,法律界的读者以为作者是律师。
中国作家住院时会想到写医生,嫖妓时会想到写小姐,这些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没有做功课的耐心和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