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舞蹈家的摇篮,一摇51年”
作者: 张琼
“高老师,坏了!”手机里弹出一条学生发来的消息,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看了一眼,摸不着头脑,问道:“怎么了?”“我把您的课堂教学片段发在了社交媒体账号上,这才一会儿工夫就有2万多点赞了,可我才7个粉丝呀!”
高度就这样意外走红了。这是一个时长仅12秒的短视频,从2024年6月7日发出不到3天,就有了近3亿浏览量。视频中,只见满头银发的高度正领着学生们跳蒙古族经典舞蹈《鄂尔多斯舞》,摆臂、踏步、转身,举手投足间尽显民族韵味。“高度老师一个人跳出了千军万马的感觉”“洒脱、自由,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民族舞”“老师连头发丝都在跳舞”,网友的留言还在不断增加。
事实上,早在走红之前,高度已是业内公认的“民族民间舞天花板”。几十年如一日的舞蹈生涯,从一个人在教室“练私功”到斩获荷花奖、桃李杯、文华奖,从学生到教师,从民间采风到创新民间舞教育理论,高度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民族民间舞事业。

“说实话,我之前其实特别抗拒网络流量,我跳舞不是为了流量。但看到大家因为这些视频开始关注民族民间舞,这让我觉得流量也有好的一面。”4个多月过去了,高度对走红这件事仍然保持谨慎,虽然他欣然同意学生继续发布教学视频,但也反复强调:“发之前一定得给我看一看,在专业这件事上,不能有一点疏漏,不敢有一丝怠慢。”
“差一点”“差很多”
看高度的讲课视频,很难不被他的专业性折服。
在一条讲授藏族舞腿部动作的视频里,高度注意到学生吸腿跳、撩腿跳的动作不够标准,他马上停下来,仔细地给他们示范、讲解。在中国民族民间舞中,藏族舞由于地域分布广阔,而且所在地区自然条件和文化差异显著,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舞蹈形态和肢体动作。要把不同地区之间的细微差异交代清楚,非常考验舞者的专业素养。一个学生抬起了腿。“你现在跳的是青海玉树的。”高度凭借经验一眼就辨认出来,“如果我们端着撩腿,幅度不那么大,就变成另一个地方的了。”说着,他带着同学们做起动作,帮助他们体会其中的分寸。
“对于舞蹈教学而言,口传身教是重要的教学方法。‘口传’包括舞蹈教师在授课时讲解动作的要求、举例启发和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身教’指教师做出示范,学生进行模仿。”高度告诉记者。
动作到位了,理解也要到位。舞蹈演员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向观众传递信息,对应到民族民间舞中,每一个动作都是人民生活的真实瞬间。于是,在高度的课堂视频里,经常能看到他带着学生们“下地劳作”:右膝跪地,左手悬空按住“羊头”,右手从下往上斜推,这段《牧业丰收》中的舞蹈动作其实是再现了牧民剪羊毛时的样子;“团扇”“招扇”的手上动作交替出现,像极了推销员在街边招徕顾客……“艺术最重要的是真实,风格取决于地域,民间所有的舞蹈都有自己的功能和要表达的情感。说到底,它就是我们的生活。”高度说。
专业还体现在情绪的表达上,课堂上,他总提醒愁眉苦脸的学生拿出精气神来。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严肃的课堂教学里,他偶尔也讲讲趣闻、说说笑话,总是逗得学生们哈哈大笑。这种对舞蹈的热情甚至延伸到了生活里,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讲到高兴处,高度会比划起来,仅靠着一双手,鱼儿游动、虎啸山林、孔雀开屏就有了画面,讲到民族民间舞的细节,又起身示范一番。“跳舞是情感的表达,我一兴奋就忘记自己在做什么,不由自主地会跳起来。我也跟学生说,要快乐一点,快乐地跳舞,快乐地生活,快乐地劳动。”
肢体表达、动作理解、情绪反应,在高度看来,舞蹈不仅仅是肌肉和骨骼的律动,举手投足间都是对专业标准的一丝不苟。“每次上课,我一说‘差一点’,学生们跟着就接‘差很多’。这是我和学生之间的默契。”高度说,“在今天的专业舞蹈院校里,中国民族民间舞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审美标准,这个标准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
民间舞从民间来
很难想象,今天被人们称为“民族民间舞专业天花板”的高度,刚进北舞时,能力并不出挑。
1958年,高度出生在辽宁大连一户普通人家,在被选入北京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院前身)之前,他完全没有接触过舞蹈。1973年,北京舞蹈学校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生。招生老师来到了高度所在的小学,看中了这个身材比例好、浓眉大眼的孩子,老师在他课桌上敲了3下,舞蹈的大门就这样向他敞开了。
“我记得很清楚,我是我们班的大队长,那天正在给鼓号队做指挥。校长朝我招了招手,我收了指挥棒,来到了他跟前。他递给我一张纸,我一看,是北京舞蹈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拿了就往家跑,我妈也不知道什么是舞蹈,只知道被北京录取了是件很光荣的事,就和我说‘去吧’。”高度回忆。
当时,北京舞蹈学校在大连只选了8个人,高度是其中之一,那一年他15岁。人生中的第一堂舞蹈课,他至今记忆犹新。第一堂课12个人,许多人都有童子功,老师一句“拿顶”,众人齐刷刷倒立起来,只有高度一个人站在那儿,手足无措。“当时我就暗下决心,他们会做的我也要会。”此后,从横叉、竖叉、拿顶等基本功到各种高难度动作,他都要利用课余时间偷偷跑到练功房做到标准、完美。3年过去,他成了班里的优等生。“有的网友会在视频里说,高老师的基本功怎么那么好啊,其实和当年的苦练有关系。老师教给你的是一部分,你的早功、晚功也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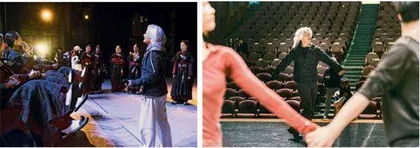

1976年,高度毕业留校,开始了漫长的舞蹈教学生涯。“我其实也想和同学们一样,去文工团、歌舞团做演员,站在舞台上跳舞。但当时学校缺老师,我就留下来了。”高度笑着回忆起往事,“其实我们那时候跳舞和现在一样,也面临很多诱惑,中间有人找我拍电影,赚快钱,但我最后还是选择留在教学一线。”
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源泉在民间,因此,到祖国各地采风是高度十分重视的教研工作。“第一次到云南采风,老师让我跟着民间艺人学鼓。我每天上午学鼓,下午就跟着他们下地干活。民族民间舞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你就得跟着老百姓,跟他们真正生活在一起。”
教研之余,高度还做过8年的舞剧导演,先后创排了《红河谷》《黄道婆》等作品。“和不同的剧团合作,和不同的演员接触,对于丰富艺术经历、拓展艺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时期,高度把荷花奖、文华奖等行业最高奖项几乎拿了个遍。
这次凭借短视频出圈后,有不少朋友纷纷给高度打电话、发信息、留言,有一条令他印象深刻——“高老师,我是你当年去云南采风时的司机,当年我只有20多岁,现在我已经70多岁了,看到你依然还在跳舞,我感到特别高兴。”
“我热爱这个职业,热爱民族民间舞。我们国家的民族民间舞蹈才是真正的富矿,有太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挖掘、去研究。”高度说。
“把头发都摇白了”
最近,北京舞蹈学院70周年校庆活动上,1980级到2024级的历届民族民间舞系师生在校园广场上跳起了藏族舞蹈《库玛拉》,领舞的就是高度。他和同事开玩笑说:“北京舞蹈学院被称为中国‘舞蹈家的摇篮’,我在这里一摇就是51年,把头发都摇白了!”
高度心里装的,始终是教研工作。“大学艺术教育走到今天,我们要不断地回过头去看一看,我们有没有丢失什么?因为一旦丢失,便是永远的丢失。”开创中国民族民间舞动作分析与编创等创新课程,主编出版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列教材,搭建技术技巧大赛、新剧目展演平台……高度希望民族民间舞这一学科不断升级、孕育人才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关注到它一直以来的发展。
2021年起,高度多次带队去云南,录制了近80套奔子栏锅庄舞。锅庄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奔子栏位于云南迪庆,藏语译为“公主起舞的乐园”,当地跳锅庄的习俗可以追溯到1300多年以前,起舞的百姓祈求地气茂盛、农务丰收、世界和平、吉祥安康。“用影像记录这些民间舞蹈非遗传承人的工作与生活,以及中国民间舞的生存发展现状,以便于我们进行相关的研究与提案,这是民族民间舞传承保护工作中重要的一环。”高度解释。
采访快要结束时,高度讲起自己的一个美好畅想:“将来,在每个城市的公园里,我们都开辟一块小小的练舞场地,旁边设立一个打卡点,还有一个小剧场。所有人可以来这里学习民族民间舞,锅庄、秧歌、花鼓灯……只要愿意,谁都可以跳起来。因为民族民间舞从民间来,最后还要回到民间去。”
编辑 高塬/美编 苑立荣/编审 张培
高度
北京舞蹈学院教授。1958年出生于辽宁大连,1973年进入北京舞蹈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民族民间舞教研工作至今。2024年6月,因为一条课堂教学视频走红,引发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