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为唐诗“破案”
作者: 陈娟
在复旦大学光华楼2715室和资料室中间,有一间“神秘的办公室”,那是陈尚君工作的地方。凡去过的人都印象深刻——屋里堆满了书籍和资料,桌上、凳上、地上到处都是,书架间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平日里,除特殊情况, 他每天会到这里上班,一待就是一整天。
这位专治唐代文学与古典文献的学者,常独坐此屋,将散布各处的文献资料,按照规范辨真伪、明归属,成一代学问。12年前,60岁的他曾站在十字路口。回身望,研究唐代文学近40年,正主持新旧《五代史》和《旧唐书》的点校,也凭一己之力编成《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往前看,年岁已高,身体渐衰,心忧自己还能做些什么。犹豫之间,他记起了一位老朋友“司马光”——人生失意之时,退而著书,用19年的时间写就《资治通鉴》,毕其功时已64岁。
“司马光身上最感人的一点,是一人一手一力完成一部传世大书。想到这里,我就心潮澎湃。我也想凭个人之力来做一件大事——重编全部存世唐诗。”陈尚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自此,他便将全部心血花在唐诗上,最终完成《唐五代诗全编》的纂校,于今年8月出版。
这是一部超大型唐诗总集文献,共收录唐五代时期诗歌55000余首,涉及诗人4200余名,总1225卷,包括无名氏68卷,“只要有一首诗、一句诗就收入”。甫一面世便“一部书成天下惊”,学界称赞陈尚君“继往哲,开来学”,直言这部大书的出版“是中国当代文史学界的荣誉”。
“一个人一生能完成这样一部宏大的著作,奉献给学术界,我感觉何其有幸。”陈尚君说。当整整50册书摆在面前那一刻,他既感到如释重负,又有惶恐与不安涌上心头——要接受所有人的检验和审视。
一人一手一力,重编唐诗
长期以来,大众最为熟知的唐诗总集文献是《全唐诗》。它成书于清康熙四十五年,由10位江南在籍翰林用一年半时间仓促编纂而成,不注文献来源,缺漏讹误百出。如一些重要作者未收录,一些唐以后人的诗误作唐诗,还有互见问题——一首诗既见于甲的名下,又见于乙的名下,还见于丙的名下,等等。
陈尚君最早发现《全唐诗》的问题可追溯到1979年。当时,他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研究唐宋文学。一天,他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读到学者孙望所著《全唐诗补遗》的摘录,发现一些重收、误收,便写了一篇文章,经老师之手转交给孙望。没想到孙先生回了信,用工楷写了几页纸,逐条答复,书出版时还有多处引用了陈尚君的意见。
当时的陈尚君,初涉学术,“读了孙先生的回信,有了信心”。之后,他先后写《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等文章,开始留心各类典籍资料中的唐诗,并将之与《全唐诗》作比较。再后来,他编《全唐诗续拾》,修订《全唐诗外编》,辑录唐人佚诗4000多首。20世纪80年代末,唐代文学界计划做一部《全唐五代诗》,“编纂出符合于我们这个时代学术水准的唐诗总集”,以取代清编《全唐诗》。陈尚君作为主编之一,“负责凡例、细则、样稿的起草……承担全书有别集传世者二百余家以外所有中小诗人作品的整理,并在第一阶段即杜甫以前部分文稿收齐以后,承担第二遍定稿之责任”。可惜后来因“人事纠纷而几度苍黄”,只得中途放弃。

直到20多年后,陈尚君下定决心重编唐诗。这一次,他不再假手他人,全凭“一人一手一力”完成。
“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步步有地雷,步步要小心。所有存世唐诗,都因校勘各本而读过5到10遍。所有涉及唐诗的文献、资料,包括一些传说、争议、是非等,都曾逐一分析条理,考订取舍。”陈尚君说。为完成这一浩大工程,他常年埋首在书桌前,每天工作到深夜,寒来暑往,不曾中断。“从复旦大学北门的一条小路回家,那个地方的树叶枯了,又繁茂了,又枯了,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这本书终于完成了。”
在《唐五代诗全编》中,陈尚君写了4000篇以上唐代诗歌作者的小传,剔除了历代流传的上万首诗歌,对那些诗“为什么是假的”做了考证和说明,并列举证据,还对可信的文本做了详尽的校对。
比如张继的《枫桥夜泊》。陈尚君研究发现题目有误,实则应为《夜宿松江》。而因题目误传,也影响了后人对诗意的理解,“原题中的松江,是今苏州河上游在苏州远郊的一段。近处没有寺庙,也没有桥,只有月落乌啼、江枫渔火,荒寒的远山间传来隐约的梵钟,伴随诗人无眠的夜晚。如是而已”。
再如李白的《静夜思》,宋本中是“床前看月光”,通行文本是经明代李攀龙所改的;《登鹳雀楼》几乎可以确认不是王之涣所写;崔颢《黄鹤楼》首句肯定是“昔人已乘白云去”,作“昔人已乘黄鹤去”是明代妄人所改;“清明时节雨纷纷”到南宋才出现,作者缺名,《全唐诗》和杜牧文集都不收,很难说是唐诗……
“我努力做到一切表达和取舍都追求冷静客观,避免个人感情,力戒一己好恶。”陈尚君说。他旨在“让唐诗回到唐朝”,“回到唐人立场,回到唐诗原貌。剔除大家长期以来的一些误解,改变一些文本的基本面貌,展现唐诗丰富而立体的真相”。
认识的唐代人比现代人多
“个人的能力非常有限,但是当天地同力一起支持我的时候,我也跟着时代的节拍努力前行,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回望整个纂修过程,陈尚君如是说。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似乎总能踩在时代的点上。
他生于上世纪50年代,父亲是会计,母亲是裁缝,没什么家学渊源。中学刚读一年,学校停课,他被下放到农场。8年间,他至少4年担任生产队长,天不亮就吹哨子,叫大家起床劳作。农闲时分,他找来所有能找到的书,从外国名著读到马列,从生物分类读到孔子、鲁迅。印象最深的是,1971年读《唐诗三百首》,“借来的,大会时翻看,被点名没收,至今想起来仍觉心痛”。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陈尚君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当时,整个校园一派新气象,每天早上图书馆、资料室的门还没开,门口就排起长长的队。陈尚君也疯狂读书,“全无条理,全无目的,兴之所至,浑囵吞象,一往无前”。 一年后,经老师推荐,严格考试,他考上本校研究生,师从朱东润先生,研究唐宋文学。朱东润先生是古代文史学家,也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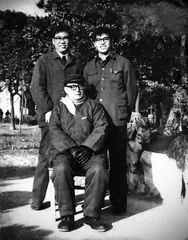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一年一个新气象,各种新思潮、新思想、新观点不断出现。我远离主流,孤独地行走在唐宋文学的世界里。”陈尚君说。后来,孤勇的他也慢慢蹚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学问之路。
朱东润当时已83岁,在家中书房授课,隔周上一次。“朱先生上课,格局宏大,议论透彻,充满怀疑精神。他主张讲中国文学必须知道外国文学,讲现代文学必须知道古代文学,也讲读懂作品必须知道作者为何这样写,这样写与前代有何不同,有什么寄意,有什么技法,等等。”陈尚君说。其间,先生会不断询问你如何看,说研究学术不要人云亦云。当时,陈尚君自觉学问浅薄,也未经过严格学术训练,对先生所讲还不能完全理解,但都记在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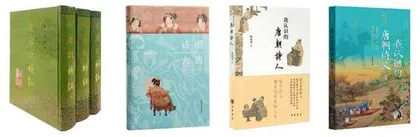
研一结束,朱先生给陈尚君布置学年论文,写大历元年之后的杜甫。这一年,是杜甫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离开成都,舟行万里,颠沛流离,最终死于途中。整个暑假,陈尚君搜集各种文献资料,遍读杜甫离蜀前后的诗歌,发现以前人都没有讲清楚杜甫晚年为何离开成都。再仔细研读资料,他找到一个线索——杜甫离开成都,并非是剑南节度使严武去世而失去寄托,严武是在他离开后去世的。事实的真相是,严武去世前曾奏请朝廷任命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这才买舟沿江东下,准备经荆州溯汉江北上,走京洛大道到长安赴职,途中因病无法继续前行,滞留夔州。
陈尚君沿着这一线索,一点点还原当时杜甫的生活与所思所想。他将发现写成论文《杜甫为郎离蜀考》,“朱先生看后大加赞赏,坚定了我做学术的信心”。之后,他感到难以兼顾唐宋,便弃宋专唐,渐渐将目光放在唐诗上。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一边教学,一边做研究。
“常常会有惊喜,比如发现一首诗的新版本,或发现一首诗的真正作者,都会让人激动不已。”陈尚君说。他不怕坐“冷板凳”,数十年如一日,翻检文献和资料,通过海量搜集证据、调查取证,解决一个个古人留下的悬案。久而久之,学生称他“大唐神探”,他则自嘲“唐朝户籍警”,因为对唐朝诗人做过拉网式排查,每个人的简历都了然于心。
“可以说,我认识的唐代人比现代人多。”他说。
站在古人的立场
无数个夜晚,陈尚君独居斗室,据善本校勘诗歌,口诵心念,目验心会,体会唐人在诗中倾诉的喜怒哀乐,内心不能不受到深深的触动。
“唐诗不是一张纸,也不是简单的文字,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有感情、有欲望、有爱恨的人,活生生地写出来的。将所有东西都读通后,唐代的社会以立体的面貌向我们展示,是生动而活泼的。”陈尚君说,他认为唐诗研究离不开对诗人的研究。2019年年初,他开始在《文史知识》开设专栏“我认识的唐朝诗人”,每月撰写一篇文章,为诗人写小传,皆是有感而发,力争做到深入浅出,客观论证,接近真相。
他写欧阳詹的深情。欧阳詹才华出众,可惜进士及第后仅八九年就去世了。好友韩愈很伤心,作《欧阳生哀辞》,称赞他“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可谓道德完人。事实上,根据同时人孟简和同乡后学黄璞所作之诗,可知欧阳詹往太原游历期间,曾与一官妓相恋,当时无法公开,只得分离。后来此女病亡,他得知消息,伤心不已,昏迷数日后离世。“中国古代文人多以道德示人,为爱情而情动五内,以身相殉者,则少之又少,欧阳詹之特别可贵之处,正在于此。”

他追踪杜甫在大历三年的足迹,梳理诗作,证实《登岳阳楼》里所谓“亲朋无一字”,确实是走投无路了。他写韩愈在潮州的经历,本想批评其《潮州刺史谢上表》的谄媚无耻,写的过程中则原谅了他的一切,“努力挽救自己的自然和政治生命,也有可以理解的理由吧”……这些文章,后来都被结集成书——《我认识的唐朝诗人》出版。
“我是站在唐朝特定的环境中来评价诗人或诗作,也比较愿意用古人的思路来理解作品,不是用当下的标准来要求古人。”陈尚君说。
研究唐诗这么多年,总有人问陈尚君,为什么现代人要读唐诗?唐诗究竟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