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团与迷雾
作者:陈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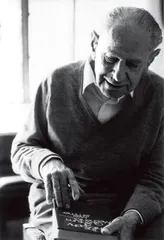 ( 卡尔·波普尔 )
( 卡尔·波普尔 )
本·拉登的下落是个谜团,美国人找不到他的原因是情报不足。与此相反,战后伊拉克局势是一团迷雾。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黑白分明的答案。而解谜的困难不在于信息太少,而是信息过于泛滥——对于伊拉克的战后局势,美国中情局有自己的立场,政客、学者、媒体、包括巴格达的出租车司机也有自己的看法。
判断谜团与迷雾,最好的方法是看更多的信息是否有益。对谜团而言,每增加一个新的信息,问题就会变得简单一点,迷雾则恰恰相反,更多的信息不仅无助于判断,反而会坏事。从泛滥的信息中理出头绪才是关键。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世界上最让人困惑的问题大都属于迷雾,而非谜团。气候变暖、核电安全、恐怖主义、生物工程、贫困问题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信息太多太复杂,并且涉及大量的“模糊地带”和“不确定性”,几乎没有得出一个结论的可能性。
费曼说,理解一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自己去完成它的推导。这是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这个世界是可以被人类所理解的,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其中的联系和潜在的规则。
科学家设计了很多模型,来解释气候变化的问题,但很少超过50个变量。真实世界远比模型要混乱和复杂,充满了我们尚未了解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气候的科学模型没有将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人类的心理、认知与行为模式考虑在内。

人类大脑之构造,就是要给每一个事件找出确切的理由。对模糊与不确定性的厌恨,是一种基于人本性中寻求安全感的本能。
为了降低判断的复杂性,我们宁可忽略一些矛盾的相关信息,或者编造理由,扭曲现实,以至于陷入各种非理性的认知陷阱,比如叙事谬误(编造并不存在的因果关系)、沉默的证据(忽略那些我们看不到的证据)、认知上的自大(习惯于高估自己的知识,而低估自己的无知)、损失厌恶(对损失的恐惧比对获得的快感更敏感)。我们的判断还很容易受到情境的暗示,比如在面试的时候,如果考官手中捧着一杯热咖啡,他给面试者的印象就会“温暖”;如果是一杯冷咖啡,则给对方的印象变成“冷漠”。
在MRI成像技术的帮助下,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观察”到自己如何掉入这些认知陷阱的。人类大脑中对不确定性情境进行评估的部分,和处理情感——非理性的主要来源——的大脑区域,二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当我们面对不确定性的决策,比如信息缺乏时,与情绪状态尤其是恐惧感相关的大脑区域,同时也被激活。这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后,美国人狂买防毒面具,而中国人集体抢盐。反之,当面对过多的选择时,大脑中与错误检测、损失厌恶等相关区域就会被激活。所以,每次当你经过超市的牙膏货架时,就会不由自主地焦虑。
解开迷雾的第一步,首先是意识到这些认知陷阱的存在。
过去几十年,一个新的学术领域逐渐浮出水面,它研究的是当信息不全,或者不完美,即面对不确定性的风险时,人们是如何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这些研究综合了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如数学、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以及现代神经科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就是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一直以“理性人”为理论基础,通过一个个精密的数学模型构筑起完美的理论体系。而卡尼曼教授等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则从实证出发,从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出发,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
卡尼曼教授认为,在面对不确定性情境时,人有两套完全不同的思维系统:一个系统是理性分析,根据事实和数据,权衡利弊,做出决策;另一套系统则是将风险作为一种感觉来把握,基于个人体验,对危险做出原始而快速的直觉反应,就像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大草原上突遇天敌。
人对“不确定性”的分析机制,并非井然有序、步步为营的理性分析,而是进化因素、大脑构造、个人经验、知识以及情感共同形成的复杂产物。两套认知系统在大脑中的分界如此明显,有时候你能感觉到二者之间的争斗。比如,如果每4次中有3次,你吃完海鲜后脸会肿得跟猪头一样,那么“逻辑”的左半脑会试图找出一个模式来描述其中的规律,而“直觉”的右半大脑会简单地告诉你:“离龙虾远点。”
人的直觉系统可以很有价值,有时候我们最好的决定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做出的,比如一个消防员在火灾爆炸发生之前就意识到危险,或者一个护士在病人心脏病发之前就预感到问题。但是,作为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继承下来的认知系统,直觉也有很多缺陷,比如对于未曾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们会倾向于低估它的风险。澳大利亚的葡萄园主对全球变暖有最直观的感受——夏天的气温越来越高,葡萄的收成季节不断提前,但对大部分人来说,海平面上升、干旱等危险,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而言都距离我们很遥远,所以很少真正感觉到气候变暖的危险。
心理学家还发现,一个人的焦虑承受量有限,一旦新的问题出现,比如股市下跌,或者个人问题出现,气候问题就被搁置一边了。
即使在理性模式下,我们也不擅长长线思考。实验证明,人类不喜欢迟到的利益,所以我们总是低估未来的收益。现在给你10块钱,或者2年后给你20块钱,大部分人会选择前者。同样,很难说服人们为了未来的气候安全而放弃当下的生活方式。
1965年,英国科学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在华盛顿大学做了一次长篇学术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关于云和钟”,副标题是“对理性问题与人类自由的探讨”。他认为,过去100年,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经历了两个极端:钟与云。
之前,世界的基本特征被概括为“钟”——一个稳定、规则、有序的系统,比如哥白尼的天体理论、牛顿的力学体系、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等。科学家相信每一个事件背后必定有一个原因,总有一种理论可以解释一切现象。但真实的生活是一个“云”的世界——湍流的水、变化莫测的股票市场、人的心理活动、毫无规律可言的生物种群的行为……它们就像云一样,一团混沌,不规则,无序,难以预测。
与波普尔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天的世界更加复杂和不稳定,尤其在一些影响全人类命运的问题上。
地球气候到底怎么了?
核电是安全的吗?
生物工程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按照传统的方法,科学家会在时间轴上构建一个问题演化的大致框架,列出过去与现在的状态,并尽可能在概率上估量每一种可能性。但不幸的是,科学家在估量长期风险上的能力并不比普通人强多少。日本地震就是很好的例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地震和海啸都属于正常风险,但没有人能预先估计到海啸会对福岛核电站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这种风险属于极小概率事件,按科学家的话来说,是一百万年一次的概率,但它就是发生了。
《黑天鹅》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日本地震之后撰文写道:“对数据和模型的过度依赖,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在一个非线性的世界里,再多的数据也无法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可能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科学无法解决小概率问题,更不该鼓励人们依赖于此。”
100年前,科幻小说家乔治·威尔士曾说,现代高科技社会里,一个合格的文明公民需要具备三种技巧:阅读、书写与统计学的思考。这些都是左半脑的工作,与福尔摩斯解决谜团的手法一致——依赖逻辑思维,以冰冷的、不动感情的方式从第一手证据中推导出事实。
世界显然是混沌的,宇宙我们至今也无法解释,可是困难在于,科学似乎是我们目前唯一的武器。科学的观点是无视小概率事件,所以核泄漏虽然是悲剧,但我们还是要建更多的核电站,因为我们需要电。除非有一天,科学突然取得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之后引起人们处世哲学的完全改变。
这并非不可能。所谓混沌,只是现阶段人类对世界的理解,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人们又会发现混沌下面的秩序。行星的运动、生命的历史,曾经都是无可把握的迷雾,最终变成了可以理解的谜团。但很多时候,又是科学,将谜团重新变成迷雾——牛顿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宇宙,然后相对论出现了,粉碎了对时空关系的传统理解。谜团与迷雾之间的转换,正是科学不断战胜不可知论的过程。
不过,为了解开21世纪的迷雾,我们恐怕需要强化右半脑的功能——非线性的、多视角的、创造性的综合思维模式。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加纳在《未来的五种心智》中提出的,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里,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具有五种心智:专业性、整合性、创造性、道德与尊重。他说:“人类无法处理复杂问题,除非我们接受这个世界复杂、混沌、连接的本质,参与其中,思考,讨论,角色扮演。”■
(文 / 陈赛) 谜团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