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与他们的上帝
作者:苗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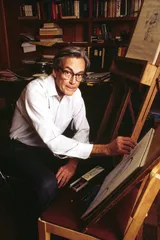 ( 理查德·费曼 )
( 理查德·费曼 )
“在这个事情上,我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我的导师边说着边摊开双手,耸了耸肩,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姿势,“我从小就被父母带着每周都去教堂,自然而然就成了一名基督徒。”我和我的导师平时并没有太多机会谈论和学术无关的话题,见面时要么都穿着防护服(这防护服是用来保护仪器而不是实验员的)在无尘实验室里一起干活,要么就在一起分析数据,难得有机会通过我的学院请研究生和他们的导师一起吃正餐来增进交流。虽说大家都西装领带皮鞋锃亮,吃饭时腰板都挺得笔直,我心里也有些紧张。不过两杯红酒下肚,就都放松下来,我和我导师的话题也从实验转到了宗教。这位以物理学为职业的大学教授毫不迟疑,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并且意犹未尽地补充道:“我们系的很多教师都是基督徒啊。”在这个宗教历史久远的国家,宗教信仰和文化就像他们对啤酒的品位一样是一种传统。“那你现在还去教堂吗?”我问道。“哦不,我早就不去了,休息的时候我在家喝红酒,听交响乐,陪我儿子玩。”这个标准的英国中产阶级这样回答我,说着喝光了杯中的红酒。
当我关心我导师的宗教信仰的时候,全然忘记了自己手腕上也戴着一串念珠,这是个鲜明的佛教徒的标志,虽然我从来没有烧过一炷香,也没有通读过任何一部佛经,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佛教徒。现在回想,和我的导师一样,实际上我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小时候我家与那座知名的古刹只有一墙之隔,那时那座藏传佛教的寺庙还没有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也还没收90块钱一张的门票,所以我每天都要爬到庙里山顶上的大雄宝殿里仰望那个20多米高的千手千眼佛像。我虽然没有佛性,在那个环境里却也不觉得害怕,只是觉得每天来看看这位老朋友。因此成为佛教徒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了,朋友之间是不需要烧香下跪的,我心里想什么他自然知道。宗教于我而言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并不虚无,不刻意,正如我手上戴的念珠也只是朋友送的一个礼物而已。
现在年轻人中非常火爆的电视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讲的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4个年轻的物理学家插科打诨的搞笑故事,这4个物理学家的家庭背景都被精心设置,4个人分别出自天主教、犹太教、印度教和科学家家庭。天主教家庭认为婚前性行为是“罪”(Sin),犹太教家庭则希望只和犹太人通婚,印度教则稀奇古怪的教规一大堆。而出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年轻物理学家们完全没有受到家庭宗教传统的影响,科学是他们唯一的信仰,因此剧情也就轻松明快,在电视剧里,科学和宗教仿佛是一对早已干脆分手的情侣,彼此关系撇得清清爽爽。而实际上,科学与宗教更像是一对纠结的怨侣,它们之间的关系没人能说得清。
1600年,科学与宗教的纠纷激化,上演了史上最可怖也最值得铭记的一幕,布鲁诺因为坚持日心说而被教廷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而布鲁诺也从此成为追求真理、为科学殉难的标志。此时科学刚刚在欧洲萌芽,基督教势力统治着社会,无神论和异教都不能被容忍,宗教犹如女星大S散发着王者气息。在当时,宗教实际上并没有排斥科学,它认为科学是理解上帝的一个途径,它也曾经不停地对科学展示柔情蜜意。这在1727年牛顿爵士的葬礼上达到了顶点——伦敦城万人空巷为牛顿送葬,牛顿作为最伟大的科学家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以这两种身份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在不朽名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牛顿空前总结出宇宙运行的规律,同时也认为宇宙是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的伟大创造。在他看来,数学和物理学都是用来理解上帝创造世界的途径。科学与宗教的结合,一方面可能是当时宗教氛围极浓厚,势力也极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科学水准尚不足让它离开宗教独立发展。要知道,牛顿晚年还曾经学炼金术,试图从其他金属中提炼出金子来,就是因为当时人们对于分子原子还一无所知,丝毫不了解事物的内在结构。牛顿的力学体系中“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概念只能求助于上帝才能有一个“第一推动”,即是说虽然宇宙在运转,人类也在自由发展,但是在这一切的开端,需要有一个更高级的智慧来创造推动这一切,这就是上帝的工作。
如同大多数的爱情一样,幸福一转眼就变成了回忆,科学与宗教关注的领域多有重叠,解释又如此不同,很快便不能互相容忍。随着宗教势力的萎缩,人类的意志得到空前扩张,好像是为科学的发展铺上了两条铁轨,而科学就像是一辆虽然发动缓慢却越来越快而逐渐不可阻挡的火车向未知前进。“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宗教无非是转眼即逝的一个山,一汪水,甚至只是一个散发着腐臭的坟头而已了。地底下有煤和石油,没发现地狱,太空里冷冷清清的,伊甸园谁也没见过。上帝?我和他不熟——宗教逐渐成为被奚落的对象。
此时的宗教如同一个低眉顺眼的小媳妇,“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心里是欢喜的,又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科学占领了它和宗教交集的所有领域,而宗教则死死守卫着“信仰”,因为科学无关信仰,只关注事实。无神论者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演讲中说道:“我认为科学不可能否定上帝的存在,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没人知道上帝是什么,究竟是一个西方宗教传统的形象或是一个宇宙的创造者。”他还说,“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科学所阐述的并不是对或者错,而是对于我们所了解的事情有多大程度的确定性”。有没有一个上帝是个宗教问题,而有多大的可能性存在一个上帝,则是个科学问题。科学与宗教的差别就在于此。
如今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如同教堂里唱赞美诗常常吸引到的音乐爱好者更多于信徒。“上帝”仍然被挂在人们的嘴边,但几乎已经没有了神学的意味。爱因斯坦也爱提到这位造物主,他有一句名言:“上帝不是在掷骰子。”在这里,“上帝”指的是宇宙规律,对此,他还曾经专门说过:“我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他以宇宙的秩序与和谐来示现,而不是那个会干涉人类命运和行为的上帝。”对于爱因斯坦来说,上帝就是自然界的法则。但是同时,爱因斯坦也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此处的宗教,我认为爱因斯坦指的是信仰,对于物理规律是美的信仰。正是因为如此,宗教与泛神论和文化传统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在科学与宗教传统都发达的国家里,出现声称自己既是科学家又是基督徒的人并不少。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们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并没有指望在原子或是宇宙中发现某种神创的证据,上帝成为他们所寻求的理论的代名词。
科学与宗教似乎又一次找到了一个可以彼此和睦相处的平衡点,尽管这并不是看上去那么容易。很多人仍然宣称进化论与《圣经》并不冲突(因为实在是有太多的证据证明进化论的合理性),也有人仍然试图在量子力学里寻找神的踪迹。在剑桥这样的小城里,常有教堂举办宗教和科学界的对话,希望创造某种和谐。这种场景,可能也只是在民众普遍科学素养比较高而且宗教传统悠久的国度内出现。在科学尚未昌明、教育水准不高、社会又缺乏宽容的地方,科学与宗教依然是相互仇视,彼此不能消灭对方却又不能相互容忍。各种旧式的迷信还有大批的信徒,打着各种幌子有各种稀奇古怪新名词的新型迷信更是方兴未艾。在这里,科学成了堂吉诃德对空挥舞的长剑,锐利却无从下手;宗教却和迷信纠缠不清,丢失传统,没有文化色彩,却又成为愚昧民众的安慰剂。在这个科学与宗教的新战场上,只有呐喊者,没有人倾听。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科学与宗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两者都可以即让人类展现出最好一面的同时也可以让人类释放出最坏的一面。核武器与核电站运用的理论相同,特蕾莎修女和本·拉登都受到了宗教力量的感召。科学与宗教都起源于人类对于未知的好奇和探索,这种探索或许也会引领人类走向毁灭。无论何时,最重要的都是宽容的心态和深刻的自省,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文 / 苗千) 上帝科学科学家牛顿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