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200周年诞辰
作者:薛巍
假如梭罗还活着
今年的7月12日是美国作家梭罗的第200个生日。他的家乡康科德将举行为期4天的庆典,镇上的旅馆3年前就被订满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前梭罗学会主席威廉·豪沃斯在《美国学者》杂志上撰文说,梭罗环保英雄的形象在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时达到顶点,如今他却遭到了嘲笑,保守主义者痛恨他的反商业情绪,后现代思想家们认为自然是可疑的绿色的模糊形状。现在有许多读者说他是懒惰的富家子弟,傲慢、缺乏幽默感,是说谎的精英。
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欣赏梭罗的老师爱默生,对梭罗则非常不屑:“这位伟大的自然保护主义者放火焚烧康科德森林;这位爱默生自助观念的典范,却在黄昏从瓦尔登潜回,向莉迪亚·爱默生要晚饭吃;梭罗敬仰的诗人惠特曼认为梭罗病态地厌弃人类。罗威尔说,梭罗似乎在公开场合主张回到燧石与黑铁的时代,而他的兜里却揣着一盒火柴,必要的时候也知道如何熟练地使用。”
豪沃斯介绍说,如今梭罗在学术研究上的命运令人担心。学院派的批评提出了各种版本的梭罗:躁狂-抑郁、同性恋、异性恋、厌恶女性、马克思主义者、天主教徒、佛教徒、迷恋仙境。但他的其他方面仍有待全面的研究:居家男人、灵性之人、科学工作者、日记作者。豪沃斯说:“我研究了一辈子梭罗。我不喜欢他也不憎恨他,但我非常了解他。我查找他的论文,在康科德住过,重复了他的旅行,两次通读他的日记。他骨子里是工人阶级,在他哥哥去世之后,独自承担家里的铅笔厂,在厂里吸入的石墨灰损害了他的肺。住在瓦尔登湖边时,他自己洗碗,在很冷的湖水里洗衣服。”
豪沃斯认为,在环境恶化的今天我们非常需要梭罗的环保意识。“南极在融化,授粉的无人机也许会代替正在死掉的蜜蜂,工业主义在损毁地球的外表。以前清澈的瓦尔登湖淤积了重金属、放射性标记物和工业磷。”1860年梭罗对一位朋友说:“如果不能把房子放在一个尚可忍受的地球上,房子有什么用呢?”如果他还活着,他会喜欢如今的许多东西:音乐点播、GPS导航(尤其是对一个测量员来说)、网上丰富的自然视频;他会喜欢强大的数据库,欣赏把他的书做成超链接、加以可视化的尝试。
《瓦尔登湖》出版之后,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不多的评论中有一篇来自英国,夸奖它富有诗意的感受力,作者是乔治·艾略特。1848年他又写了论文《公民的不服从》,直接影响了世界历史,因为他得到了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的敬佩。他的一些描写被同时代人视为无意义的漫谈,现在被气候学家视为珍贵的研究。他对康科德地区河流、湖泊做了详尽的研究,被后人视为美国第一位湖泊学家。他的植物学记录也成了研究全球变暖的必需品。
美国哲学家约翰·卡格说:“蒙田远非一位隐士,他积极地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他研究了风景和野生动植物,研究了镇上的人,研究了他自己。他的结论是,如果把其中一个跟其他事物割裂开来,它们都无法完整地被看到。”
《纽约时报》艺评人霍兰德·科特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梭罗开始厌恶人类,这是有原因的。随着他对自然界的热爱变得敏锐,他开始相信树是有灵魂的,他变得无法容忍人类的掠夺行为:肆无忌惮地猎取动物,往土地上丢垃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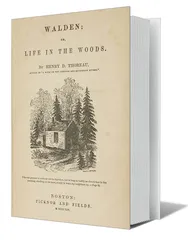 梭罗的坎坷经历
梭罗的坎坷经历
豪沃斯介绍说,《瓦尔登湖》中,一个厌倦了城镇生活的人在林中的湖边盖了一个小房子,在那里孤独地住了一年,观察内在和外在的天气。《瓦尔登湖》也是一个中年人孤独的梦,是一次治疗行动,记录的是一个作家重访他任性的、自命不凡的青年时代。这是回忆录和精神之旅的双重叙述,其范围没有超出离家几英里的范围,花销不超过3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730美元)。多年来,爱默生雇用梭罗给他打杂,后来把自己的地交给梭罗使用,希望他在瓦尔登湖的逗留能宣传一下超验主义者的美德。
今天,瓦尔登湖和它的林地组成了一个公园,每年有近50万参观者,但是在1845年7月梭罗去的时候,它的湖滨非常凄凉,都是些树桩、老旧的工业遗址和擅自占用空地者的小屋。他在《生活的目的》一章中写道:“我到树林子去,是因为我希望自己有目的地生活,仅仅面对生活中的基本事实,看看我能不能学会生活要教给我的东西,免得我在弥留之际觉得自己虚度了一生。”他脑子里想着死亡,因为他去瓦尔登湖本来是计划写另一本书的,一本记录他跟哥哥约翰的一场旅行,约翰在1842年死于破伤风。
豪沃斯指出,《瓦尔登湖》并不好读,读者最好跳过冗长、过时、粗糙的第一章“省俭有方”,从第二章读起。因为《瓦尔登湖》是很偶然地形成的一本书,是“回收利用的谈话、随笔的碎片和个人的发泄组成的大杂烩”。许多段落好像是在说给一个看不见的同伴听的。他在瓦尔登湖居住的半途中,因为拒绝交税而在监狱里过了一个晚上,他认为税收会用于赞同奴隶制的美墨战争。在有人替他交了罚款之后(可能是他的一位阿姨),他前往缅因州登山。被暴风雨困在山上时,他在一片被烧过的树林附近躲雨,看到再生的树叶时他感叹:“坚实的土地!真实的世界!常识!”入狱和登山的经历把《瓦尔登湖》的内容从狭隘的个人抱怨变成了更广阔范围内的遭遇。
1847年秋,30岁的梭罗离开了瓦尔登湖的房子,再也没有回去过。1849年他出版了《一周》一书,结果卖不出去,他用独轮车把卖不出去的书从火车站运回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有了近900部藏书,其中700多部是我自己写的。”为了还债,他成了土地测量员。这一经历帮他了解了当地的生态系统。
梭罗最喜欢的叙述体系是旅行和日历。《瓦尔登湖》把这两者融合了起来。秋天的凉意唤醒了他对地点的神秘性的感知。冬天带来了休眠和思考。在最冷的一个月,读者抵达了全书的高潮,他描写了冬日的瓦尔登湖。他对瓦尔登做了仔细勘探,发现湖的最深处是102英尺。“我真心感谢瓦尔登湖,这么深,这么纯洁,可以作为一种象征。”最后随着一年循环的结束,又到了春天。他在穿过铁路前往村子时,看到解冻后的泥沙从铁路两侧的陡坡深沟流下去。“路基上布满叶饰图案,如同火炉里的熔滓,说明大自然内部正是一片旺火。大地不仅仅是死气沉沉的历史的一个片段,它是活生生的诗歌。我们这个地球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改变自己,在自己的轨道上扑棱翅膀。”
梭罗44岁时死于肺结核。他的日记有200多万字,47册、7000页。“这是美国文学最大的、难以估量的秘密,也是会改变梭罗研究的一面透镜。”爱默生的日记是按主题排列的,梭罗的日记是按时间顺序排的。在野外远足时他会停下来记下他的发现:开花的植物,觅食的鸟,水中的树影。他的眼睛和头脑不懈地在工作。他在书中说:“清醒才是真正活着。我们必须学会自己苏醒,使自己保持清醒,不靠机械的帮助,而是寄厚望于黎明,就算我们在酣睡之际,黎明也不会抛弃我们。”//被误读的梭罗//
罗伯特·雷说,几乎所有被认为是常识的关于梭罗的认识都是错的,比如他并不是超验主义者。
摆脱绝望
《瓦尔登湖》的注疏作者杰夫里·克莱默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从中学到大学的必读书,销路很好。但《瓦尔登湖》并不好读,因为“梭罗的写作是多层次的,而且他经常用双关语或文字游戏”。再者,“梭罗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他还能广泛吸收。他阅读和理解别处发现的思想,然后把它们带进他自己的作品”。
《瓦尔登湖》在中国也十分畅销,编辑何家炜说,从2003到2012年,10年间《瓦尔登湖》出版了30个中译本,希望《瓦尔登湖》全注疏本是读者真正能读懂的译本。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盛嘉在《误读的经典》一文中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梭罗是一位被忽视的边缘人、一个被误读了的偶像、一个被扭曲了的偏执狂、一个漫画式的原野狂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异类。从表面上看,《瓦尔登湖》是梭罗在瓦尔登湖边的森林生活经历的记载,但仔细阅读文本,并考察其语境,读者可能会发现,梭罗其实是在以他特有的方式探索和回答了不仅是他自己当时所面临的一些困惑与问题,也是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基本问题。瓦尔登不仅是他的隐居之地、林中的小居,同时也是他的思想作坊、社会实验场、多样性的课堂、蕴藏丰富的书房、特异的大学、自然博物馆、祈祷的教会,还是身心放纵的荒野、怪异的梦乡、生存的角斗场、强壮体魄的运动场、疗养身体的医院、世俗建构的监狱、心灵忏悔幽暗之地和灵魂神圣的祭坛。”
罗伯特·雷说,几乎所有关于被认为是常识的关于梭罗的认识都是错的:一、他在树林里不只住了几个月,而是两年多,准确地说,是26个月,从1845年的7月4日到1847年9月6日。他1845年开始建房子,1846年他去缅因州远足了两周。二、虽然《瓦尔登湖》的第一版最终卖完了,但这本书并没有让梭罗立刻成名。实际上,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被认为是爱默生的弟子。他在20世纪因为政治抗议和环保主义问题才再次流行起来。三、梭罗通常被归为超验主义者,爱默生阐述的这种哲学是一种新柏拉图主义,认为世界提供了一系列有待破解的符号,这些符号包含着永恒、神圣、超验的真理。梭罗当初住到瓦尔登湖旁边时也许还是一个超验主义者,但之后就变了,他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永远生活在当下,有效地利用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偶然,就像青草坦然承受落在它们身上的最轻微的露水的滋润,而不是把时间荒废在为了失去机会而悔恨的话,那我们就有福了。”他的目标不是解读世界,而是把自己沉浸其中。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如果我想去的地方必须用梯子才能到,我会放弃努力抵达那里。因为我真正要去的地方是我一定现在已经在的地方。一切需要爬梯子才能到的地方我都没兴趣。”四、梭罗的目标是向他自己以及我们展示如何摆脱绝望的生活。“即使在所谓常人的游戏和娱乐之中,也掩藏着一种千篇一律然而无人察觉的绝望。智慧的一个特征,就是不要去做绝望的事情。”摆脱绝望需要扭转方向。他说,只有当我们学会用正确的名字来称呼事物时,我们才能找到通往快乐生活的大门。比如钱,它不只是我们用来购买其他商品的东西,它本身也是一种商品,需要去买。一件东西的价格是我们用来交换它需要的生活的数量。
最后,《瓦尔登湖》这本书并不好读,梭罗在《阅读》一章中提醒过读者:“正确阅读,亦即以真正的精神读真正的书籍,是一项高贵的活动,和当代的习惯所承认的所有活动比起来,会让读者感到更加劳累。读书需要的训练,就像运动员接受的训练,而且人们差不多要终其一生追求这个目标。”
梭罗与苏格拉底
梭罗离群索居,主张过简朴的生活,这很像是禁欲苦行的斯多葛学派。但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安德森提出,梭罗继承的是犬儒学派而不是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梭罗受到了古希腊和罗马斯多葛学派的影响。但支撑这种影响的是跟古代犬儒学派更直接的亲缘关系,这些犬儒把自己视为苏格拉底真正的继承人。”把梭罗当作犬儒学派的后人有一个好处,能帮我们理解阅读梭罗时遇到的一些难题。比如,关于梭罗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存在着争议。作为犬儒,他会批判政府糟糕的传统和他自己不加批判地从政府那里得到的习惯,他会推崇个人的独立。但是,犬儒不是抵制一切文化传统,他们主要是抵制对当前造成危害的传统。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梭罗为何拒绝把奴隶制合法化的政府,但是接受建造公路的政府。
乔纳森·埃尔斯沃思则提出,梭罗很像苏格拉底。“梭罗的《瓦尔登湖》今天仍处于哲学的边缘,因为我们仍然未能确定它是哪种书。所以好像《瓦尔登湖》最多被认为是一部有助于哲学思考的文学作品,但它不应被视为哲学著作。但《瓦尔登湖》对哲学很重要,忽视它的哲学关切不仅会误解这部著作传达的部分信息,而且会误解整部书。这本书是一种古代文学类型——苏格拉底的话语——的现代版,《瓦尔登湖》的核心目标是苏格拉底式的,创作它的目的是让它充当自我省察的催化剂。如果说哲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自我省察,那梭罗的著作就应该被当作重要的哲学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瓦尔登湖》是重要的哲学辅助手段之一,应该被视为最珍贵的哲学文本之一。”
乍看上去,梭罗写的都是树林或室内陈设的细节,但苏格拉底对《瓦尔登湖》有着深远的影响,梭罗在书中插入了许多对苏格拉底的影射。比如在《阅读》中,梭罗抱怨:“我们在身体的每一项营养或疾患上花销很大,超过我们在精神营养上的花费。这个镇光是在市政厅上就花费了1.7万美元,但是要为那个空壳装进真正的实质性东西,注入鲜活的智慧,可能100年也不会花费这么多钱。”这让人想起苏格拉底劝告雅典人不能更关心城市的财产而非城市本身。梭罗说:“不要给我爱情、金钱和名声,给我真理。”这说明他赞同苏格拉底的志向:“我不会停止向我遇到的任何一个人指出,作为雅典这个最伟大的、以智慧和力量著称的城邦的公民,你渴求去占有财富、名声和荣誉,却不关心智慧和真理,以及你灵魂的最佳状态,你不感到可耻吗?”对苏格拉底来说,最重要的是灵魂的健康,这种健康始于认识到和承认自己缺乏智慧。梭罗的看法是这一观点的回响:“一个忙于劳作的人,根本没有闲暇每天关注真正完整的生活。他除了当一台机器,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经常需要用到自己的知识的人,怎么还能牢记自己的无知——人的成长需要无知。”
梭罗还改写了苏格拉底因为他对雅典的贡献而提出的要求,苏格拉底说他理应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获胜者一样在表功厅得到免费的饭菜,因为那些获胜者让你们以为自己很快乐,我让你们真的快乐。梭罗说,康科德镇没有赏识他的功绩。“多年来,我将自己任命为暴风雪和暴风雨的观察员,并且忠心耿耿地行使我的职责;我还是一个测量员,不是测量铁路,而是测量森林小道和所有越界通道,看管过镇上的野生动物。”但是镇上的居民还是不愿意让他进入镇政府当公务员,不愿让他挂一份闲差,支付他一点微薄的薪水。苏格拉底和梭罗都希望扩展他们的同胞关于公共服务的概念,让他们意识到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人们交口称赞和认为成功的方式,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我们为什么要靠贬低别的成功方式,而夸大某一种成功方式呢?”这话是梭罗说的,但也是很久以前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文学苏格拉底梭罗爱默生瓦尔登湖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