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聊斋志异·画皮》中的经典语句与其现代意义
作者: 张修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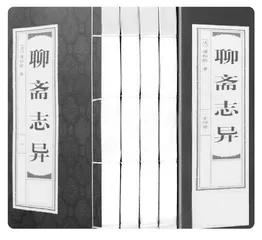
小时候读过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画皮》,也看过根据《画皮》改编的同名电影,那时候给我的印象除了恐怖之外,就是模糊地认识到人的两面性。长大后,重温《画皮》才发现自己的认知竟是那样肤浅,这篇作品语言的精粹性和思想高度有着多重解读的可能。
一、经典语句的简练性
《画皮》开篇首句“太原王生,早行”,仅六字就将地点、人物、时间交代清楚。其中,“早行”二字尤为微妙,让人浮想联翩:是大早上出门,还是大早上回家?若是前者,大早上出门是要干什么去?若是后者,昨夜他又滞留何方?短短二字引人遐思。作为一介书生,大早上回家,那王生昨晚去了哪儿?让读者不由沉思。走着走着,王生好像看到了什么,暗合《聊斋志异》的叙事传统—独行书生必遇异事。果见女子现身,按志怪逻辑推之,非鬼即魅。再看王生反应,“急走趁之”,王生飞快地跑过去,定睛一看,“乃二八姝丽”。此处“二八”明指十六芳龄,“姝”字状其容止端庄,虽值妙龄却显娴雅气度。寥寥九字既写书生急切之态,亦勾少女形神特质。王生见此美貌,心生爱恋之情。接下来引出了《聊斋志异》经典的三问三答。
“何夙夜踽踽独行?”这是王生的首问,意思是:姑娘,大清早的,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王生是要确定姑娘是不是一个人独行。一个“独”字,就将王生的心思展露出来。
那女子如此回答:“行道之人,不能解愁忧,何劳相问?”女子说,你就是一个路过的行人,又不能帮我排忧解困,问这么多干什么。女子是在拒绝吗?不,表面是拒绝,实际是欲拒还迎。“不能解忧愁”,明显地给予王生一种暗示,甚至抛出橄榄枝。女子把自己内心的渴求既展露又掩藏。
女子的这一问肯定引来王生的回答:“卿何愁忧,或可效力,不辞也。”“不辞也”,多么精湛的回答,意即定当帮之,直接亮明了自己的态度。
“父母贪赂,鬻妾朱门。嫡妒甚,朝詈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将远遁耳。”女子道出父母贪图钱财,把自己卖给有钱人做妾,早晚挨大夫人辱骂才无奈出逃。其中经典处为“朝詈而夕楚辱之”,直接把每天早晚挨打受辱之事道给王生,直接把自己的所需转化为人的同情,令王生唾手可得。
“何之?”王生直接问她要往哪里去。这两个字,体现了王生的迫不及待,直击关键之处,无须闲言碎语。
女子神情黯然地说:“在亡之人,乌有定所。”“乌有定所”,恰是女子直接抛出的暗语。一个逃亡的人,能有什么定所呢?言外之意,哪里都可以。
王生心生暗喜,开口相邀:“敝庐不远,即烦枉顾。”仅仅两个字“不远”,就让对方欲拒还迎,走向了自然的顺从。女子并未作答,只是面露喜色,“女喜,从之”。初遇到相随的转折便收束于这无声的应允之中。
这简约的三问三答直指人物的内心世界,具有极强的画面感。男女互有所需却不点破,一切水到渠成,两人你情我浓就这样名正言顺地拉开了帷幕。到了王生家里,女子问道:“君何无家口?”显然女子是问他的婚事。王生怎么回答?如若欺骗女子说没结婚,那将来女子知道真相怎么办?若回答结婚了,女子不高兴怎么办?自己的小心思实现不了怎么办?看王生怎么回答的:“斋耳。”这里是我的书房,你甭管我的婚事,这里是我们的二人世界。这样的回答是很高级的,果然二人住在了一起。
过了一段时间,王生出门,路上遇一道士,道士手拿拂尘疑惑道:“惑哉!世固有死将临而不悟者。”道士直接说王生死到临头还不醒悟,问他家里是不是来了生人,身上满是妖气。这下王生害怕了,他急忙回家,却见大门紧锁,于是便翻墙入院,只见院里阴风阵阵,一推房门也是锁着,感觉太奇怪了。于是,王生来到窗口,叠指弹窗,弹出一个小洞,往里一瞧,直吓得他三魂渺渺、七魄茫茫,他见到了什么?
“见一狞鬼,面翠色,齿巉巉如锯。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鬼的形态展现出来了—脸碧绿色,牙齿像锯;接着是心理世界的刻画—“已而掷笔”,意即女子画好人皮,兴奋之际把笔一扔,犹如画家创作完一幅满意的作品一样;然后她“举皮”欣赏,而后“如振衣状”,即抖抖衣服,那种满足状态全展露出来了。简洁的语言展现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就像我们生活中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后满意的心情跃然纸上。
但是王生害怕呀,他怎么样?他“兽伏而出”,像野兽一样逃窜出去,直接去找道士了。这是多么精彩的描写!
道士见到王生的第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此物亦良苦,甫能觅代者,予亦不忍伤其生。”道士说妖孽也很可怜,他不忍心伤害她。接着,道士让王生带着他的拂尘,挂在门口,自然能保王生性命。这个道士好像了解女鬼的背景。
王生很高兴,把拂尘带回家挂在了门口。到了晚上的时候,只听咚咚咚的脚步声,女鬼来了。王生很害怕,“自不敢窥也,使妻窥之”。原来,王生是有妻子的,他的妻子姓陈。妻子一看,外面有个面目狰狞的女子很生气地看着挂在那里的拂尘。女鬼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只能“立而切齿,良久乃去”。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了,“取拂碎之,坏寝门而入”,即把拂尘拿起来撕了个粉碎,径直破门而入王生的房间。接下来九个字,三个动作,一气呵成:“蹬生床,裂生腹,掬生心。”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场面:蹬上王生的床,直接撕裂他的肚子,挖走了他的心。但是仔细想一下,女鬼图什么?她真正想抓走的是什么?她想要的是这个男子的一颗真心。人们总说这个女子吃人心是为了滋补,那为什么那天早上不直接把王生的心吃掉呢?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陪伴王生呢?我们可以从两人初见时,王生与女子的三问三答中找到答案。女子前世被卖做妾,不要说情爱了,她连基本做人的尊严都得不到。女子可能在做妾期间而亡,化为女鬼,好像是留恋人间得不到的温暖,这辈子得到了,就想倍加珍惜。而今,她发现王生知道真相已经离她而去,他还请道士降她:门口挂拂尘。女子意识到王生再也回不到她的身边。她只希望得到一颗心,别无他求。你说这个女子做错了吗?她不就是画了张皮吗?因为只有这张皮才能掩盖她的身份,她才能继续拥有人世间的爱和温暖。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们身边有多少披着“外衣”的人呢?就像我们生活中的男女约会时,女子借补妆暂离,待卸去妆容重返席间,对方乍见素颜时的惊诧。恰因这层“外衣”剥落,对方才看到了真相。生活不就是这样吗?而这个女子什么都不奢望,只求能得到一颗真心,才把皮画得更好一点儿,不就是为了取悦王生吗?因为女子早知王生是已婚之人,她也是过来人,无须解释,她一切明了。在古代,她的身份是妾,类似于我们说的婚外情。她突然得到了人世的温馨,但这温馨又转瞬即逝。这样的“画皮”仅仅是为了得到一颗真心,但女子是用生命的代价换取的。这是多么令人可怜的高贵,这种可怜的高贵就在我们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之中,极具普遍性,这不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吗?这是《画皮》中带给读者的最经典的思考之一。
王生妻子看到丈夫的心被挖走之后,惊声尖叫后,出门去找道士。道士说这个女鬼他可以收拾,但是有一个问题,王生是救不活的。道士跟随陈氏回家后,手起刀落,收服女鬼。陈氏见女鬼消亡,赶紧磕头央求道士赶紧救救她的丈夫。道士表示救不活他,外面有一个睡在黄土堆上的乞丐能救活他。陈氏赶紧去找这个乞丐。乞丐哈哈大笑,讲了这么句话:“人尽夫也,活之何为?”意思是说,是个男子就可以当丈夫,你救他干什么?这句话对于封建时代的女子来说是莫大的侮辱。陈氏仍继续央求,乞丐便拿起拐杖敲打陈氏,陈氏仍不起身继续哀求。“乞人咯痰唾盈把,举向陈吻曰:‘食之!’”陈氏为了救丈夫强忍着巨大的恶心,吞下了这一口黏痰。乞丐哈哈大笑曰:“佳人爱我哉!”然而,乞丐说完转身却不见踪迹。先是语言羞辱,后是肉体折磨,又是精神凌辱,此时陈氏多难过、多痛苦。回到家后,“既悼亡夫之惨,又悔食唾之羞”,陈氏既痛悼丈夫的惨死,又悔恨街上吃了那口恶心的黏痰。正在这内心苦痛至极、号啕欲死之际,之前吞咽的脏东西实在咽不下去,嗷的一声吐了出来,正好吐在了王生的胸腔里。陈氏再一看,发现这竟是鲜活的人心,正在丈夫的胸腔内突突跳动,而且还冒着腾腾热气。王生竟就此复活了。《画皮》故事结束。
二、现代意义的多重解读
我小时候读的《画皮》的故事,总觉得是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我们仔细想一想,这是大团圆吗?女鬼被收服了,王生复活了。男主人公外表虽然复活了,但他的心脏是乞丐吐出来的一口痰。现实生活中,太多华丽的外表掩盖了肮脏的心。而那女鬼将那王生的胸膛直接撕裂来看,展示的是“心”的真实。抛开女鬼,从读者的角度看王生的“心”,那应该是多么肮脏。是的,是黏痰,还是乞丐的黏痰。
《画皮》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解读。道士本不想杀女鬼,想必知道她的身世,不然有什么理由让女鬼危害生灵。王生求助道士时,道士说的“此物亦良苦”中的“良苦”,是对女鬼的评价,他又言:“予亦不忍伤其生。”只是后来女鬼害人性命,他才将其收服。道士的内心是明了的,女鬼为了得其真心,不惜搭上自己生命,连道士都不忍心取她性命,她却为了真心,什么都不顾了。而王生是咎由自取,可救可不救。道士仍给陈氏指了挽救丈夫的路,让她去找一个乞丐。道士和乞丐又何尝不是一个人呢?细想,陈氏遭受乞丐的语言、肉体、精神的折磨和羞辱,那应该是考验陈氏的真心。一个女鬼为了得到真心,宁愿搭上自己的性命。陈氏若受不了这般侮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难道人还不如女鬼吗?而世间哪里有鬼,故事中的鬼,应该是一个影子,渴望一颗心的影子,它曾经是多少人童年的阴影。今天看来,它应该是王生的另一个自己,“我觉得像做了一场梦”。梦是一种潜意识,是因为心里有欲望和冲动。王生说的做了一场梦,也许是对自己的反省。在1966版《画皮》结尾处,并没有吃痰唾这一情节,而是道士在收服女鬼后,捡画皮时发现的心。王生最后得救是因他的“心没有死绝”。“心没有死绝”,多令人深思。
在现实生活中,人有时候会丢掉自己的心,明明了解对方的意图,却只因对方化了浓妆,被误认为是美女,从而迷失了自我。明明是真诚的忠告,却被当作欺骗。《画皮》中的王生“贪婪地追求和占有美色,自己的妻子也将会去舔吃别人的痰唾,而且是甘愿这样做”。贪婪也是人性的一个显著弱点,唯有通过灵魂的净化,才能抵御那些身边的“画皮”。我们常从善的角度、从美的方向,对待世事,但是假的东西,往往容易使我们接受,因为美好的底色往往是悲剧,它更接近事物的现实。我们的意志与智慧本应引领我们向美好的方向发展,使我们不相信乃至拒绝接受坏事,认为这些危害与己无关,这既是潜意识的驱使,也让我们更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然而,正是这种盲目自信,导致了“画皮”现象的越来越多且生命力顽强。
陈氏在《画皮》中作为配角出现,展现出作品的另一个主题,也是易于忽视的主题。陈氏在闹市上找到乞丐,见其“鼻涕三尺,秽不可近”。可见,陈氏所求之人竟是满身粪便、臭气扑鼻,但陈氏为救丈夫吃下乞丐的黏痰,而且她是甘愿那样做,恰是人性本能的流露。中国传统女性的宽容、善良的美显然占据了作品的另一层主题,包括本文中女鬼的“良苦”和对“真心”的渴望,还有那黏痰化成的心,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也一直存在吗?
我觉得《画皮》的主题不能仅仅归于贪婪上,而应从人性的本真和当下的迷失中去寻找。我们看问题常带有艺术的情绪,总是认为从远处看风景,容易发现诗的意境,一切“溶在自然的一片美的形象里”,而缺乏改变看问题的心理习惯的勇气。转换角度看问题是我们审美的心理方面的积极因素和条件,做不到“‘心理距离’‘静观’,则构成审美的消极条件”。《画皮》的主题应该是多层次的,而关于人的“本真的心、善良和美”,那才是永恒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