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笛20世纪30年代诗歌的现代体验
作者: 宫宇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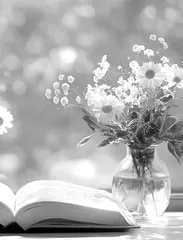
辛笛在时代气息浓厚的“现代派”诗艺的影响之下,他的现代眼光层层摄入到其个人的诗歌创作当中。20世纪30年代是辛笛创作的初期阶段,其间形成的《珠贝篇》《异域篇》是他正式踏入诗坛的有力证明。在这两部诗集里,辛笛利用带有接续性和广阔性的时空观念,塑造了一个自我意识逐步实现转型的抒情主体,使其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诗歌极具现代实践意味与审美体验,成为遗留在中国诗歌“潮汐”下的对新诗创作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的一枚枚“珠贝”。
1928年,高一的辛笛以一民为笔名,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白话诗《蛙声》,自此开始了新诗创作的生涯。现代主义对辛笛的诗歌创作具有贯穿作用,助推着诗人情感的抒发和诗美的构造。首先,“现代派”对辛笛有着“启蒙”之功。辛笛称,在上海出版的《现代》杂志是他爱读的杂志之一,上面发表的大多是中国的现代派诗歌。其次,辛笛在异域求学时也与艾略特、奥登、史本德等诗人来往,深受现代主义和西方诗艺的影响与熏陶,开阔了辛笛的现代视域,令他早期的诗艺探索更为多样化。辛笛的诗每写至激昂之处就会显得气势不足,如唐湜称其诗歌“单薄与倩巧”(王圣思《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但正因有“艺术中那令人沉醉痴迷、心神震撼的东西”(王一川《意义的瞬间生成》)的体验所在,才使其诗风的过渡自然而顺畅。
一、现代化的时空观念
戴维·哈维曾说:“空间和时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文化研究》)人类不可脱离时间和空间进行思考。波德莱尔对现代性定义是“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来看,该理论阐述了一种平衡且矛盾的存在形态,即瞬时性与恒远性,而因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区分性而致时间的流动必定伴随着相应的空间转变。在辛笛的时空观念中,时间维度上强调其延续性与动态变化的特征,空间维度上则关注变迁过程的历史回溯与未来前瞻。
(一)时间的绵延与变奏
时间流动不居,其中兼存着瞬间与永恒,而瞬间与永恒交织的体验一直存在于辛笛的诗歌中。《夜别》夹杂着诗人在绵延的时间之下,对于离别的体验。《潭柘》用“灵魂的小语”象征着短暂,而与永恒相并肩的则是“潭光和柘”,野花与松树的季节更替衬托出山的永在,这一时间长度的对比体现辛笛想要成为一个对自然充满热爱的“山中人”的渴望。
在多样的时间变奏中,诗人用慢动作拉长时间体验,“漫天的星光下/草垂垂地白了”(辛笛《款步口占》);也体验着时间促逝,《秋思》内四季的转换如眨眼般闪逝,“思念的话语”也融合于诗人的寂寞心境中,随着时间和行人走远了。
一切拥有生命的事物都具有短暂性质,而宇宙则永恒地扎根于无来无去的时间中。关于永恒的指认,辛笛将其称为圆圈,这种体会全数体现在辛笛的成名作《航》中。在回环往复的变与不变的统一中,时间实现了永恒和不朽,连缀成“我们”烟水般茫茫的生命的背景,“将生命的茫茫/脱卸与茫茫的烟水”,将短时存有的肉身投掷于伟大而无限的永恒中,表现诗人对生命的思考。《航》的前一篇《生涯》也是对于循环时间的描摹,一个“航不出”,另一个“画不就”,都带有长远追随的意味,昭示着时间的恒变恒久,是“罗马的指针不曾静止/螺旋旋不尽刻板的轮回”(辛笛《对照》)。从全诗来看,“生涯”一词未免位重而言轻,辛笛对于生命的体悟更多地发生于美学上,而对于人性、现实等方面的挖掘深度仍显不足。
(二)空间的回眸与展望
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里希所说:“存在,就意味着拥有空间。每一个存在物都努力要为自己提供并保持空间,只有拥有独立的生存空间,才能拥有独立感。”(《蒂里希选集》)《珠贝集》写于辛笛在清华园求学阶段,这一时期诗人的笔法兼具现代派和西方现代主义浪漫因子,所状写的梦境、印象、离别等所在的空间基本也都存具着浓烈的抒情色彩。辛笛经常把自己的思绪寄托在“水”“海”当中而非实际的土地上,如《印象》《航》《款步口占》《告别》等,足见诗人的空间追求。“水”和“海”本是流动无静的,诗人在其诗歌空间中将如蚁般的人放入庞大的海与水中,苍茫的视域之下更能回眸人情感的变迭与存在本体的意义,在动与静内寻求有关生命永恒意义的诗性思考。
辛笛于1936年远离祖国赴英国留学,这一经历使得他建构空间的规格扩大。在《异域集》中,抒情小诗的分量减少,增添了诗人对于家国等现实问题的考量,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个人的幽哀气质。辛笛这一时期的诗歌多将脚步落实在土地上,构筑了一个实在的、沉思的空间。《欧战休战纪念日所见》中从历史故事中生出的现实感怀、《寄意》将“碎裂的怀想”撒播于悠远无限的田原上。种种对于乡土的希望与理想、中西都市对比之中的个人的悲悯与感愤,促成了一个个兼具反思与思念的“乌托邦”空间的建成。同时,诗人并未被异域风情所迷惑,而是仍旧忧思国家。空间的转向促使空间性、生存性和体验性紧紧融为一体,揭示了空间所具有的内在意蕴,令“文学审美创造获得了无限性、想象性和超越性。空间体验敞开了文学体验的无限性,作家在对无限宇宙空间的体验中,摆脱了有限空间的限制,使其对于宇宙人生,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这便为辛笛20世纪30年代的诗歌创作注入了不同的活力。
总而述之,“中国诗人往往会在整体上寻求时间的绵延性,而在片断上寻求空间的并存性,这样就有利于创造思维(时—空间)的艺术境界,既具情愫绵绵之长,又有明心见性之优,足以容纳东方智慧和沧海桑田,把人们从皎然在目之视镜推向清空邈远之心境”(孙益波《诗性智慧:瞬间印象中的生命主体—论辛笛诗歌中的抒情自我形象》)。
二、现代化的自我意识
诗歌重在自我意识的呈现。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提到:“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他在四周的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并且给予它们以一定形象的表现。”(普列汉若夫《论艺术—没有地址信的信》)辛笛在20世纪30年代的诗歌中,具有三个存在连续性表征变化的自我意识,富有强烈的个性色彩与现代意识。
(一)“心沉向苍茫的海”—感伤自我
辛笛初涉创作时,常常将日常生活中的片段、镜头以及新鲜的感受收纳其中,并将其转化为表达个性和思维的感官体验。在《弦梦》中,“静的长街上”突兀地出现“繁促的三弦响”,在对立的景致中失落了光明的“他”来了,来去之间只留下“绿的梦/怅惜的梦”。“他”一定程度上是诗人自我的投射。无论光明如何在“他”身边照射,却照不亮“他”的眼睛,反映出诗人的迷茫。诗人用第三视角旁观“他”的同时也是在审视自我,“怅惜原是他的本分”抒发了感伤的无可回避。“他”或诗人自我并非完全抛却希望与积极,而是在怅惜的梦前添加了“绿”这一修饰词,用“绿”加以修饰足见一抹渴求的色调。
在《印象》中,诗人的意识如同小溪一般流动,自然地将过去的记忆、当下的感受与对未来的想象有机地联结起来,自此将人生的种种印象由感性升华为知性,即生命如水般肆意流淌。同时,诗歌营造出一种朦胧而迷离的氛围,这种氛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外界环境的复杂与不确定性,因此只得在梦中寻求一种放松与安稳,但也难脱伤感。诗人的自我发掘未曾跳离怅然若失的总体声调,好似《夜别》中“心沉向苍茫的海了”所阐述的失重感。在20世纪30年代,传统思想与“五四”新思想、西方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中国知识分子深知中国的封闭落后,并于现实的重压之下呼唤文明的到来,辛笛的诗歌于此时饱含着挣扎的无措和奋进的寂寞。
(二)“不再是贝什的珠泪”—觉醒自我
20世纪30年代后期,现实环境已经使知识分子的心态或写作风格发生变化。之所以将《垂死的城》视作其诗风的转折点,共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现实因素的浸透。《垂死的城》的落款为“一九三六年夏别去北平”,这一时间标记赋予作品鲜明的历史背景。诗人在北平的生活经历使其敏锐捕捉到时代变迁中的紧张氛围。诗中写道:“风景与人物都会因空气的腐朽而变的/暴风雨前这一刻历史性的宁静。”通过对“历史性的宁静”的描绘,诗歌表现出对未发生变局的隐约预感。对外部环境的感知进一步加深了内心的焦虑,并转化为诗歌中对现实的深刻书写与审视。二是向“现代派”诗学的告别。在诗歌结尾处,诗人称“从今不再是贝什的珠泪/遗落在此城中”。诗人想要表明的是,即将坍塌的不仅是北平,还有之前所过的“轻鸽的梦”的生活,以及建立在此生活之上的“一眼看着美幻,一眼看着世界”(辛笛《夜读书记》)的诗学。这首《垂死的城》是诗人离去一个阶段的历史时期和诗学追求的标志,并将之前的一切随着即将陷落的北平而一同“抛弃”。同时,其也具有一定的指涉性,象征着诗人提前向北平这一地理位置所容纳或代表的“现代派”诗学进行告别,隐含着诗人现实意识的觉醒。
在北平之外,辛笛写的第一首诗作是《挽歌》,诗歌中的“自我”是一个孤独且自信的芦苇形象。帕斯卡《思想录》称“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苇草”,在这首诗中辛笛对自身的认定便是如此。“我”是寂寞的,“我”又是自信的,“我”相信智慧用水写成。因此,《挽歌》实际上是诗人告别过去重新出发的序曲。值得注意的是,《异域篇》中第二人称的使用明显增多,指明了诗人自我意识的对象化追随,也增加了对话式书写,自省的同时又多了一份寻求确定性的考虑。
(三)“一颗怀旧的心”—反思自我
觉醒自我的生成,标志着现实主义在辛笛的诗内苏醒。其20世纪30年代后期所创写的诗歌,无不带有一定的现实主义风格以进行反思。在《欧战休战纪念日时所见》中,诗人诉说着20世纪“不幸的一群”的故事,诗中的“自我”发出慨叹,以对历史的反思,以相对抗的形容词陈述着对灾难意义的寻觅,“阴霾里会再来一次响雷”,这声“响雷”便是新的突围与转变。结尾句“可怜的泥土之子”含有感时伤事的意味,“泥土之子”的多重指向也增添了诗人对于自我、民族、国家的审慎与思考。
《对照》以多重视角的转换与对比,构建了具有张力的诗意世界。“俯与仰一生世”“南北”“东与西 远与近”等对照意象揭示了空间层面的巨大反差,而诗人通过自己设立的距离,生出“白手”的思考。根据辛笛的女儿王圣思的解读,辛笛在创作过程中或已关注到“白手”象征着未能充分付出劳动或实践价值的个体。这一意象不仅是诗人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反思,也是他在个人经历中对责任与意义的探索同追问。因此,在爱丁堡留学期间,辛笛积极参与了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抗战募捐等社会实践活动。在《手掌》中,诗人以新鲜的手掌意象批评身为知识分子的纤弱。另在《巴黎旅意》的书写中,辛笛主要通过法国看似繁盛的外貌联想到其“败絮其中”的实际状况,在反思之中转向积极入世的心态。
诗人从感伤,走至觉醒,再逐渐进行反思,这三个诗歌坐标全然展现了其20世纪30年代自我思想意识上的跨步与转变。本节的小标题是《门外》的一句诗,《门外》虽已被认定为爱情诗,但其中远道而来的访旧者在某种程度上与诗人当时的现实情状或思想内核相一致,访旧者的“怀旧的心”,正是辛笛作为漂泊学子的孤寂之心,还体现着诗人怀旧于原本的诗学艺术。诗人于反思之中并未完全忘却离国之前所追求的现代性诗歌艺术,反而实现了更为巧妙的融合。于是,辛笛在现代自我的建立与重建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的是“怀旧之心”。
如辛笛在诗歌创作70年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所述,他青年时代体会“我感觉我在”更真切。辛笛20世纪30年代的诗句以语言文字符号为媒介,以美幻与现实为主线,以凸显自我意识及其转变为内涵,在动态与静态之中创造了一个符号化的时空。虽然辛笛早期的诗被认为规格狭小,辛笛本人也自谦其幼稚而感伤,但正是有了这两个诗篇的积淀,其现代性体验的种种在初期得以更恰当地安放,也为他后期诗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