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闲情赋》中体现的文学思想之我见
作者: 吴海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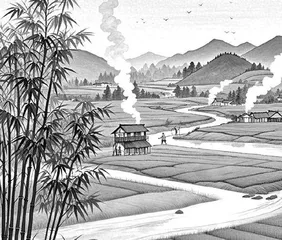
陶渊明,这位生活在晋宋交替时期的诗人,以其高尚的人格闻名于世。他的诗歌语言清新自然,于东晋时期独树一帜。其诗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不经意的描绘中展现了诗人内心的宁静与满足。陶渊明对心目中的桃花源进行了细致描绘,为历代文人打造了一个心灵的避风港。无数吟咏陶渊明的诗作和模仿其文风的作品,成为文人表达失意情绪、寻找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
陶渊明的文学价值得以彰显,与南朝梁时期的昭明太子萧统的慧眼识才密不可分。萧统搜集并编纂了《陶渊明集》,并为之撰写序言和传记,为后世研究陶渊明开启了先河。在《陶渊明集序》中,萧统表达了对陶渊明作品的热爱与对其品德的仰慕:“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同时,他指出《闲情赋》的不足:“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在此之前,陶诗虽有流传,但未有系统的整理;虽有颂扬,却未有详细的记载。至于萧统为何仅对《闲情赋》提出批评,以及这寥寥数语为何在后世引起广泛讨论,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然而不可否认,《闲情赋》作为陶渊明众多文学作品中的一篇,其独特性凸显了其在陶渊明文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分析作品所体现的文学思想首先要了解作品,因此我们需要对《闲情赋》一文进行细致分析。
一、千古华丽之篇,意欲讽谏之赋—《闲情赋》赏析
分析一篇作品首先要细致理解它的主旨,从梁至今对《闲情赋》主题及内涵的争论主要分为三种说法:爱情说、政治寄情说和守礼说。前人在论述此三种说法时或多或少都缺少关键例证,但这也恰恰说明此作意蕴深厚,非一语可以见之。此时拿出文章本身和作者自己阐述的创作思路来讨论问题就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接下来将结合陶渊明个人生平来讨论。
提到陶渊明,就不得不谈其高风亮节的品格和归隐山林、悠哉自得的志趣,在西晋文学逐渐雕琢华丽、趋于绮靡的文风笼罩之下,脱颖而出的便是陶渊明之诗,其诗兼备质朴语言与真情实感的大胆流露,而又不乏哲思与社会批判,独成一派,开先河于田园诗。但他在世时作品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当时的文坛偏好骈文和俪辞,对于陶作中质朴直白的感情表达并不看重,这从某种程度上也使陶渊明的形象更加真实可感,对理解陶作有一定帮助。
陶渊明以“闲情”为题,使我们从题目开始就略观到作者闲逸达观之心境。这个标题是很有韵味的,后来有人说此赋体现了宋代盛行的“闲情文化”。对于闲情文化的定义,韦凤娟认为,它的本质意义在于:追求人生的审美境界,把寻常的人生提炼为高雅脱俗的生活艺术,把寻常的“人境”点化为充满诗情画意的境界,在寻常的生活中获得巨大的精神乐趣和审美享受。笔者理解为既要有画作之美,又要以此为基础描绘生活之美,最终上升到高尚情操之人至真至美的审美境界。
那么简要来看内容,此赋通过赞美一名女子“瑰逸”,寄寓了陶渊明的政治理想和精神追求。陶渊明一向擅长运用丰富的意象和比喻,赋予作品鲜明的画面感,如“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把女子的多愁善感之情描绘得缠绵悱恻,充斥着女子特有的阴柔美,让人心生怜爱之余,颇感陶赋之技法高超。以花草喻美人,很难不让我们想起屈原《离骚》中的“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等句。这里陶渊明显然受屈作之影响,不过是表述得更加含蓄,塑造出一位高洁美丽的女子,用来自比而已。又如“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褰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这样的句子,陶渊明在欣赏女子之美之际,也慨叹时光易逝,人生漫长,同时表达了自己坚守道德信念、坚定追求理想的意愿。综上所述,是陶渊明使闲情文化得到最完美、最生动的表现形式。欣赏此赋,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拘泥于对美丽女子的告白,而看到背后的深意。
通过对赋文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单说其思想情感的话,其实它通篇更加倾向于自然情感的流露,而对于陶渊明自己在《闲情赋序》中写到的“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的初心是不尽相符的。同时,这首赋作模仿楚辞及前人作品痕迹较重,个人写作特点不太突出。袁行霈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此赋写作于陶渊明十九岁,他正值青年时。笔者比较倾向于这一考究,青年陶渊明才华横溢,写作风格独特但仍未成熟,导致作品最后呈现出的效果不尽合初心,这也是合理的。一个没有认识到官场险恶的人的讽谏之词,的确很难切合实际。但这仍然不能掩盖《闲情赋》的光辉。此作想象奇特,浑然天成,实可谓千古华丽之名篇也。
二、《闲情赋》中体现的文学思想
在《闲情赋》中,陶渊明通过对个人情感体验的深入挖掘,展现了对自由与自然生活状态的向往。他以自己的情感体验为出发点,表达出对人生短暂、时光易逝的感慨,既在赋中表达了对传统儒家伦理的尊重,又不遗余力地追求个人精神的自由。这种矛盾的体现,正是陶渊明文学思想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所在。
(一)情感体验的深度探索与反思
陶渊明在其众多作品中,巧妙地运用了对女子“瑰逸”特质的赞美与爱慕,并以此作为媒介向我们展示了他对理想爱情的深情告白。这种告白并不仅仅是对男女之间爱情的单纯渴望,而是深深植根于对“美”的追求和欣赏之上,即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美的事物因其特质被人们所追求,这是人们一致达成的共识,然而,所有美好之物均无法恒久存续,上至大川大河,下至美人容貌,此乃美的珍贵、稀有性的体现,这种珍贵就在于美的易逝性。因此,赋中发出感慨:“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美人迟暮的忧虑与悲剧感再次浮现,成为本赋的情感基调。
在求美而不得的失意之中,陶渊明将自己复杂的情感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以一种曲折而隐蔽的方式,在其赋作中得以表达。因此,陶渊明在写作中“一方面很自然地出现了把主观感情投射到客体中去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把客观情调吸收到主体中来的倾向”(朱光潜《悲剧心理学》)。这两种倾向纵横交织,陶渊明急切地想要将自己对爱与美的渴望宣泄出来。从其写作手法上我们可以看出,他更倾向于随性洒脱地运用各种大胆的意象,而不是过分考虑如何凸显个人的写作特色。正是在这种创作态度的驱动下,《闲情赋》应运而生,这部作品深刻地体现了作者对自身情感体验的深度探索与反思。
(二)对人生短暂、时光易逝的感慨
自古以来,生命与死亡始终是人们无法绕开的重要议题。陶渊明作为一名深受儒佛道三家思想熏陶的诗人,对生死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与体验,最终确立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三首》)的生死观。在陶渊明的诗中,他吟唱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这表明陶渊明年轻时怀有远大志向,渴望成就一番大业。正是这份壮志,激励他不断尝试出仕。
青年陶渊明心有壮志,更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理想,但其此时就已经表现出了超乎同龄人的深沉心境,对人生短暂的感慨直白而沉痛。“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这是《闲情赋》中直观抒发陶渊明对人生短暂、时光易逝的感慨的几句,以艺术的手法,通过“求女不遇”的传统模式,隐喻性地表达了作者的全部人生体验和历史经验,以其浓郁的悲剧感蕴含了在无情时间摧折下美的必然陨灭的象喻意义。尤其是前二句,极具表现力地体现了陶渊明在情感与理智间的挣扎,表达了他对于人生短暂如沧海一粟的感慨。《闲情赋》这部作品不仅加深了他对“不遇”主题的诗意哲学探索,也象征性地表达了他悲剧性生活经历的诗意。
此赋诞生于特定的政治和心理环境,内含丰富的内涵和象征意义。它不仅展现了陶渊明对时代“不遇”状况的寓言式解读,也表达了他对美好事物短暂和生命易逝的深切忧虑。其主题复杂而深邃,思想上的痛苦连绵不断且沉重。这篇充满文学隐喻的寓言赋,汲取并超越了传统求女模式,赋予了更高的哲学品质,其艺术成就超越了前人的同类作品。
(三)儒家伦理与个人精神自由追求的冲突与平衡
陶渊明的创作显然是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其大部分作品都遵守礼制、不逾矩,但在《闲情赋》中,我们不得不特别提及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十愿十悲”这一段落。这几句诗在整篇赋中显得尤为突出,充分展现了“赋”这一文学体裁的独特魅力。陶渊明通过运用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巧妙地采用了连续十个“愿”与“悲”的句式,将自己幻化为各种物件,以一种如泣如诉、缠绵悱恻的语气,委婉地表达了对理想中美人的深切思念。这种由“愿”而生的“悲”,不仅仅是因为佳人难以陪伴在身旁,更深层次的是对时光易逝、乐极生悲、理想难以达成的哀叹。这种情感的表达,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色,即不受外界束缚,只在强烈情感的冲击下,发出真挚而直接的告白。这种告白方式,使得《闲情赋》在众多赋作中独树一帜,散发出独特的光彩。从这“十愿十悲”的内容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陶渊明并没有刻意地与主流文风保持距离。他所采用的偏向骈文的格式和句法,可以视为一次文学创作上的大胆尝试。这种尝试,与陶渊明所受的儒家思想影响不无关系。正如他那炽热的告白并未改变整首赋的悲情基调一样,他的创作最终还是受到了礼制的限制,不得不以一种守礼的方式草草结束,这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背景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三、浅谈《闲情赋》之评价种种
陶渊明自述的写作思路中交代了自己是在“园闾多暇”的时候进行写作的,可以看出陶渊明在创作时比较随性自然,这种心态也符合他“悠然见南山”的本性。《闲情赋》完美地诠释了“闲情”的精神内核,且在表情达意上做得十分完美,只不过重于表“情”而讽谏不足,这也是合理的,作品写作时的思路和最终完工后的成效并不一定总是一致的。钱锺书在《管锥编》详细谈到过这一点:“昭明何尝不识赋题之意?唯识题意,故言作者之宗旨非即作品之成效,其谓‘卒无讽谏’,正对陶渊明自称‘有助讽谏’而发,其引扬雄语,正谓题之意为‘闲情’,而赋之用不免于‘闲情’,旨欲‘讽’而效反‘劝’耳。”而萧统在整理陶渊明作品时批评《闲情赋》“卒无讽谏”,认为这样不合本心的作品不符合圣人陶渊明的形象,如美玉上的微小瑕疵,也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但陶渊明有没有违背自己的本心,笔者是持否定态度的。对美的追求是人类的本性,而陶渊明在社会的重压之下还能把自己的情思表露得淋漓尽致,这正符合了他儒道融合的思想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作风。总之,萧统做出这样的评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对陶渊明极为推崇,对陶渊明“期望太高,在别人无妨的作品,在陶渊明就成为瑕疵了”,大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感。虽然萧统留有余地,只是说“微瑕”,但他也不曾料想陶渊明的文学功绩会在后世有这样深的影响,也没有想到陶渊明的作品会一直流传至今被广泛讨论。但短短几字能对后来的文学界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学作品的解读往往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本文通过赏析《闲情赋》,试图揭示陶渊明在此赋中所蕴含的文学思想,如情感体验的深度探索与反思,对人生短暂、时光易逝的感慨,以及儒家伦理与个人精神自由追求的冲突与平衡,以及这些思想如何与他的生活经历和哲学观念相互映照。尽管萧统的评价带有个人情感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陶渊明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它们不仅反映了作者的个性和时代特征,也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和思考空间。通过对《闲情赋》的深入分析,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的文学追求和精神世界,以及他如何在文学创作中坚持自我,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