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滕泰:应对关税冲击,须激活14亿人超大市场
作者: 何子维
34%……50%……104%……125%……145%……245%……
近日一睁眼,满屏都是中美关税税率创新高。
特朗普政府喜怒无常的政策,高举的关税大棒,不断给世界局势不确定性增添新的注释。
对应这种不确定性,在国内,提振消费已成共识,成为了2025年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底层逻辑。被人津津乐道的西子湖畔“六小龙”,则在科技突飞猛进的蓝色大洋上扬起风帆,激荡着2025年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信心。
然则我们仍然要思考与追问,当关税壁垒与技术封锁成为常态时,该怎么应对?中国经济的突破口在哪?经济发力的方向会有什么变化?为此,南风窗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他表示,面对美国关税之战,我们不仅要放弃幻想,更要加强修炼内功。
在发展策略上,滕泰认为,我们应当继续以强有力的措施释放消费动能。只要对内所有的措施都花在提振消费、改善民生方向,激活14亿人的超大市场,就能对冲关税战的影响,立于不败之地。
过度投资挤占了居民消费?
南风窗:近年来,关于如何提振经济,学界有不同观点。有人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有人倾向于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你则呼吁把提振消费放在首位。如今,“提振消费”被放在2025年政府工作任务之首,与你的观点不谋而合。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做出了这个判断?
滕泰:对促消费的呼吁始于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2020年以前,中国消费占比低、内需不足的矛盾虽然早就存在,但并不突出。2020年疫情来临,中西方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模式,使中国的这一矛盾进一步被放大。
当时,中国把力量用在恢复生产、恢复供应链、扩大投资等方面,效果确实立竿见影。中国2020年的GDP实现了正增长,但81%由投资贡献,消费贡献率为负的0.5%。
相比之下,欧美等地区刺激需求端,采用大规模财政发钱,叠加零利率等政策,出现了需求旺盛、供给缺乏的局面。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中国填补了全球供给缺口。一时间,“中国供给平抑了全球需求”的特殊经济平衡出现了。
而特殊时期一旦过去,就会为后面进一步的供给过剩和总需求不足埋下隐患。到了2022年下半年,随着海外供应链逐步复苏,我国出口订单开始流失。加上逆全球化抬头、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等,国内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逐渐激化。
这正是我们持续呼吁转向消费驱动的现实依据。如今,提振消费被放在九大任务之首,可以说,我们从学术上也贡献了一份微薄的力量。政府工作报告中“投资于人”等价值主张,也能在《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这本书中找到相关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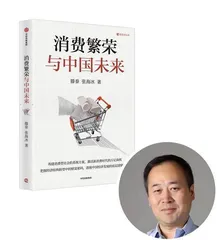
南风窗:一如你的新书书名《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为什么说消费繁荣而不是投资繁荣关乎未来?今天,我们是要以过去抓投资的力度去抓消费吗?
滕泰:在经济起飞阶段多搞一点投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每一块钱的投资不仅有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通常都有几倍的乘数效应。但是在工业化后期和城镇化后期还保持那么高的投资率,势必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比如现在的一线城市,还能建几个机场?还能修几条高速?还能盖多少大楼和厂房?房地产、厂房设备和基础设施都出现了过剩,继续扩大投资,不仅微观经济效益下滑,宏观上也循环不起来,乃至可能落入“过度投资陷阱”。
宏观消费压抑和宏观过度投资陷阱是孪生的,当财政资金不断地被投入各种低经济回报、低社会效益的项目,不仅挤占了消费,而且根据相关测算,当前我们财政资金用于投资的乘数效应是1.06倍,个别省份甚至小于1,而同样的财政资金用来发消费补贴,其乘数效应是3倍以上。
这意味着,如果把每年10万亿元的低效投资变成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话,就会产生30万亿元的总需求,那么扩大内需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南风窗:在这种背景下,部分投资仍在扩张,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滕泰:投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行政主导性投资占比过高是重要原因之一。当前,我们决策部门仍然是投资驱动的体制,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抓手也是招商引资、搞基础设施投资等。
让原来搞招商引资、搞基建的人,转去推动消费,就要从认知转变,到机制转变,再到实践变化,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既要深化投资驱动的体制改革,也要建设消费驱动的体制,最终从建设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型。
具体而言,就是将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从增加基建、补贴生产、补贴出口,尽快转向社保、医疗等民生支持,或直接补贴居民消费。跨过这个坎,我们才能实现消费繁荣。
关键是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南风窗:今年3月16日发布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将“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放在了首位。你也明确指出,抑制中国消费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较低。为什么可支配收入不够高是抑制消费的主要原因?
滕泰:短期来看,消费是收入和利率的函数。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增长;利率下降,储蓄就减少,消费就增加。这两个经济学变量不改变,就想让消费增加,最后一定是南辕北辙。
过去我们认为,消费是慢变量,要促进必须先提高就业。但现在观念发生了彻底转变,我们开始从收入端发力去促进消费。
但必须指出的是,不能一提收入的增加,就要企业提高工资待遇,这是首先要排除的观念。原因很简单,工资和劳务收入是企业成本的一部分,由市场决定。如果在企业利润没有增加的前提下,直接干预企业提高工资,那么,企业第一反应必然是减少雇佣。
因此,先得有一个“外力”,增加非工资居民收入,再把消费搞上去,让市场活起来,企业才能有利润、有就业、有收入。所以,收入是启动消费、激活市场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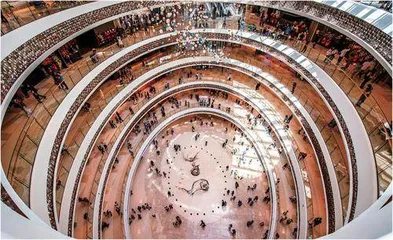
南风窗:从收入端着手的话,短期里我们看到,国家增加了消费补贴,推出了“以旧换新”等政策。一次性收入对经济循环,到底有多大的促进作用,能持续吗?
滕泰:短期与消费相关的收入变量中,一次性发放消费补贴是最有效的“外力”之一。
宏观来看,消费补贴的杠杆倍数,城市大概是3倍以上,农村为5倍以上,笼统地说就是3倍到5倍的宏观需求乘数。
微观来看,就像经典的“萧条小镇”案例一样,这种“外力”是繁荣市场、促进企业消费的最重要切入点—小镇里,旅馆没有人住,屠夫的猪肉没有人买,理发馆没有人理发,裁缝的衣服卖不出去……一个旅人拿着100块钱去旅馆住宿,旅馆店主把赚来的100块钱给了屠夫买猪肉,屠夫把赚来的100块钱用来理发,理发师又用100块钱买了衣服……于是,萧条的小镇活了。
这就是在特定条件下,一次性收入对经济循环的作用。
老百姓用自己挣的钱进行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很低,而政府发放几万亿元的通用消费券,不是“打水漂”,而是百分之百转为了消费。不过前提是,政府筹集到足够规模的资金。若仅有一两千亿,效果并不明显。
南风窗:那么,多大力度的补贴才算合理呢?资金的规模怎么衡量?
滕泰:考虑到扩大内需的迫切性,最少1.5万亿元的补贴,人均才能达到约1000元。如果重点补贴中低收入者,效果则更大,每人补贴2000元,那么大约需要3万亿元的资金规模。按照3倍的乘数效应计算,3万亿元消费补贴会带来将近10万亿元的经济增加。
从货币方面打开空间、解放思想
南风窗:除了发钱,还有什么方式?
滕泰:增加财产性收入。它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仅次于一次性消费补贴。
人们买的房子价格涨了,人们投的股票价值涨了,人们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自然就会增强。所以,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专项行动都明确提出,要稳住楼市、股市,实际上就是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放眼全球消费旺盛的地方,其股市正是呈现出上涨的趋势。怎么促进股市繁荣呢?货币政策应该发挥主要作用。
南风窗:谈及财产性收入,多是指楼市、股市,但这类收入主要是针对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对于广大的低收入群体,有什么渠道可以拓宽他们的收入?
滕泰:提高中国人的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对消费也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一般公共预算中用于养老的支出仅占3%左右,即便加上社保基金的支出,两者合计也不足10%。这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美国约18%、日本超20%、欧洲国家在20%到30%之间。
因此,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的比例,从而增加我国社保覆盖水平。比如,再增加划转5%—10%的国有股权到社保基金,筹集5万亿至10万亿元资金,确保农村老人每月养老金能达到500元至1000元,他们还会因为担忧养老问题而不敢消费吗?
南风窗:刚才提到,要做到这些,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首次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连续实施了14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怎么理解?
滕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从总量上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资扩张,中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如今,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峰阶段过后,拉动经济增长不能再继续依靠投资,而是要投资与消费并重,并且更加重视消费。那么,货币政策亟需从总量上解放思想,也需对传导机制作相应的深化改革。
促消费,货币政策应该发力,且其发力的目标顺序应当是,把利率、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资产市场价格等影响国内经济全局的经济指标,放在汇率等外部指标前面。
要知道,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汇率影响的只是少数进出口部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为了保经济增长而牺牲汇率,日本就是参考,汇率贬值越多,消费越旺盛,甚至各国人都争相去日本消费,连巴菲特都去日本投资。
另一个影响货币政策的重要观念是认为,降息会影响银行利差,进而影响银行体系稳定,增加金融风险。由于中国直接融资比重较高,银行体系的安全性自然非常重要,但确保银行体系安全,不等于要保证银行的利差收入和盈利。
在几百年的全球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会在经济衰退时为了保住银行盈利而牺牲经济。当各行各业盈利下降时,商业银行的盈利下降甚至亏损都是正常现象,等经济复苏后,银行自然会盈利。
对当前中国经济而言,如果我们在降息方面打开空间,比如降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就会增加1.5万亿元、家庭部门的利息支出就会减少8000亿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成本也会减少1万亿元以上……这时的货币政策是不是就推动了“政府培育消费,消费激活市场,市场引领企业,企业扩大投资”的良性经济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