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说 | 在大西南的山岭之间,发现浓缩时间进程的戏剧性时刻
作者:邢海洋大家好,我是邢海洋,这期封面故事是我写的《行走云贵川:近代之前的变革》。
说来话长,前年写长江的时候,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中原人“殖民”长江流域,经历了从东晋到南宋的三次南渡,历时大概是80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重心才转移到了南方。在一个不熟悉的地理环境中,先民对南方的开发是一个不断摸索、整合,相对漫长的过程。
可明清鼎革之后,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四川盆地从原来的一个原始的野生环境,突然就变成了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从区区50万增长到了5000万。如此大的变革,和800年的那种向长江的人口转移是否有某种可比性?
当然,后来我仔细想了以后觉得是很难比较的。前者是具有开创性的过程,没有经验可遵循;后者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虽然遭到了极度破坏,可是那时候的人已经具有了开发南方山野的经验,是带着知识和与之相应的社会组织奔赴而来,速度就要加倍了。这就像工业革命之后,殖民者来到了原始的丛林中,其实是很容易把丛林改变为现代环境的。
既然如此,在“湖广填四川”的语境下,其实很难产生对这段“浓缩历史”的不同思考。但当时间极度压缩,如同一片白纸的土地,突然间就迈过了资源红利的门槛,这其中就有了挺多值得琢磨的题目。
比如中国的科技无法进步,是否是因为劳动力过于廉价,抑制了对节省人工的工具的改进?藏于大山之中,天高皇帝远,这里的工商业是否自发地生长出了不同于大山之外和官僚体制捆绑的工商业制度?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蔗糖、井盐、火炮和滇铜,这四种中国进入近代之前重要的物质或者称为事物,不经意地就汇聚在了17~18世纪云贵川的大山里。
我们知道蔗糖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工人阶级突然就能够享受到的,从奢侈品到大众消费品的调料。我在四川盆地南部的内江就感受到,在那个时候中国的甘蔗种植就如同南美大种植园一样,遍山遍野,这时的甘蔗榨糖技术也有了飞速的发展。可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积累出足够的财富,实际上这里生产的蔗糖主要是外销的,中国人的蔗糖消费并没有飞跃,但实际上这也形成了一个产业聚集。井盐就更不用说了,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835年,我们就在四川自贡打出了深1000米的盐井,这种深度即使在西方进入了工业社会之后也没有做到。
完成对这两种物资的踏访,我又开始在大西南游走,追溯更古远的社会。比如在宋朝的时候,中国人开始把火药用于武器,因为当时整个中国的版图上有多个政权在互相竞争,火药技术和火器技术的进步是非常快的。在重庆北部一点的钓鱼城,宋军就是用了各种火石武器,将蒙元大军阻挡在了那里,使整个元朝征服宋朝的过程迟滞了至少二三十年。
最后是滇铜。我们国家一直缺乏铸造货币的各种金属,比如像白银,到了明朝的时候,主要是靠海外流入。铜也是这样,主要是从日本进口。但是到了清初的时候,日本也意识到他们的铜也不敷用,开始有意地卡我们脖子,或者说在贸易过程中设置了贸易限额,我们国家突然就陷入了货币的混乱,因为没有那么多铜可以用来铸造货币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大规模开发云南的铜矿,最多的时候每年能生产1000万斤的样子。
通过对这四种物质的梳理,我就大概得到了在明清鼎革之际到鸦片战争之前,整个国家物资流通、矿产开发,以及农业生产的一个大概样貌。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去想象,如果我们没有在1840年被炮舰打开大门,这些在大山深处的物质生产和基于物质生产所出现的机制变革,是否给我们集齐某种敲开工业革命大门的动力?
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正如英国一些研究工业革命的专家所讲,敲开工业大革命大门,就如同你去按一个密码锁,你得把所有的这些条件都集齐了,才在一个很偶然的环境里迸发出这种改变人类社会进程的革命性发展,其实也是很偶然的。
但是即使是这样,在云贵川大山里的行走,也给我带来了某种很乐观的预期,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地方是在创新的,不管这件事情在多少年才后能带来这种革命或者变革,但是我们中国人是有制度创新的潜力。
这期的杂志封面的内容大致就是这样,谢谢大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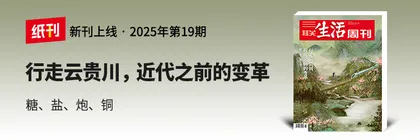 ———编辑/一丁剪辑/译丹
———编辑/一丁剪辑/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