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患者回到“家门口”看病?
作者: 霍思伊
乡镇卫生院留不住两种人:病人和医生。
75岁的邱杰住在广东阳江市沙扒镇,膝关节疼的毛病已经几十年,疼痛发作时像有密密的针在扎,严重时甚至下不了床。实在疼得受不了,他就到乡镇卫生院针灸,但只能轻微缓解。过去,对镇上的居民来说,“稍微重一点的感冒也要去县医院看。如果是肿瘤这种涉及开刀的病,直接跑到省里的大三甲,但大医院连挂号很难”。
这是中国基层医疗的一个缩影。长期维持这样的局面,就不可能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卫生院也陷入恶性循环。“招不来人,也留不住人。有些医生连简单的清创都无法完成。”沙扒镇卫生院院长卢先整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解释,要进一步推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对多数人而言,县域医共体还不是一个熟悉的名词,但它的改革目标是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实现这一点,要让县里的医院带着乡镇卫生院、村卫生站“抱团发展”,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和分级诊疗。
2019年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全国启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2023年后,医共体改革进入快车道。各地纷纷组建了医共体,并强调对县镇村三级医疗资源整合,但实际效果仍有差异。
“改革之所以很难,就是因为涉及基层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原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原卫生厅厅长于德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县域医共体是对整个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构,它的效果究竟如何?
资源应“向下倾斜”
沙扒镇位于广东阳江市阳西县,是粤西南的临海小镇,气候温和,自然环境优越,有不少“候鸟”老人来此过冬,但年轻人却爱往外跑。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阳西县常住人口43.41万人,与十年前比减少了1.85万。同时,这里60岁及以上人口占17.21%,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超过五分之一。
在中国,像阳西县这样的地方很多。但当越来越多留在村镇的老人想求医问药时,在家门口却找不到合适的医生。
阳西的改变发生在2017年。当年11月,阳西县开始进行医共体改革,将3家县级医院(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妇女儿童医院)、8家乡镇卫生院和138个村卫生站整体“打包”,成立阳西总医院。县人民医院为牵头单位,其他医院为成员单位,相当于总院下的分院。“我们是‘身怀六甲’,因为3家县级医院都是二甲医院。”阳西总医院党委书记关登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关登海介绍,医共体改革前,3家县级医院之间竞争激烈,遇到车祸事故,甚至会各自派救护车去“抢”病人。县人民医院想要建妇科肿瘤中心,县中医院也要跟着建。“但阳西县常住人口只有约43万,不需要建这么多肿瘤中心,完全是重复建设。”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症结,就是资源短缺和浪费并存。王程明是清华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县域医共体医防融合课题组组长。2018年,他去甘肃某地调研时了解到,当地中医院为了发展,把县人民医院的骨科团队“一锅端了过来”,因为骨科在基层是收益最多的科室之一。
纵向上,县级医院持续从“下面”虹吸病人,加剧了乡镇卫生院的萎缩。于德志指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医疗资源一直是“向上走”,出现中心化趋势,城市大医院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张,县级医院也在无序扩张,但从卫生经济学角度,最经济、有效的卫生服务体系,资源应“向下倾斜”,要建立健康“守门人”制度。
“向上”带来的后果,是不同层级医疗机构职能的错位。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原副局长、基层医改专家徐毓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边是三级大医院越位严重,过度承担不应由其负责的常见病和小手术;另一边是基层医疗机构缺位,县级医院难以对县域内常见病及时、有效地诊疗,乡镇卫生院水平更差,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需求严重脱节。
事实上,早在2009年这一轮新医改开始,国家就明确提出要“强基层”。但广东省基层卫生协会会长王家骥注意到,此后,城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还在加剧。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全国住院人次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从2009年的29.2%降到了2023年的15.1%。“仍然呈倒三角形。我们的医疗卫生体系应逐步变为正三角,基层占比是大头,大医院是小头。”他说。
于德志指出,要想真正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让医疗资源下沉,县镇村三级医疗机构间必须紧密地抱团,做到利益、责任、发展、服务和管理的一体化,不能仅组成松散的合作关系。
“最关键的是利益共享。”王程明说,“在一个锅里吃饭,成为一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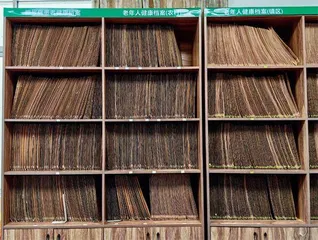
收权与放权
2018年,沙扒镇卫生院多了一个名字:阳西总医院沙扒分院。这一年,分院迎来了第一批下沉专家。总医院要求,县医院要安排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专家下沉到卫生院,每次下沉时间不少于半年,每个卫生院至少有三人常驻。“这是总院评估后认为性价比最高、对县医院负担最小的下沉模式。”关登海说。
对下沉人员的选择,乡镇卫生院可以提出需求,总院也会根据卫生院所在地区的人口特征和常见疾病谱确定人选。下沉专家不仅要给基层带教、查房,参与学科建设,有些还会成为医院的管理者。
各地医共体建设中,直接派驻管理人员是加速成为“一家人”的有效手段。2018年,阳西总医院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刘以举来到程村镇卫生院担任副院长。他发现,这里的住院部早上不查房,手术在简陋的换药室做,多数医生只懂一些外科的基础理论,操作上一片空白。挂职半年,他手把手地带教、规范查房和手术流程。“我很清楚,来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人才培养。”
对病人而言,医疗资源下沉后最直观的好处是:在家门口就可以救命。一次,一个阑尾炎病人在镇卫生院开刀,切阑尾时发现肠子也有问题,但卫生院只能做腰麻,缺乏全麻设备。刘以举立刻向总院汇报,很快,一位麻醉师带着全麻设备来了。
不过,随着下沉工作全面铺开,县级医院人手也出现短缺,这在各地的医共体建设中相当普遍。东部某市卫生健康局基层科一位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今年省里进一步强化了对人员下沉的考核,要求每个乡镇卫生院都有常驻专家,下沉至少半年,但对部分管辖区域内乡镇较多的县而言,同时抽调大量骨干会影响自身运转,“虽然报上来各县都说是落实了,但我们自己心里清楚,实际效果可能要打一个问号”。
在阳西,距离县中心最远的乡镇,车程只有40分钟。如果将目光转向中西部,在秦岭南麓的大山深处,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东西跨度88.5公里,南北长60.7公里,35.9万常住人口分布在16个乡镇,镇与镇之间的距离很远。这样的地区要想进行医疗资源整合,难度比东部沿海地区要大得多。
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局长龚忠涛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山阳县政府让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医院两家各自牵头,分包所有乡镇卫生院。与单一牵头医院的模式不同,两个牵头医院之间形成了良性竞争,表现好的医院会获得更多乡镇的资源分配。政府通过这种激励机制推动它们更积极地下沉。
从结果看,激励是有效的。山阳县从2023年开始深入推进医共体建设,对比2022年和2024年的数据,县域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占比从54.93%提升到65.53%。“强基层,关键要强镇村两级。”龚忠涛说。
山阳模式引入了类似市场性的手段,而非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强推。“有些试点地区存在政府指挥不动的问题。县级医院只是把医共体建设当成政治任务,担心下面卫生院强了,自己的病人跑了,在下沉上动力不足。”龚忠涛说。
如何才能让县医院真正“沉下去”?关登海认为,这需要将医共体内所有单位的法人代表统一,全部归为总医院院长一人,这是成为“一家人”的关键。
他解释,法人代表拥有充分的资源调配权,可统筹规划整个医共体的战略发展;当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发生矛盾时,法人代表能一锤定音。“不统一法人代表,人财物就没办法真的上收到总医院,总院对成员单位没有约束的权力,医共体建设只会是空中楼阁。”
阳西医共体建设已经八年,在县级层面实现了法人代表统一,但乡镇还没有完全打通。阳西县副县长卢伟青最近去调研,发现仍有大约一半卫生院院长反对统一,“特别是一些真正想做事情的院长比较反对”。
山阳则采取了另一种模式,在建设医共体时没有统一法人代表。龚忠涛说,在山阳这样医疗资源严重碎片化的地区,如果将管理权力全部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卫生院院长的权力被剥夺,可能导致基层的活力不足。
这正是基层医改的复杂性所在:一方面,收权才能整合资源,防止各自为政;另一方面,还要放权,给成员单位足够的空间,不能“管死”。收权与放权之间的平衡,则是最难的。
一位持续参与医共体建设的政策研究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山东、江苏的部分地区,卫生院原本就有很强的活力,“有些卫生院年收入就有上亿元,相当于一个二级医院,它们的法人代表很难统一”。因此,各地要因地制宜,统一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搅活基层的“一池春水”
村医赖昭诚很喜欢村口那棵200多岁的大榕树。广东夏季燥热,村里的老人常在树下纳凉,如盖的树冠将暑气都隔绝在外。赖昭诚在树下给老人们体检抽血,讲解高血压、糖尿病如何管理。这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县、乡镇、村三级网络中,村医是“网底”,也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多位专家指出,成立医共体总医院,只是把框架搭好,要想真正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关键在于如何激发医务人员的内生动力。这意味着必须同步配套薪酬制度改革,这是一个重要的杠杆。
在阳西,村卫生站被纳入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卫生站的法人代表由卫生院院长担任。村医不再像过去一样自负盈亏,工资由卫生院统一发放,享受同等社保待遇。“相当于卫生院的编外聘用人员。”关登海解释。
不同于县医院整合乡镇卫生院时遇到的挑战,卫生院在整合村卫生站时,相对顺利,多数村医都想从个体户变成更稳定的“单位职工”。整合之后,村医收入在基本工资和医疗收入之外,多了岗位绩效工资,多劳多得、优绩优酬。这是医共体薪酬制度改革的核心逻辑:靠绩效来搅活基层的“一池春水”。
以前,沙扒镇渡头村卫生站负责人赖昭诚的月均收入为3000元上下,主要靠公卫补贴和给村民看点感冒、腰痛等小病。现在,他的月收入涨到4000多元,加上广东省财政给村医每年发放的2.5万元补助,年收入达到7万多元。
乡镇卫生院职工的收入也有增长。卢先整介绍,沙扒分院在职员工共79人,编制人员占75.9%,这部分人的月均收入,从医共体建设前的5000元涨到了1.3万元,编外人员的月均收入也从2500元提升到4200元左右。
这一增长并不容易。2011年,为杜绝基层医生乱开药、乱收费的现象,中央出台政策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统一归入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实行“收支两条线”,这意味着人员经费靠财政全额拨款,与业务收入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