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构建战争理论殿堂的“西方兵圣”
作者: 杜燕波
古今中外谈兵论道者众多,但真正将战争作为一门学问、将战争理论研究作为毕生志业并取得卓越成就的,非克劳塞维茨莫属。克劳塞维茨不仅具有丰富的战争阅历,而且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在繁忙的军旅生涯之余,他对战争理论问题进行了长期而专注的思考,对战争本质、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以及战争活动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精深的辨证分析与精辟的理性阐释。其遗作《战争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克劳塞维茨本人更是藉此赢得“西方兵圣”的美誉。尽管书中大量晦涩难懂的哲学语言难免引发争议甚至误解,但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研究范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为后世兵家从事战争理论与实践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滋养。可以说,直到今天,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战争论》依然是人们观察与理解现代战争的一面镜子。
将战争研究上升到理论层面
战争是一种攸关无数人性命的特殊、复杂且不断演化的社会现象。自古以来,人类对战争问题的思考从未停止过。中国在这方面最早成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便涌现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大量优秀兵学典籍;西方在古罗马时期、拜占庭帝国时期也涌现出少量类似兵书。尽管这些古代兵书富含战争哲理和伟大兵学智慧,但从今天的科学视角看,它们都不具备完备的理论体系,因而不能称为“战争理论”。对此,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曾作过如此论断:“古代的辩证法带有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立志于突破这一困境的,正是被誉为“西方兵圣”的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早年也与其他军事理论家一样,善于将他对战争的思考提炼为一个个富含哲理的结论。但他深知,这些规律性的结论放在复杂的现实战争中,犹如一条条“细线”,并不能构成对战争问题的透彻阐释。于是,他立志“建立一个关于大规模战争的理论”。简言之,克劳塞维茨要“致力于研究战争现象的实质,揭示其与构成它们的那些事物的本性之间的联系”。他认为这才是战争理论需要完成的任务。由此,克劳塞维茨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理论探索之路,这也“耗尽他生命中最后12年的全部精力”。
最终,克劳塞维茨出色完成了这项充满挑战的伟业。原本他的抱负是“写一部不是两三年后被人遗忘的,而是对军事感兴趣的人会不时翻阅的书”。结果却远超预期,《战争论》被后世视为真正洞悉战争本质、形成战争理论体系、称得上“战争科学”的杰作。阅读《战争论》,犹如进入一座气势恢弘而又琳琅满目的理论宫殿,克劳塞维茨用长期凝思淬炼形成的各种抽象的概念、定义、范畴,把战争的本质、构成战争的基本要素、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机理阐释得清晰透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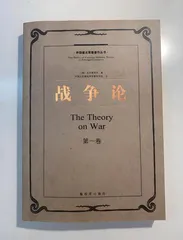
当然,克劳塞维茨取得如此大的理论成就,除个人努力与天赋外,还与其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有关。拿破仑战争的洗礼给克劳塞维茨带来直接而强烈的战争体验,漫长的军旅生涯使克劳塞维茨长期沉浸于对战争问题的思考,德国古典哲学的兴盛则为克劳塞维茨提供了重要思想养分与思维范式——最后这一点对于克劳塞维茨开创性地构建战争理论体系尤为重要。克劳塞维茨早年听过康德主义者基塞韦特的哲学课,读过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和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特别是深受同时代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的影响。
在战争理论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最伟大之人,行最艰难之事”。《战争论》基本实现了克劳塞维茨的初衷,即“阐明战争现象的实质,并揭示其与构成它们的那些事物的本性之间的联系”。之所以说“基本实现”,有两个原因。第一,《战争论》是克劳塞维茨的未竟之作。因感染霍乱,克劳塞维茨英年早逝,未能如愿完成他的战争理论著作,世人看到的《战争论》是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夫人整理而成的遗作,其中只有前面很少部分(即第1章,关于战争的本质,约2万字)是作者认为达到定稿要求的,因而人们永远无法知晓克劳塞维茨心中满意的“最终版”究竟是什么样子。第二,克劳塞维茨认为他的理论成果并不完美,尚有很大提升空间。他把其研究成果比作“纯金属的小颗粒”,希望“也许不久就会出现一位更有智慧的人,呈现给读者的不再是这些零星的颗粒,而是一整块没有瑕疵和杂质的金属”。
尽管如此,克劳塞维茨期望出现的那位“更有智慧的人”似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他在战争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至今令人高山仰止。与极尽简约的《孙子兵法》不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体量非常大,共3卷8篇124章,达80余万字。然而,真正读进去后,读者总能发现各处令人惊喜的军事理论的“纯金属的小颗粒”,而无重复、累赘之感。这有赖于克劳塞维茨精密、清晰而又有力的辩证分析。总的来看,克劳塞维茨在战争理论领域的革命性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深刻洞悉并揭示战争的本质。克劳塞维茨把阐述战争的本质作为《战争论》的第一项任务。首先从抽象的纯概念入手,他认为“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决斗”。随后,他又回到现实,修正了上述观点,指出战争中并不存在绝对的确定性,就像“数学上所说的绝对值,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坚实的基础,它们像织物的经纬线一样交织在战争中,使战争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最接近和类似于纸牌赌博”,并得出一个著名论断“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最后,克劳塞维茨将战争的本质归结为一个“奇异的三位一体”,即战争由三方面组成:一是战争要素固有的暴力性,包括仇恨和敌视,这些可看作盲目的本能;二是概然性和偶然性,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是作为一个政治工具的从属本性,使战争归于纯粹的理智。这三个方面,按照“三位一体”中提到的先后次序,分别对应于民众、军队(包括统帅)、政府。克劳塞维茨指出,“这三种倾向就像三个不同的立法,深植于战争的本性之中,同时其作用大小又是变化无常的”,因而战争“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
“奇异的三位一体”这一研究结论成为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后面内容皆由此生发出来。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对战争本质最深刻、最透彻也最正确的理性认识,任何一场战争都逃不开这一概念框架。此后许多流派的战争理论也均可从中找到源头。例如,毛奇的“任务式指挥”可视作对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第二个方面的发挥;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可视作对战争理论的三个方面同时发力;利德·哈特的大战略理论可视为由战争理论的第三个方面引申出来的;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可视为对战争理论的第一个、第三个方面的最大化发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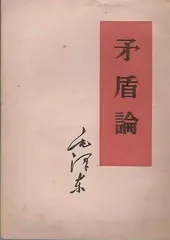

全面考察各种战争要素并阐明其特性。面对复杂的战争现象,克劳塞维茨既未陷入战争不可知论,也未如比洛、约米尼那样流于对战争问题不适当的简化,而是以极大的理论勇气直面战争固有的复杂性。第一,对于战争中无处不在的危险、劳顿、偶然性(概然性)、政治因素以及人的情感、意志、军事天赋等诸多因素,克劳塞维茨分门别类地深入探讨了这些因素的性质及其对战争行动和结果的客观影响。尽管人们能够普遍感知到这些因素,但只有克劳塞维茨极其认真地对待这些因素。克劳塞维茨认为,严格意义上讲,战争中的许多要素在战争分析中是不能简单约减的。他指出,“在战争中属于整体的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的,因此每个原因(即使很小的原因)的影响必然会贯穿至整个战争行为结束,并使最终结果有所改变(无论改变是多么小)”。第二,对于精神力量在战争中的作用,克劳塞维茨给予极大关注,并认为它是高于物质力量且对物质力量发挥巨大促进或制约作用的重要因素。克劳塞维茨精辟地指出,“战争就其本义来说是斗争……斗争是双方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借助于后者进行的一种较量。不言而喻,人们不能排除精神力量,因为心灵的状态对物质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克劳塞维茨明确知道“任何理论只要触及精神领域,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是他丝毫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坚持认为,“军事活动从来就不是仅针对物质,而是同时针对使物质具有活力的精神力量,把两者分开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三,对于几何学在战争中的功用,克劳塞维茨并未一概排斥,而是从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四个层面进行探讨,对几何学在战争中的作用给出恰当的评价。克劳塞维茨指出,“在筑城术中,几何学几乎支配着从小到大的一切问题。在战术上,几何学也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现代战术比起要塞战来,一切都更为机动,精神力量、个人特点和偶然性都起着更大的作用,因此几何要素不可能像在要塞战中那样居于统治地位。在战略范围,几何要素的影响就更小了……战略上更重要的是胜利战斗的次数和规模,而非这些战斗地点相连形成的线条形状”。
科学阐释战争规律与作战思想的基本原理。中国古代兵学典籍饱含着大量颠扑不破的战争规律和正确的作战思想,但是受语言文字、哲学思想、物质条件等方面的时代局限,未能充分阐明这些规律或思想的基本原理,故而长期处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地。相比之下,克劳塞维茨以其深厚的哲学功底和非凡的思维能力,较为系统地完成了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壮举。例如,我国古代著名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精辟地阐述了战争中攻守之间的辩证关系——“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焉”,其中包含的积极防御、攻防快速转换的思想实际上与克劳塞维茨对该问题的认识高度一致,克劳塞维茨用严密的分析论证、不惜笔墨地细致阐述和贴切形象的修辞手法,从原理上把这一问题阐述清楚了。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事实上我国古代早就认识到这一重要问题,这不仅是“儒家兵学”学派的核心议题,在其他兵家学派中也有精辟的论述。例如,《吴子兵法》所言“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等。然而,现代战略学界(特别是西方战略学界)把阐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版权”归于克劳塞维茨,他的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被无数人铭记并引用。原因还在于,克劳塞维茨用大量朴实的文字围绕这一核心论点进行了系统论证,把其中的原理阐释得十分清楚。诸如此类的论证使人类自古以来便发现的战争规律和作战思想首次有了理论归属,上升为战争科学领域的“定理”或“定律”,为现代战争理论和军事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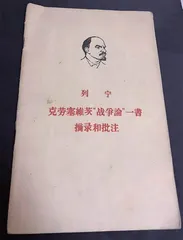
形成科学的战争概念体系。概念是研究问题的逻辑起点,完备的概念体系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称得上科学的重要标志。克劳塞维茨对这项基础工作极为重视。他有句名言:“对于任何一个理论,首先要做的就是澄清杂乱,也可以说是澄清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观点。人们只有对名称和概念有了一致的理解,才有望清晰而顺利地考察问题,才有把握与读者一直站在同一个立场……如果不准确地确定其概念,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它们的内在法则和相互关系。”事实上,克劳塞维茨对战争问题的每一步理论推导,均以概念厘清为先导。可以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大厦正是由一根根概念的“柱石”构建而成的。突出表现如下有三。一是善于厘清复杂的概念边界。例如,克劳塞维茨对“战术”“战略”“军事艺术”等人们常说常讲但又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了严谨而科学地界定,作为其研究战争理论问题的有力工具;对进攻、防御、追击、撤退等作战行动样式及其性质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辨识,作为提出不同作战行动、不同作战时节作战原则的基本依据。再如,他把勇气列为军人的首要品质,并区分为“针对危险的勇气”和“敢于负责的勇气”,前者指在战场上不惧危险,后者指从理智中生发出来的勇气,称作“智者之勇”——这与我国古代所言“匹夫之勇”“大智大勇”的涵义相当。凡此种种对概念边界的厘清,在《战争论》中随处可见,成为其一大魅力所在。二是善于根据研究需要创造新概念、新术语。克劳塞维茨是一位具有极大创造精神的军事思想家,此前的术语体系并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于是他在其战争理论著作中创造性地提出许多新概念、新词汇,包括“天才”“战争阻力”“武德”等。这些词汇大都成为后世军事理论界耳熟能详的热词,甚至成为人们研究与考察战争的“行业标准”,影响了一代代兵家。三是善于用贴切而形象的修辞手法阐明概念。克劳塞维茨的语言延续了德国哲学与德国文化特有的严谨性,同时又特别善于用类比、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加以阐述,从而把问题讲得清楚、透彻、令人信服。例如,在谈到物质和精神在战争中的作用时,克劳塞维茨指出,“物质力量的作用与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会像合金那样被化学反应所分解”,“物质的原因和作用几乎只是以武器木柄的形象出现,而精神的原因和作用才是贵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武器”,“巨大的精神力量,有时像真正的酵素一样渗入战争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