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大学里的青春岁月
作者: 石岩 万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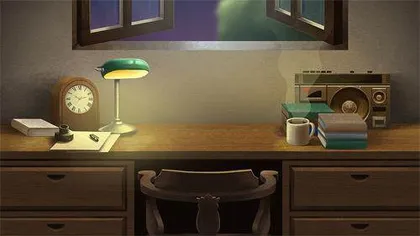
1977年,高考恢复,当年12月,570万青年走进考场,只想“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
1978年3月,一份份录取通知书,送到了那些在1977年高考中“突围”的考生手里。从570万考生中脱颖而出的幸运儿们,开启了“追赶时间”的青春岁月。
北京大学:时事与潮流一起跟
刘学红以北京市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新闻系77级,在此之前,她在京郊密云县(现密云区)插队,被分配到林业队,日常的工作是管理果树。1978年2月19日,刘学红写的高考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她写了热汗淋漓的劳动,也写了公社果园的诗情画意,漫山遍野的梨花杏花,瓜果飘香的金秋。
1981年3月21日,中国男排先输两局后奋起直追,以3∶2战胜韩国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4000多名北大学生集队游行,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和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在同一时期喊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并称20世纪80年代的“最强音”。刘学红在日记里记下了同学们欢呼雀跃的场面。
除了紧跟时事,刘学红和班里的女生也是时尚的引导者和追随者。刘学红有一张烫着大波浪、穿着大红连衣裙的照片。裙子是同宿舍的鲁薇给裁的,刘学红自己扎的。
北京大学新闻系77级的同学自己办了一份叫《实报》的小报,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从报头到版花全是手写,全班同学的笔迹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主笔孙冰川被称为辣椒主笔,国际国内的大事小情没有他和他的同学们不敢评论的。
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可以救国
广州知青霍东龄考取了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通信工程专业,他特意找了身军装,“很神气”地去学校报到。他记得在高考完体检的时候,就有人把翻毛的皮鞋都穿上了,“盛装出席”。
入学之后,全班同学自发早上6点半起来跑步,一跑就是好几年。一则锻炼身体,二则避免睡懒觉。霍东龄还给自己提出“三戒”口号:戒电影、戒电视、戒娱乐。“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国家的期望就是认为科技可以救国,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振兴中华”。
当时学校里闹“教师荒”,两百多号人一起在阶梯教室上大课,坐在后面的要靠望远镜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课本不缺,参考书却不够。每出一本参考书,大家都去排队买。学校附近的五山新华书店,也改为专门经营教学参考书的书店了。
霍东龄毕业后进入广州微波站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他下海从商,做电子和通信类产品贸易。1995年,霍东龄跟大学同学张跃军一起创办京信通信,现在,京信通信已经是中国移动及中国联通最主要的外围设备供应商之一。他们同班的77级无线电学生们,很多都成为国内电子电信行业的老总,诸如TCL的总裁李东生、康佳的总裁陈伟荣、创维的总裁黄宏生、德生电器的总裁梁伟。
四川美术学院:共用一支蜡烛的宿舍
四川美术学院在“1977年招生总结”中写道:报考人数众多,盛况空前,大有可选之才。大批云贵考生赶来应试,但招生指标有限……
走进四川美术学院的时候,杨千是一个懵懂的19岁青年。考大学之前,他已经在母亲的单位干了两年临时工,跟成都一所中专的美术老师何多苓学了几年画。1978年3月,“师徒”二人一起考入川美,那时的何多苓已经是四川小有名气的“画家”。

杨千对大学生活最深刻的记忆是他和何多苓共用蜡烛读书。宿舍熄灯之后,点点烛光映在宿舍的窗户上。杨千和何多苓一个宿舍,都在上铺,头挨着头,熄灯之后共用一支蜡烛。
跟何多苓的名声一样的是外号“罗锅”的罗中立。参加高考的时候罗中立29岁,平时安全帽、工作服,标准的工人阶级打扮,业余画连环画补贴家用。罗中立投考川美纯粹出于经济考虑,他听说大学生每月的补助是五十几块钱,当时他的学历是中专,中专生每月的补助是29块。
临近毕业的时候,杨千和罗中立共用一个6平方米的画室做毕业创作。重庆的夏天溽热,两人光着膀子画画。罗中立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画出来的。
(摘编自2007年第6期《党员文摘》/原载《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