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
作者: 马一瑄“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是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文化影响下提出的观点,然而人们常常简单地因字面意思将两个词进行等同,其实两个词并不一样。二者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文如其人”的发展历程比“风格即人”要复杂得多,但相同的是,二者都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如其人”是中国从古至今多个朝代均有提及的对文章的看法与期望的理论,表达了文章的风格同作者的性格相吻合的观点。“风格即人”则是由法国18世纪文学家布封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饱含其对风格的看法。本文主要围绕这两个词进行简单的解释与分析。
一、文如其人
“文如其人”的说法实际上在各个朝代均有。“文如其人”,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写的文章与作者的品性相符合,深入理解便是文章的风格、内容、情感等方面能够反映出作者的性格特点、思想立场等。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在《论语·宪问》中便提出了“德”与“言”的关系:“有德者必有言。”这就说明孔子认为有德行的人一定有好的言论,他强调了“德”对于“言”的决定性作用。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便是“文如其人”的渊源。虽没有专业性的文章,但也初现滥觞。到后来,汉代扬雄在《法言·问神》中说道:“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他认为无论是言还是书,本质都是心灵的表现。所以扬雄认为,从作者的精神世界与内心世界当中就能区分君子与小人。这就是所说的“言为心声”,由言行就能看出人的品质。西汉著名的才女卓文君,是一位有着自己想法,有勇气的女子。在丈夫司马相如想要纳妾时,她提笔写下流传千古的《白头吟》告诫他,她希望“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还道他若纳妾,两人婚姻便破裂。司马相如遂打消纳妾的念头。即使卓文君年少时因爱私奔,但她也从不失敢爱敢恨的勇气与决心,这点在文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汉朝时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儒家思想因此在社会上占据了统治地位。无论是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扬雄的“言为心声”,还是王充的“德弥盛者文弥縟”(《论衡·书解》),都是或多或少从伦理学的层面来强调人的品德与文章的关系。而到了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儒学逐渐衰微,玄学兴起。当时的人们可以直抒胸臆,不再受礼法的约束,“建安文学”便是其中的代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便是著名的“文气说”。他以一个新的角度观察“气”与“文”的关系。其中的“气”指的是个性,与伦理无关;其中的“清浊”更是各指两种不同的气质。他所谓的这种“文以气为主”,应指的是作者的天赋与个性,表明文章应把作者的个性放在首位。这就将“文如其人”从伦理的层面扩大到生理与心理的层面。所以,“建安七子”各不相同的原因应该就是“性”不同。无论是曹操“老骥伏析,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抒发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还是曹植“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赠白马王彪》)感叹郁郁不得志的悲伤,抑或孔融“闻子不可见,日已潜光辉”(《杂诗二首》其二)痛苦儿子的离去,他们都展现了各自的个性气质。刘勰在创作《文心雕龙·体性》时,就是建立在曹丕的“文气说”上,提出了“因内符外”“表里必符”的观点,并对风格论进行了完善。他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谪,文苑波诡者矣”,说明了创作者创作的作品受不同的性情所影响,更加深化了“文”与“人”的关系。
宋代,作为文化繁荣的又一高峰,文人雅士更加注重内心世界的抒发与哲理的探索。苏轼的“文如其人”,不仅是对个人品性与文风一致的肯定,更是对那个时代文人追求真我、不拘一格的精神风貌的反映。他虽历经贬谪,却能在逆境中保持豁达,其诗文中所流露的乐观与坚韧,正是其人格魅力的真实写照。这种将个人情感与文学表达紧密结合的趋势,使得“文如其人”的观念在宋代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和深化。苏轼的《答张文潜书》写道:“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文如其人”才首次正式出现。苏轼本人就是“文如其人”的杰出代表。尽管他是文学史上的一位伟人,他的一生却艰难坎坷。但无论他是否身处逆境,他都保持着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首贬黄州时,他写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再贬惠州时,他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最后贬到儋州时,他依然写下了“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的旷达诗句,可见他的品性。明朝冯时可在《雨航杂录》卷上说得更加直白:“永叔侃然而文温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则,苏长公达而文遒畅,次公恬而文澄蓄,介甫矫厉而文简劲,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这就是“文如其人”的明确出处。其举出了多重例子说明“文如其人”的普遍意义,使得“文如其人”更加广泛化。在此之后,也不乏叶燮、徐增等人对此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但“文如其人”这一观点并不是绝对的,作者的品性与文章风格不符的情况时有发生。正如吴处厚在《青箱杂记》中所言:“山林草野之文,其气枯碎。朝廷台阁之文,其气温。晏元献诗但说梨花院落、柳絮池塘,自有富贵气象;李庆孙等每言金玉锦绣,仍乞儿相。”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中与之相似的大有人在。例如潘岳,《晋书》中记载他性情浮躁,趋利避害,与旁人一起谄媚、侍奉贾谧。每次等到贾谧出来,他必然望着尘土下拜,这完全是一副小人模样。然而,这样的人却能写出《悼亡诗》,并且开创了中国悼亡诗歌之先河;还有极负盛名的《闲居赋》《秋兴赋》等作品。被《明史》列为明朝六大奸臣之一的严嵩,在位时陷害同僚,结党营私,横行专断,最后在举国的唾骂声中死去,却能写出“白屋扉临一水静,苍山路入万松迷”(《宿深溪馆》)这样清丽的诗句,实在令人咋舌。元好问就曾在《论诗三十首》其六中无不感慨地喟叹:“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
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他在这里既讽刺了潘岳的人不及文,更批评了扬雄的“心画心声”说。
在探讨“文如其人”这一命题时,我们不可忽视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历史变迁对文学创作与人格评价的影响。随着朝代的更迭,文学风格与士人风气亦随之变化,进而影响到“文”与“人”关系的解读,如上文中说到的潘岳与严嵩等人的例子,揭示了文学才华与个人品德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文人虽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其人格上的瑕疵却与作品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引人深思。这促使后世学者在评价文学作品时,不仅要关注文字背后的情感与思想,还需结合作者的人生经历与时代背景,全面而客观地分析“文”与“人”之间的微妙联系。
综上所述,“文如其人”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其内涵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它既是文人墨客追求内在品质与外在表现相统一的理想境界,也是对复杂人性与多元文学风格并存这一现实的深刻省察。在评价文学作品及其作者时,我们应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既要欣赏文字之美,也要关注人格之真,如此方能更全面地理解“文如其人”这一命题的深刻意蕴。历史上关于“文如其人”的争论从未停歇,其中多数认为文不如其人的实例,仅是因为文章风格与作者品德不相符,而忽略了对作者性格与个性的考量。因此,我们应当从品德和个性两方面同时审视,再作出结论。
二、风格即人
风格,这一创作主体对客观事物深刻体认后的个性化反映,不仅是文学艺术的灵魂,更是创作者精神面貌与内在品质的镜像。正如布封在入职法兰西学院院士时的演说《论风格》中所深刻揭示的,风格之于创作者,犹如灵魂之于躯体,是不可或缺且独一无二的存在。在布封看来,风格是创作活动中最为核心且不可复制的元素。与知识、事实和科学发现相比,风格具有一种难以捉摸却又无可替代的独特魅力。它不像知识可以被学习、被传授,也不像科学发现可以被验证、被复制。风格,是创作者内心世界的直接映射,是创作者独特个性和才智的结晶。布封强调,那些仅仅以细碎事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往往缺乏深度和内涵,难以形成独特的风格。而真正能够构成风格的,是那些创作者独有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元素,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作品的灵魂和生命力。
布封对于风格独创性的坚持,是对创作者智力与思想的高度肯定。他认为,真正的风格不能只停留在堆砌、组合的词汇上,而应该是形象的、有力量的、有灵魂的表达。这种表述源于创作者对世事的独特认识和深切体悟,集中体现在创作者的人格和才干上。在布封看来,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又艰辛的过程,它要求创作者在前期对构思、选取主题、确定停顿点等有着确切的把握,然后不断地回顾与填补、充实构想的内涵,从而达到前后贯通的构思目的。这一过程既加深了创作者对自我的认知,也深入探索了创作主题。
然而,塑造风格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布封指出,创作者需要在风格形成的中期,制定出挑选核心词语的计划,以保证行文流畅、一气呵成。这一阶段的创作者,就像是精心布局的画家,将内心的情感和对世界的认识通过细腻的笔触和色彩的搭配,融于作品之中。要紧扣主题的真实风格,不应单调乏味,而应像一幅能引起观者共鸣和思考的生动画面一样,色彩斑斓。布封在风格的最终成型阶段,强调的是创作者同时要有思想、有灵魂、有品位,才能有智慧的聚合。这三者的融会贯通,在賦予作品深度和广度的同时,又赋予了作品独特的韵味和神韵。“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所说。每个人的精神面貌、精神活动和表现个人精神的样式、形式都是千差万别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千姿百态和丰富性。所以,自由个性在一般意义上是人的本性,风格则是艺术化地表现这种个性。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将风格视为创作者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每一位创作者都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感悟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领悟和感悟不仅表现在作品的内容和题材上,也渗透在作品的文体中。布封曾言“风格即人”,正应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在欣赏一部作品的时候,其实是在和创作者进行心灵的一次跨越时空的沟通。通过作品的风格,我们感知创作者的情感、思想和态度,从而对作品所传达的信息和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如其人”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观念认为,文章的风格与作者的性格、品质是紧密相连的。虽然“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二者在本质上都强调了创作者个性与作品风格之间的紧密联系。事实上,“文如其人”可以视为“风格即人”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具体表现。它提醒我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不仅要关注作品的内容与主题,更要关注其风格与创作者个性的关联。
受到中国传统的“文如其人”与西方“风格即人”观念的影响,巴金主张“文学与人格的一致”。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与独特个性的人。只有这样,其作品才能具有真正的价值与意义。巴金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追求艺术的精湛与完美,更要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与提升。因为只有这样,创作者才能创作出既具有艺术魅力又蕴含深刻哲理的作品。一个作家如果仅仅追求技巧上的精湛,而忽视了对自己品德与个性的锤炼,那么他的作品即使再华丽,也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相反,只有那些既注重艺术技巧的提升,又不断修炼自己品德与个性的作家,才能创作出既具有艺术魅力又蕴含深刻哲理的作品,这些作品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流传干古的佳作。
综上所述,正因为“风格即人”与“文如其人”在意义上的相近,很多人会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起来,其实二者并不等同。布封提出的“风格即人”其实更强调风格的独创性,强调才气;而“文如其人”则包括品德与个性两个方面。所谓二者的等同,要将其放在特定的语境下。因此,我们应准确把握不同词中的含义,扎扎实实地进行分析,而非简单地理解字面意思。风格作为创作者独特个性和才智的结晶,是连接创作者与观者的桥梁。在欣赏文学作品时,我们不仅要关注作品的内容与主题,更要通过风格这一独特视角,去感知创作者深邃的情感世界和丰富的思想內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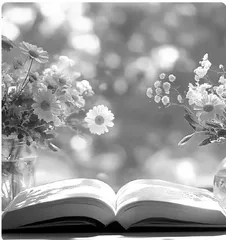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wxji20251175.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