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与跨大西洋关系的分化
作者: 张健【关键词】跨大西洋关系 特朗普2.0 美国 欧盟 大国关系
自冷战结束以来,跨大西洋关系一直处于变化调整之中,在经贸、科技、地缘政治、人文等领域,量的变化一直在持续累积。特朗普1.0已经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实质性冲击,而特朗普2.0对欧洲看法更为负面,政策调整力度更大,对欧洲的冲击也更大。与此同时,欧洲对特朗普政府的幻灭感和憎恶感增加,对跨大西洋联盟特别是北约的信心急剧下滑,开始采取实质性举措对美“去风险”,增强自身战略自主能力。跨大西洋关系在几十年持续量变的基础上正在经历质的变化,未来或将呈现持续分化的态势,竞争的一面增多,协调及合作的一面减少,联盟性进一步下降,交易性将更加突出。
跨大西洋关系的主要矛盾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欧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体,跨大西洋关系对美欧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均被彼此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跨大西洋联盟在二战中形成,在冷战期间强化,虽然在冷战结束后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重要性有所下降,但跨大西洋关系因其人文、血缘及经济、科技、安全纽带依然十分紧密。过去几十年来,跨大西洋关系起起伏伏,时有分歧和矛盾,包括经贸纠纷以及对待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等国际问题的不同态度等。但总体而言,跨大西洋关系保持了延续性和稳定性。即使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跨大西洋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并且在拜登政府时期很快得到恢复。然而,特朗普再次执政后,跨大西洋关系相较于其第一任期时遭遇的冲击更大、分化更深、矛盾更为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安全领域的矛盾前所未有。安全联盟是跨大西洋关系最重要的纽带,北约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基石和欧洲安全的支柱,但这一纽带正变得日益松散。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曾称北约“已经过时”,引发欧洲恐慌。在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称不会保护在军费支出上不达标的欧洲国家,并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反对继续援乌,再次引发欧洲恐慌及对美国和北约是否可靠的质疑。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对欧洲在安全上长期搭便车的行为更加嫌弃,且在处理相关事务时不顾及欧洲安全利益。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特朗普倾向于支持俄罗斯的立场且拒绝谴责俄罗斯,指责乌克兰挑起战争。2025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公开声称,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也不可能收复已经失去的领土。美国还撇开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直接谈判,也不愿对俄罗斯施压,而是更乐意施压乌克兰,甚至在白宫公开羞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23日,特朗普再次指责泽连斯基拖延和谈进程,认为其拒绝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对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非常有害”。[1]欧洲在震惊之余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有效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包括推动欧洲重新武装,减少购买美国武器等。就连一贯亲美的德国也开始转变态度,德国总理默茨公开质疑北约的未来,声称“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获得真正的独立”。[2]
二是经贸领域遭遇重大挫折。欧美经贸联系紧密,双方互为对方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来源方。2024年,欧美货物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9760亿美元,其中美国逆差2360亿美元,相比2023年增长270亿美元。[3]跨大西洋两岸的经济竞争一直存在,且不时会爆发较大规模的贸易分歧和冲突,比如空客与波音的补贴之争持续几十年至今仍未解决。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对美国与欧盟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十分不满,曾称欧盟为“敌人”,其第二任期以来对欧盟的不满有增无减,称“欧盟的成立就是为了坑美国”,[4]要求欧盟尽快减少对美贸易顺差。鉴此,美国对欧盟祭出关税“大法”:3月8日,美国决定对出口美国的所有钢铝产品加征25%的关税;3月26日,美国决定对所有进口汽车及部分零部件加征25%的关税,包括欧盟出口的汽车和零部件;4月2日,美国宣布对欧盟加征20%的对等关税,但暂缓90天执行;5月23日,特朗普宣称,与欧盟的谈判毫无进展,将对欧盟加征50%的对等关税,于6月1日起生效;5月25日,特朗普宣布将这一关税措施推迟至7月9日,以给双方更多的谈判时间。美国自2025年4月4日起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的10%“最低基准关税”并未豁免欧洲。5月30日,特朗普宣布将对钢铝产品的进口关税从25%提升至50%,从6月4日开始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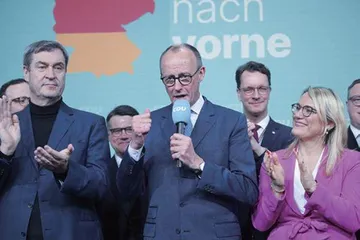

欧盟当前经济形势不佳,最大经济体德国连续两年负增长,美国的关税政策及其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让欧盟经济雪上加霜,也加深了欧盟对美国的怨恨。除传统贸易领域外,欧美在数字服务领域的矛盾也在发酵。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基本垄断了欧盟的数字市场并且赚取了巨额利润,这让欧盟十分不甘,遂以保护隐私、反垄断等名义出台多部法律,特别是2024年生效的《数字市场法案》及《数字服务法案》明显加大了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和打压。2025年3月18日,欧盟委员会认定美国的苹果、元宇宙(Meta)等高科技企业违反了《数字市场法案》,称将对相关企业处以其全球收入10%至20%的高额罚款,例如苹果公司2024年全球收入为3910亿美元,最高可能面临约800亿美元的罚款。[5]但由于害怕过于刺激美国,欧盟委员会4月23日最终决定对苹果、元宇宙两家公司分别征收5亿和2亿欧元的初步罚款。鉴于美国科技企业此前曾多次遭欧盟罚款,美国政府早有抱怨。在欧盟作出这一处罚决定后,白宫声称,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歧视美国公司,“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勒索”,美国对此“绝不容忍”。[6]
三是在价值观方面渐行渐远。长期以来,欧美双方都认为彼此拥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如民主、人权、法治、自由贸易等,但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双方在价值观上的冲突和矛盾日益凸显。欧洲认为特朗普是右翼民粹主义者,“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就是一场民粹主义运动。特朗普及诸多美国政府官员则对欧洲所谓主流政党和主流价值观持蔑视态度,反而极为青睐欧洲主流政党眼中的所谓“极右翼”政党。2025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抨击欧洲压制言论自由,打压极右翼政党,并会见德国右翼政党选择党领导人;3月31日,巴黎法院裁定右翼民粹主义政客勒庞挪用欧盟资金罪名成立,禁止其竞选公职5年并立即执行,而勒庞被认为是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人之一。这一判决遭到美国政府质疑,特朗普本人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法院对勒庞的判决是“猎巫行动”,应该“放了勒庞”。[7]
跨大西洋关系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欧美矛盾激化,特朗普再次执政是直接原因,但从根本上看,特朗普2.0只是一个催化剂,其深层原因是跨大西洋关系自冷战结束以来持续分化。欧美分歧和矛盾几十年来一直在持续累积,虽然在拜登政府时期有所缓和,但并未根本改变跨大西洋关系的分化趋势。毫无疑问,特朗普2.0将放大欧美分歧和矛盾,也将让这种分歧和矛盾在未来更加难以调和。
第一,跨大西洋两岸在安全利益和安全观上的分化加大。冷战结束后,欧美安全上的共同威胁消失,安全利益和安全观开始分化,美国将更多注意力投向亚太,而欧洲则着力推动中东欧转型发展和改造俄罗斯。
然而,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特别是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对俄罗斯的态度逐渐转变,将之视为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欧俄关系急转直下。美国国内则相对分化,两党对俄罗斯态度虽有不同,但均将之视为主要对手。拜登执政时期,虽与欧洲一道制裁俄罗斯,但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不愿全力援助乌克兰,更不愿与俄直接对抗。而共和党更关注如非法移民、提振经济和制造业回归等美国国内问题,其对外政策更多是从维护和捍卫美国的霸权地位出发,不愿将精力用于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认为乌克兰或者俄罗斯都是欧洲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美国“有更要紧的事要做”,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甚至撇开欧洲与俄罗斯单独谈判令欧洲很是不满。[8]

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多极化发展,美国和欧洲的实力相对下降,美国越来越难以承担庞大的海外安全义务,因此开始强迫盟友分摊更多的安全成本,也就是说,美国的安全保护费将更为昂贵。欧洲由于自身绝对实力的下降,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不减反增。因此,当美国不再关注和重视欧洲安全关切时,欧洲面临的压力更大,对美国的怨恨也就更大。
第二,跨大西洋两岸经济民族主义上升加剧经济竞争。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西方在科技、经济上的垄断地位持续遭到削弱,无法倚仗传统的科技、市场和规则优势继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其传统经济和社会运作模式遭受冲击,高福利社会难以维系。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末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经济民族主义在跨大西洋两岸兴起并持续发酵,其主要表现是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强调保护主义,热衷于排外。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推出所谓“购买美国货”条款,欧盟则持续强化贸易救济工具,打着所谓“公平”“对等”的旗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加征名目繁多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然而,欧美经济民族主义不仅针对第三方,也针对彼此,而且由于跨大西洋两岸在经贸上的紧密联系,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在彼此之间招致的反应和影响也更大。跨大西洋两岸在货物贸易上存在较高的同质竞争,比如美欧都是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但美国在货物贸易上对欧洲存在巨额逆差,在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以及公债都在持续快速攀升的情况下,美国愈来愈难以忍受对欧贸易逆差。而欧洲在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下,更加依赖美国市场,对美出口及顺差持续上升,加剧了美国的不满。
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则是顺差方,特别是美国高科技企业垄断了欧洲市场,赚取高额垄断利润。在这方面,欧美矛盾的本质就是垄断与反垄断、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欧洲一直想要获取“技术主权”,如果说过去欧盟因为依赖美国在安全上的保护还能忍受美国在科技上的垄断和控制,那么当前在美国视欧洲为竞争者且不愿提供安全保护的情况下,欧洲更难忍受美国在科技产业上的垄断和控制,将采取更多手段捍卫“技术主权”。而美国则将极力捍卫自己在欧洲的垄断地位,视欧洲构建“技术主权”的努力为反美行动,双方的对立和对抗将有增无减。
第三,跨大西洋两岸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加剧欧美价值观冲突和矛盾。过去20余年来,右翼民粹主义在跨大西洋两岸持续发展壮大,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跨大西洋两岸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的一次高峰。此后,右翼民粹主义的浪潮持续高位奔涌,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表明,右翼民粹主义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欧洲,近年来特别是2024年的几次重要选举表明,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目前来看,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等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经成为本国议会第一大党。德国选择党在2025年大选中一举成为该国议会第二大党。2025年4月8日的一项民调显示,选择党已经超过中右翼的联盟党成为德国支持率最高的政党。跨大西洋两岸的右翼民粹主义并不完全一样,但形成了共鸣和合流,这是因为两岸的右翼民粹主义都是民族主义的、排外的、反多元文化的、反建制的,而特朗普政府显然对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抱有好感。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受到所谓“主流政党”的排斥,特别是德国构建所谓“防火墙”,即拒绝与右翼政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这招致了美国政府的批评。特朗普本人自认为曾长期遭受建制派和主流媒体的不公平对待,在其看来,美国的民主党与欧洲所谓的主流政党是一丘之貉,这是特朗普特别反感欧洲建制派、同情欧洲右翼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