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词的传播方式变迁与词乐离合
作者: 唐梦斯

从南唐到南宋,李煜词的传播方式经历了从“口头歌唱”到“案头阅读”的文本化变迁。这一变迁过程受到词体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媒介等外部因素变化的助推,也深受词体本身创作目的、社会使命以及体裁技法成熟程度等内部因素影响。以梳理李煜词的传播方式变迁过程,归纳其文化性质由演唱歌辞向阅读文本迁移的原因为切入点,可以探究词体发展过程中内部文学性与音乐性的离合,一窥唐宋词从“词乐合一"到“词乐分离"的内在动力。
一、南唐时期的歌唱传播与歌辞性质
词在唐代兴起时,又称“曲子词”,常以配乐歌唱为主要传播方式,在发展初期与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故而在传播方面也更倾向于将乐工伶人的演唱传播作为主要方式。至于李煜词诞生的五代时期,受创作主体与社会期待双重因素影响,“词乐合一”的趋势更为明显,词类作品的音乐色彩浓厚,多数时候作为演唱脚本而非阅读文本存在。
入宋以前,李煜词多数为合乐演唱而作。作品语字浅白稀婉,题旨香艳浅薄,歌辞存在。这一明显特质与当时词体宏观上所处的“由乐定体”“倚声填词”的发展阶段相呼应,是词体内部音乐性压过文学性的外化表现。晚唐五代时期的词体将宴会酒桌作为主要传播环境,将歌舞乐妓作为主要传播媒介,将口头演唱作为主要传播方式,是当时词体的发展阶段受歌唱这一媒介支配的表现。与此同时,歌唱行为中鲜明的音乐因素也会成为塑造这一文学体裁的整体风貌的一大作用力。
任半塘在《唐声诗》中记载当时“文人为词按常情必自求合于调。如白、温诸家,或亲自调训歌舞,或躬与管弦雅奏,文人与乐工之间丝毫无隔,亦即声与词之间丝毫无隔”。此时的南唐君臣广泛接受“词为歌辞”的定位与歌舞传播方式,将“倚声填词”“乐主词从”作为创作准则。且身兼传播与创作主体的李煜本人本就对于音乐十分热衷,更加具备使其前期词作归附于音乐,依托于演唱的主动性,如其词《玉楼春》: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照烛花红,待放马蹄清夜月。
此词生动地描绘出封建帝王彻夜纵酒欢歌,整个宫廷随帝王之情欲“好恶取舍”,管弦笙箫不绝的场景。此词既是宫廷乐队演奏的唱辞,也是李煜生活态度的真实刻画。这样的创作环境与呈现方式自然会反作用于作品,如其词作中的“郎”“奴”“些个儿”等浅白口语多次出现;题材多写女子闺情与享乐;风格多婉转妩媚,偏好描写与贵族女性关联且充满暖昧情调的事物。李煜前期词既是词体初期文体特征的个体案例,又是传播因素反向塑造文学的结果。
与此同时,晚唐五代时期,“朝代不断更迭,各个小朝廷间不断战争,内部皇位争夺中不择手段,背信弃义,亲属残杀,叛国弑君,卖主求荣等等,成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这时社会思想中的一个明显变化,便是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淡泊”(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罗宗强文集》)。与此对应的是重功利、主教化文学观念的式微,与重娱乐、主缘情文学思想的复归。于是上行下效之风日盛,社会各阶层在创作与传播曲词作品时,因上层雅好奢靡享乐,逐渐摆脱政教功用的思想桎梏,转而沉溺于频繁举办的奢靡宴饮。人们通过放纵无度的声色之娱,试图消弭乱世带来的惶惑不安。因而虽然同处国家危亡之际,南唐时代的李煜君臣进行词篇创作的目的与蕴藏其中的情志,皆与后文中南宋时代的文人集团大相径庭。
二、南宋时期的文本传播与文学特质
李煜词从南唐时期的歌妓传唱到南宋时期的印刷传播,经历了一个交叠演变的过程。据王铎《默记》记载,入宋为俘以后,李煜仍然保留着依调填词的习惯,只是全然不同于南唐君主时期的纵情声色。于是有了《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一时期的李煜词,情感真率诚挚,感慨深邃广渺。《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一词,《尊前集》在其调下注:“中吕调。”可知到此时,李煜词仍然可以通过演唱的方式呈现,具有一定的音乐性质。但由于李煜本人思想深度的提升,他入宋后的这些作品显然已然打破“词为艳科”的轻浮格调,大大拓宽了题材范围,升华了内涵题旨,有了明显的“士大夫”之词的色彩。
词在此时虽仍被当作“艳科”与“小道”,但由于创作与接受群体中高级官吏与上层文人的占比日趋增大,传播过程中的文人视域逐渐扩大。李煜词作为南唐词的代表,时常被北宋词坛评点化用。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引《雪浪斋日记》曰:“荆公问山谷云:‘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云:‘曾看。’荆公云:‘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又“细雨湿流光”最好。’”这里王安石虽把李璟词认为是李煜之作,但其加以品评的行为却可以证明,北宋文人对于李煜词的文学水准与审美价值是加以重视,予以肯定的。
及至南宋时期,这种交叉并行的传播方式又发生变化,进一步向文本化方向偏移。词与音乐关系在南宋时期的疏离,首要原因是南渡造成的乐谱散失、音乐断层。当时情形便如龙榆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后记》中所言:“宋南渡后,大晟遗谱荡为飞灰,名妓才人,流离转徙。”作为传播内容的李煜词被世事变迁所裹挟,成为诸多仅保存文字、佚失演唱曲谱的作品之一。进行演唱传播所需物质媒介的丧失,亦大大推动了其向案头阅读文本转化的进程。同时,在南渡“靖康之耻”未雪,半壁山河沦丧的社会背景下,南宋各阶层爱国主义高涨,“兴邦救国”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而一向与政治话题瓜葛甚少的词也在南渡爱国词人群体有意识的倡导与改造下开始承担书写家国情怀的使命。
同样面对动乱时局,宋代的南渡词人与南唐词人醉生梦死的软弱态度全然不同。他们重视其在抒情叙怀方面的天然优势,将词篇作为抒发其悲愤高亢情感与不屈斗争信念的渠道,李煜词的传播与接受形势也受到辐射。关于这一点,唐圭璋就在《唐宋词简释》中言道:“所以‘独自莫凭栏者’,盖因凭阑见无限江山,又引起无限伤心也…辛稼轩之‘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亦袭此意。”与李煜并称词中“二李”的李清照对其词也有赞誉与学习。李清照所著《词论》中评价李煜父子说:“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既表明了她对李煜父子词作的肯定与推崇,又反映出她面对相似时局下对词体社会功能、词人社会责任的思考,亦体现出她较之李煜所代表的南唐词人,更为入世积极的词学观念。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wxji20251296.pd原版全文
与此同时,南宋活字印刷术的技术逐渐纯熟,造纸技术也在不断进步。造纸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编印集册的成本大大降低,稍有家资的文人雅士也能够负担。且南宋时期对于词体的态度已经不同于北宋,北宋人收录文集的范围虽然相当广泛,但鲜有词集。不过,经过了数代词人的理论与创作建设,南宋时期的词体文学地位提升、文学价值也得到了认同。编定词集的做法由此逐渐流行。
故而到了南宋时期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中乐曲一类才首见《李后主词》书名,只是该本并未流传。此后,李煜词多与其父李璟之作合编为《南唐二主词》,以各版本流传。李煜词此时虽然仍保留着初时合乐而就的长短句式与浅近语言,但其文化功能却已然转变为供文人品评师法词学的参考资料,而再不是便于演唱的音乐底本了。至此,李煜词基本完成了从“口头之辞”到“案头之词”的变更。
三、李煜词传播方式的变迁折射出文学与音乐的矛盾斗争
李煜词的传播方式从五代时期全然由歌舞传播,到北宋时期歌舞演奏与文学鉴赏并行,再到最后彻底转变为文本流传的变迁过程,不仅受制于诸多外部因素,更受到词这一文体内部文学性与音乐性矛盾斗争的影响。
在最初的词体创作过程中,遣词造句均要“倚声填词”“按谱填词”。这是由词体诞生之初“词乐合一”的传播形式对其文本的格律要求造成的。这种要求被后人广泛继承,成了约定俗成的词体创作规则。
词体初期的传播形式中明显的音乐性使其迅速适应于娱乐消遣性的酒宴场所,以满足听众追寻感官享受的需求。但词体创作毕竟依赖于文字而非音符,其根本上属于文学创作而非音乐创作。随着文人尤其是官僚集团对词体创作参与度的提升,“词乐合一”“乐主词从”的情形必定不会长期存在。
五代时期,词体发展时间尚短,创作与评价标准尚未定型,且与音乐高度绑定,无法独立承担抒情言志的文学使命,难以与正处于唐代诗人成就余晖中的诗歌比肩,文学定位为“小道”。因而,以李煜为代表的创作与传播主体均以娱乐的眼光看待词体,乐于强调其音乐性而疏懒于文学水准。但在靖康之耻发生后的南宋时期,家仇国恨成了贯穿全民族各阶层的时代主题。词体发展到南宋,也已经具备了广泛的受众基础与创作人才,可堪成为文人抒发保家卫国之志的文学新途径。因此,在官僚集团有意识的参与和国家危亡的社会背景作用下,儒家的“政教”“实用”等文学观对词体创作的影响力逐渐增加,促使其带有娱情性质的音乐性日趋剥离,更具政教价值的文学性日益凸显。这样的变化反映在实践中,就是对词作创作方式与鉴赏视角的转变。南宋时期辛弃疾为抒发心中壮志,更主张“以文为词”,频繁用典,愈加违背词体依附于音乐演唱时通俗易懂、合乐可歌的原则。所谓“文字弦歌,各擅其绝。艺之材职,既有偏至;心之思力,亦难广施。强欲合并,未能兼美,或且两伤,不克各尽其性,每致互掩所长”(钱锺书《谈艺录》)。重心在于旋律悦耳的音乐与重心在于内涵语言的文学之间的关系,其实难以做到完全平衡与高度协调。一旦脱离醉眠温柔乡的浅薄创作环境,而进入文学,需要承担更为复杂深刻的表情达意之功能时,词体内部文学与音乐相互掣肘的局面便会暴露无遗。若要全然保留其动听悦耳的初始特征,就会“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沈义父《乐府指迷》);若想兼顾乐曲与文意,则“语工则音未必谐,音谐则语未必工”(赵以夫《虚斋乐府序》)。故而在南宋时期,面临词人群体越发慷慨纵深的情感表达与沉重宏大的时代主题,固定的曲调已经从原先表情达意的增益辅助变成了桎梏,所以才有“两宋词家虽多,其协律之作,实如凤毛麟角词之音律与辞章分离,盖自宋代已然矣”(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之言。
词体最终归向文学根茎的过程中,李煜词也逐渐剥离自身音乐性而转为阅读文本。这不仅由于此时乐谱散失、印刷书集盛行等外部因素,其自身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内涵与重要文学价值也是重要原因。李煜词虽已然完成创作,内容固定,但其情感丰沛真挚,前后差异甚殊,具有充分的解读可能,所以在南唐时期能够发挥其歌辞娱乐功能,南宋时期转换传播方式后又能作为阅读文本引起广泛共鸣与认可,流传后世。
传播方式由“口头歌唱”到“案头阅读”,文化性质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李煜词的创作虽然早已完成,其所承担的文化功能、承载的文学内涵却在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这不仅是因为李煜词的传播方式在不断顺应社会变迁而变化,也因为其作为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丰厚的文化内蕴,所以才能够承担不同时代的社会期待与解读,在南唐时期能够作为演唱歌辞满足视听之娱,在宋代社会能够逐渐升格文学定位,成为词体演进进程中承先启后的桥梁;所以才能够适应一动一静,一直接一间接两种截然不同方式的传播,成为我国词体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抹亮色。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梳理从南唐到南宋年间,李煜词的传播方式与文化性质的变迁过程,论证传播方式与词体文化功能的交互影响力,体察词体内部文学性与音乐性从共生和谐到矛盾分离的流变过程,一窥唐宋词从词乐合一到词乐分离宏观趋势中的内在推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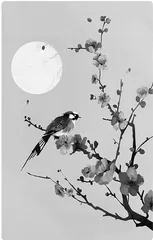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wxji20251296.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