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三国志》与《三国演义》 的人物形象变化
作者: 徐嘉辉 王浩宇从实证性研究的层面看,《三国演义》成书的主要史料基础是陈寿的《三国志》,正如又名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名称,其为《三国志》的通俗化演义。然而,《三国志》作为正史自然侧重于对人物生平功绩的描写,而《三国演义》则为通俗小说更偏向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从褒贬角度看,陈寿蜀汉旧臣、西晋官员的身份,名义上自然更偏向于曹魏为正统,具体篇目《三国志》纪传体的叙事格式也会偏向于对传记的主人公的正面描写;而《三国演义》作为通俗小说则更偏向于遵从民间之褒贬,偏向蜀汉为正统。加之《三国演义》较多地参照《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的内容,因此在故事人物的塑造上,人物形象相对于《三国志》出现了许多变化。本文围绕《三国演义》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形象变化进行浅谈。
一、刘备:“仁德”属性的强化
《三国演义》的刘备人物形象相对于《三国志》而言强化了对“仁”的刻画,情节上对此更为侧重,甚至部分情节进行了改造。相对于《三国志》中从社会底层爬起的枭雄形象,《三国演义》的刘备更像是一个汉氏血脉的“仁义君子”,一个理想化的明君形象。因而,在刘备故事情节的处理上,《三国演义》并不完全遵从真实性,进行了艺术化的改造。
《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结义,斩黄巾豪杰立首功”便是出于虚构。《三国志》中仅有对刘关张三人关系亲如兄弟的描写,并无对结义的提及。后代对此有“王及车骑将军飞与昭烈为友,约为兄弟”(郝经《重建庙记》)的表述被认为是这一传说的雏形,但表述来源于元初,并非史实。文中“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结义之誓强化了对刘关张三人忠义的刻画,而在《三国演义》的第一回出现,则隐含了作者乃至明初社会“尊刘”的基本思想倾向。至于《三国演义》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三国志》中的督邮则为刘备所鞭。惩治督邮,明明大快人心,为何改为张飞所鞭?《三国演义》的改写可以理解为刻画刘备仁慈的一面,凸显其正面形象。与此同时,在第四十一回“刘玄德协民渡江”中刘备撤退时“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而后因百姓伤亡而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无不表现了刘备对百姓的关爱与仁慈。刘备因爱惜赵云而不忍劝他离开公孙瓒;对于孤军驻江北而无奈降魏的黄权,刘备对其家属进行了善待。这些细节表现了刘备对待部下之信。当然,刘备“仁德”属性的强化与《三国演义》“尊刘”的主题相适应。
然而,《三国演义》的“美化”,尤其是清代毛本的塑造,使得人们对于刘备的认知更像是空泛苍白的仁德,正如陈松柏《刘备形象塑造的尴尬》中所称:“聪明反被聪明误,净化得过于纯洁。”据笔者统计,《三国志》中明确记载的刘备之哭总计有六次,而《三国演义》中则添加至三十五次,其中虽然不乏听闻关羽和张飞去世之哭,以及白帝城托孤之哭等经典,但整体而言反而将刘备的形象刻画得稍为软弱。与此同时,《三国演义》中刘备数次被部下劝说夺取荆益二州,却以“但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皆汉室宗亲,备安忍夺之?”为由推辞。虽然罗贯中本意润色这段剧情以此突出刘备“明君”形象,但更多人反而觉得其虚伪。
而从刻画的形象看,《三国志》中仁义与枭雄色彩并存的刘备,或许比《三国演义》中有些许道德瑕疵的“圣人”刘备更具人物魅力。沈伯俊《枭雄与明君——论刘备形象》曾评价:“过分淡化刘备的枭雄色彩,无形中降低了刘备作为刘蜀集团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使这位历尽艰辛的开国明君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因而,《三国演义》中刘备宽厚爱民与仁德敬士的形象无疑是成功的,其也成为这些品质的代名词。然而,也是因为与这些品质的高度绑定,刘备的形象也失去了《三国志》中草莽英雄的立体性,人物的形象反而显得较为扁平。
二、曹操: “立体化人物”之典范
与刘备的形象在《三国演义》中的扁平化恰恰相反,曹操在《三国演义》的形象相对《三国志》而言,反而更为立体丰富。“狡黠多疑”“多谋善断”“奸诈残忍”,这些形容虽然与曹操的主要描写相切合,但仍然难以准确形容曹操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多面形象特征的人物,我们不妨先从《三国志》的角度看曹操这一人物形象。
《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作为曹魏政权的接力者,西晋自然尊魏为正统,因此《三国志》不可避免地受价值观影响,对曹操的正面历史功绩进行肯定,而对其存在的过失而曲笔。《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录了桥玄对曹操的评价:“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而作者陈寿是这般评价曹操:“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褒扬的成分较高,但曹操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以及取得的巨大功绩,也能够与这些评价相匹配。然而,对赤壁大战的失败的叙述却只有寥寥几句:“公自江陵征备…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而南朝的裴松之注则对《三国志》进行了查缺补漏,矫正谬误。对于年少时的曹操形象,其引用了“装病诬叔”的故事,表现了青年曹操的放荡不羁和智谋权术。当然裴松之的补注相对陈寿的原著而言受时代影响小,因此对曹操奸诈的性格加深了一些刻画,如裴注丰富了“许攸来降”“曹操诈粮”的情节,使得曹操的形象趋于立体化,不再像《三国志》原著中那般高大但扁平。
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的刻画,立体程度无疑更上一个台阶。面对国之大患董卓,群臣无助之际,曹操出于义愤,借七宝刀行刺董卓,被发现后以“献刀”之命化险为夷。尽管并未成功,但其本人忠勇和机智的形象跃然纸上。在人才察举方面,曹操唯才是举,以能力为任贤之标准,即使是“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郭颁《魏晋世语》)的有道德污点的程昱,还有导致“文和乱武”这一灾难与引发“张绣叛乱”的贾诩,曹操都能容纳之。对人才大度宽容,显示了曹操顾全大局的一面。而官渡之战则是曹操正面性格集中展现之处:粮草将竭,他仍故作镇定,安稳军心;军势颓危,他仍能对“宛城之围”的惨败谈笑风生;面对旧友许攸不知真假的消息,“袁绍军粮辎重,尽积乌巢”,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并抓住时机扭转战局。而袁绍因小儿病危而无心用兵,激反谋士许攸,逼死贤臣田丰的优柔寡断与刚愎自用之形象,也对衬托曹操的英明神武有一定作用。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光辉亮丽的形象并非主流,更多的情节展现的是他狠辣的负面形象。在误杀吕伯奢的情节中,曹操因“庄后有磨刀之声”和“缚而杀之”的言语而怀疑并灭门吕家,而后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此处情节虽短,但曹操多疑而残忍,狠辣且不义的性格特征便清楚地展现出来。而对曹操多疑性格最典型的描写莫过于第七十二回的“梦中杀人”,近侍在曹操睡时为其盖被子,“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醒来之后却故作“何人杀吾近侍?”并装作痛哭而厚葬之。为了自己睡时的安全,不惜杀近侍以杀鸡儆猴,此时的曹操无疑是多疑而狠辣的。至于曹操权倾天下后,以不孝之名诛孔融,以乱军心之命杀杨修,乃至先后间接逼死反对其加九锡、封王的荀或和荀攸,颇有“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之态。当然,通过这些刻画,曹操冷血自私、奸诈残忍的形象也更加深入人心。
总体而言,《三国演义》中塑造的曹操既是谋略果敢的军事家,也是诗风慷慨悲壮的诗人;既是冷酷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也是残忍狡诈的野心家。错综复杂的个性在他的身上融合,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立体的曹操形象。正如沈伯俊先生在《再论曹操的形象》中评价的:“对于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人们应当肯定其历史功绩,也有权批判其恶德劣行。”也正如许劭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
三、周瑜:小说改编的“牺牲品”
在《三国演义》的改编中,刘备、曹操形象与《三国志》中刻画的人物形象即使有所差异,人物整体塑造也并无大变化。然而《三国演义》的改编,周瑜形象的塑造对比《三国志》无疑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三国志》对于周瑜人物的塑造,无疑是极其正面的。在《周瑜传》中,周瑜未出山时,袁术欲使之为将,而周瑜并未就职,反而“故求为居巢长,欲假涂东归”,选择辅佐粮少兵稀的孙策。这一独具慧眼的举动使得他不仅与此后狂妄称帝众叛亲离的袁术相脱离,同时也使得孙策渡过难关。周瑜未及三旬便随孙策平定江东,奠定了他在孙吴的重要地位。这充分地体现了周瑜的目光长远与出色的军事才能。而面对平定北方的曹操要求孙权送来质子时,周瑜仔细陈说曹操意欲以此控制东吴的企图,并以楚国为例劝谏孙权割据一方,也能看出他高超的政治智慧。
《三国志》也对周瑜的心胸宽广有直接的描写。在孙策落魄时,身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周瑜仍与孙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以兄弟之礼待之。而面对“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的老将程普,周瑜却能“折节容下,终不与校”,使得程普也不禁称道:“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如此豁达的谦谦君子形象,加之横溢的军事与政治才华,也无愧于苏轼之刻画:“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橹灰飞烟灭。‘
而《三国演义》中对周瑜初登场时的刻画无疑是极其惊艳的:“当先一人,姿质风流,仪容秀丽。”正可谓真人臣矣。而后他推荐二张,以三面围城之法擒太史慈,乃至孙策去世后稳定孙吴政局,安心辅佐孙权。此时的周瑜形象与《三国志》相近,是极为光辉的。但在赤壁之战后出场的周瑜,尤其是在跟诸葛亮同时亮相时,在情节的改编上,他无疑是成了“可怜的牺牲品”,才能平庸,嫉妒贤才,不顾大局一次次与诸葛亮内订。乃至在第四十四回,周瑜听闻曹操驱众南侵,竟说出“曹操以天子为名,其师不可拒。且其势大,未可轻敌。战则必败,降则易安。吾意已决,来日见主公,便当遣使纳降”的投降之语,直至诸葛亮道曹操欲娶二乔而怒发冲冠,以求出师,全然是意气用事的匹夫形象。至于大敌未胜,他便因嫉妒先后以“十日筹箭”“争夺南郡”“借道灭蜀”,乃至让主公之妹为饵诱杀刘备。周瑜的种种行为让老好人鲁肃都自思曰:“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
而在如今,学界对于《三国演义》中的周瑜主要的探讨方向有两点:一是周瑜是否心胸狭隘;二是周瑜形象的刻画是否为失败的。
关于前者,主流看法认为《三国演义》赤壁之战时刻画的周瑜是心胸狭隘的,当然这样的刻画才能使得“孙刘联盟”显得更加矛盾重重,使得赤壁之战与争夺荆州的斗争更加错综复杂,从而更好地突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和力挽狂澜。从小说的角度看,这是为主要人物的人格魅力服务,从而使得主要人物正面形象达到最大化,因此罗贯中不得已而为之。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周瑜奉孙权旨意,而非气量狭小,如邱少成在《〈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周瑜形象比较研究》中认为“周瑜对于诸葛亮的‘妒忌’实际上是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然而至少在赤壁之战结束前,本该同心协力的东吴与刘备集团,出于生死存亡之际,却本末倒置内订不断,将之归纳于“让刘备、诸葛亮参与筹划抗曹大计,无异于引狼入室,养虎遗患”(杨绍华《论周瑜》),未免过头。以寡敌众,此时的周瑜岂有十成把握获胜,进而达到可以肆意打击盟友的地步?
至于后者,个人认为,周瑜的性格割裂过大,在艺术层面反而成为小说改编的“牺牲品”。即使是在与诸葛亮斗智斗勇屡战屡败,敌对曹魏时,我们也能看到周瑜闪耀的瞬间,“伪书诈蒋干”“诈死取南郡”,他思谋精密,运筹帷幄。然而在面对诸葛亮时,他却变得鼠目寸光,屡屡因私废公。时而是有雄才大略的谋士,时而是锱铢必较的小人,两个性格迥异的形象强行拼接在一起,难免使得一些读者难以接受。《三国志》中一般正面刻画的谦谦君子,“尊刘贬曹”派民间杂剧中刻画的浅薄小人,作者都欲有所保留,就如“小说作者对两种素材都不愿舍弃,但又无法糅于一体,于是只好把两个迥然不同的周瑜形象硬拼合到一起”(杨润秋、苗怀明《丹青圣手还是艺术败笔一《三国演义〉周瑜形象得失新探》),在正史的基础上实现“尊刘贬曹”式小说化,周瑜形象便不可避免地“牺牲”了。
本文对《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曹操、周瑜的形象变化进行了探究,对于其人物刻画的得失进行了初步分析与探讨,在“尊刘贬曹”、民间改编等层面分析《三国演义》变化之处的由来。《三国演义》在正史《三国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小说化的改编。《三国演义》在人物的形象刻画上较之正史有得有失,或有歪曲之处;但在小说的角度看,其无疑是极其成功的,其在故事性充足的情况下,仍能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人物塑造力,瑕不掩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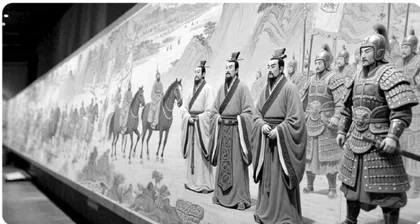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wxji20251297.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