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文学”视域下的李钰诗论探究
作者: 杨吴笛“弱势文学”概念的谱系学考察可追溯至卡夫卡(1883—1924)关于小说创作的日记,用于描述他在早期写作中发现的文学语言的潜能。德勒兹与迦塔利在《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中重构了这一概念,将弱势文学的特质概括为生成于结构秩序化的主流文学体系内部的文学新范式,既在主流话语内部产生,又对抗和疏离于主流,具有辩证的双重属性。由于写作方式的少数性和边缘性,卡夫卡成为弱势文学实践者的代表。
李钰(1760—1813,一说1760—1815),是朝鲜朝后期重要的诗人、文学家和小说家。其祖籍京畿道南阳梅花洞,出身失势的武班庶族,字其相,别号花石子、梅花外史等。终其一生,李钰始终坚持使用被统治阶级贬斥的少数文体写作,为此仕途阻绝,屡遭流放。无论是李钰被边缘化的生命经验,还是文本不见容于当世的命运,李钰不被主流收编的其人其诗,都与“弱势文学”理论高度契合。在“弱势文学”视域下对李钰诗论进行阐释,对解读朝鲜朝后期文学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变革有启示作用。
一、李钰诗论形成的基础
在集中体现李钰诗学理论的作品《百家诗话抄》和《俚谚》中,作者阐释了自己文学创作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突出的特点是解构传统的革新意识:历时性层面上反对因循拟古,共时性层面上反对一味慕华;强调诗歌应以表现真实情感为归宿,显现出关注个体生存境况的现实主义倾向;主张使用谚文俗语和“熟典”,在与中国语言的差异性中体现朝鲜文学特色。下文现就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对该诗学理论的发生学基础进行分析。
(一)作者的生命体验
从主观方面看,在对待主流文学的态度上,李钰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迥然相异。
李钰的作品不见容于当世,未曾收入别集,身后才被收录进由金鑪编写的《庭丛书》,可见其边缘文本的属性。对李钰的人际交往关系进行考察,亲朋至交多为使用边缘文体进行创作的文学家,如编写《庭丛书》的金、编纂野史丛书《大东碑林》的沈鲁崇等人。
在文学创作中,李钰使用了丰富的体裁,不仅有书、序、跋等常见文类,还包括俚谚、文馀、戏曲等,其中就有朝鲜朝最早的戏曲《东厢记》。对于李钰的创新,金鑪给予了极高评价:“见吾友李其相之为文词也…或嫌其时用方言俚语,以为文字之一疵,然大抵了无生涩、牵强之态,真可谓一时之奇才也。”(金《潭庭遗稿卷之十·题花石子文抄卷后》)对李钰来说,“长篇大文、短篇小闋”是构筑平滑空间的媒介,它们时刻处于流动和偶然之中。不同的描述对象在非四六骈体的“真诗”洞穴中穿梭,多种文体以流的方式打破壁垒,逃出传统的捕获,规避可能的停滞腐朽。
遭到来自国家机器的排斥后,李钰并未屈从权力规训,始终忠于自己的诗学理想。如此,他的文学创作从固化的框架中逃逸,不再汲汲于唐宋范式,而是在融贯了俗语、边缘描写对象以及真实生命体验的平滑面上流动生成。
(二)时代的思潮更替
从客观方面看,18世纪中后期社会剧烈变革的背景下,新旧思潮的更替为李钰诗学理论的形成做了现实的铺垫。
该时期,朝鲜资本主义萌芽肇始。在意识形态上,朝鲜朝前中期占宰制地位的性理学学说流于空疏,地位下降,实学、西学思想逐渐盛行。17世纪后,朝鲜朝经历壬辰“倭乱”、丙子“胡乱”,乾嘉学风传入,实学成为朝鲜士林的思想潜流。时代稍前的丁若镛、朴趾源等实学派学者开始摆脱传统的性理学文学观,燕岩文学论即为其中代表性的例证。
朴趾源反对当时朝鲜拟古和仿中国的文风,主张文学应追求“真”,体现真实的朝鲜国风。李钰与朴趾源生活在同时期的朝鲜,虽无直接交流的记载,但两人的诗学思想在民族文学自觉的面向上具有一致性。
对李钰诗论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有两个,一是朝鲜朝后期的诗学革新。在实学派文学观的指导下,朝野文坛呈现多种文体并存的格局,包括官僚骈体文及拟古文、经世致用派的六经古文、利用厚生派的时宜文,以及李钰等人使用的稗史小品体。二是“文体反正”事件。朝鲜朝后期,正祖为巩固政治统治理念,在思想上主张宋明理学,指斥以晚明小品为首的文体“噍杀奇诡,实非治世之文”(《正祖实录·十五年十一月七日》)。正祖十六年(1792),李钰在成均馆应试的策文中使用稗史小品体,被正祖认定为“不经之文”。三年后,李钰再因文体问题被罚以“停举”,流放至忠清道。其后,李钰应试京科,又因文体“怪异”,发配至庆尚道三嘉县充军。翌年,李钰在别试中原本名列状元,因文体与正统相悖,被降至末,再遭流放,直至1800 年获赦回汉城,此后隐居南阳著述,郁郁而终。
由于“文体反正”政策,李钰文学观中“表现真实的、对古文具有超越性的”理想文体成为被禁止、被治理的对象,而作者本人的生命历程亦饱受牵连。
二、李钰诗论中的“弱势文学”特点
“弱势文学”(littératuremineure)是卡夫卡在日记中提出,由德勒兹和迦塔利进行系统概念化的文论思想,“是一个少数族裔在一种主要语言内部缔造的文学”(《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其核心特征并非指向创作主体的族裔身份,而是通过文学创作内在的“弱势族性”,对文学共同体的固有表述形式、政治功能和价值判断进行超克。弱势文学构建起了块茎式的文本繁殖体,与艺术的、游牧的、边缘的、政治的抽象机器联结,在克分子线、分子线与逃逸线相互转换的张力中,随时断裂、重组,生成新的融贯性平面。
以“弱势文学”为逻辑起点,对重构文学的创作批评历史有启示作用。李钰诗论的“弱势文学”特点可以从三个面向加以解读,即对强势语言的解辖域化、一切与“政治”相关联,以及表述的集体性配置。
(一)解辖域化:反传统的诗歌作为逃逸线
“弱势文学”指“栖居在语言中的一种方式,是小族群挪用大族群语言并破坏其固定结构的一种途径”(罗纳德·博格著,石绘译《德勒兹论文学》),生成于强势文学内部,二者使用同一构件,在弱势的变化中,不规范的用法对占据宰制地位的规则进行解构,因而意味着文学的革命。
首先,在有关诗歌本质的论述上,李钰从主流的“性情之正”转向“性情之真”,提出“诗难其真”的主张。李钰的《百家诗话抄》几乎照搬袁枚《随园诗话》,但为了突出自己的诗学理念,李钰对袁枚的部分诗学观点作出修改,如将“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矣”改为“诗难其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俚鄙率意矣”(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卷六·百家诗话抄》)。袁枚在强调诗歌保持性情之真的同时,要求“学问”表现形式的雅化,而李钰的改动,单方面强调了“真”的重要性。
李钰《宕调序》有言:“宕者,迭而不可禁之谓也。此篇所道皆娼妓之事,人理到此亦宕乎不可禁制,故名之以宕,而亦诗之有郑卫风也。”该类诗歌在主题与风格上都是“变调”,但李钰强调它们与《诗经》中的《郑风》《卫风》一样,具有抒发真情的价值。又如《悱调序》写道:“《诗》云,小雅,怨而不悱。悱者,怨而甚者之谓也…此悱之所以有作,而悱者所以悱其宕也。”对于传统诗歌,“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是基本法则。但李钰指出“怨而甚者”才是真实情感,所谓使风格显得“薄陋"的对象,有着成为诗歌题材的天然合法性。
XHID W nhrr
其次,在创作方面,李钰反对因袭秦汉唐宋,主张使用体现本民族特色的谚文俗语。在用词上,李钰主张言文一致,反对拟古,表明“吾今世人也,吾自为吾诗吾文”(《题墨吐香草本卷后》),要写作“今时此地”的诗文;也反对一味慕华,在《俚谚·三难》中用模拟问答的方式,对诗歌表现自我、表现民族特征的必要性进行阐释:“或以俚谚中所用服食器皿,凡干有名之物、无名之物,多不用本来自名称,以妄以己意傅合乡名,用之文字也,以为僭焉,以为诡焉,以为乡音焉。余曰:‘是然矣。然则,我之犯是科也,久矣彼以彼之所名者名之,我以我之所名者名之。’”
以上诗论都在针对传统诗学进行解辖域化与反叛,同时在创作范式的差异中生成新的内容、风格,体现出弱势文学的表达方式。
(二)与“政治”关联:男女之情为天地万物之观
“弱势文学”概念中“政治”的概念与中文通常语境的“政治”含义截然不同。弱势文学中的一切与政治挂钩,是指弱势文学中人物的个人问题总是与更大的社会的、非社会的环境相关联,向万物敞开自身,如与商业的、官僚的、司法的等其他的多重关系产生关联。因此,弱势艺术的诉求不在于政治学意义,政治本身并不关乎政治,而是连通了生活的、社会的、非人类的方方面面。弱势文学期待并实践着大众化与内在性,表征出“根茎”的普遍连接性原则。
李钰《俚谚·二难》有如下论述:“夫天地万物之观,莫大于观于人;人之观,莫妙乎观于情;情之观,莫真乎观乎男女之情故其心其人,其事其俗,其土其家,其国其世之情,亦从此可观。”李钰以对男女之情的肯定作为切入点展开阐释,将诗学理论自身与天地万物、与抽象的社会国家机器相关联,在一个融贯了“其事其俗,其土其家,其国其世”的开放平面上生成诗歌,正与弱势文学中一切与“政治”关联的特性相照应。
(三)集体性配置:从“文以载道”到委巷之诗
“委巷”一词初见于唐代刘知几《史通》,这里的委巷诗歌论,指洪世泰、赵秀山等中人阶层为代表的委巷诗人的诗学理论。李钰的诗学理论,与委巷诗歌论同样重视刻画市井生活的真实。“集体性”意味着弱势文学的功能在于集体表达。在弱势文学中,任何个体皆是通过集体而存在。卡夫卡并非孤独的自我折磨的艺术家,而是政治的、群体性的作家,K(卡夫卡小说《城堡》《审判》中主人公的名字)并不指代叙事者或故事人物,而是代表一种装配。在此意义上,德勒兹与迦塔利把表述的集体性配置视为正在建构中的民族的先驱。弱势语言使作为共同体主导规则的强势语言解辖域化,弱势用法直接参与表达的集体装配,创造出一个未来民族的声音。
集中阐发李钰诗学思想的《俚谚引》肯定了诗歌在本体论上的意义,让诗歌从中世的载道文学观中解脱出来,关注对象从既成观念的“道”转向具体现实的群体。在《俚谚·一难》中,李钰通过虚构人物问答的方式,解释为何要创作自己的“俚谚”,而非效仿主流推崇的中国的《诗经》和乐府诗:“余对曰:‘是非我也,有主而使之者。吾安得为国风、乐府、词曲,而不为我俚谚也哉?此吾之亦不可以不有所作者也,亦吾之所以只作俚言,而不敢作桃夭葛覃也,不敢作朱鹭思悲翁也,并与烛影摇红蝶恋花,而亦不敢作者也。’”此处的诗论阐释了两个核心思想,一是创作“民族自觉的文学”的合理性,二是创作“面向群体的文学”的必要性。通过“是非我也,有主而使之者”的集体装配,李钰诗论在民族意识自觉中生成相对于清朝的他者,传达出市井群体众声喧哗的普遍语言。
《百家诗话抄》与《俚谚》集中体现了李钰的诗学理论,最为突出的是解构传统的革新意识。在“弱势文学”视域下,李钰诗论是对强势文学的解辖域化,是一部与“政治”关联、向万物敞开的文学机器,在表述的集体性配置中,裹挟市井语言的喧哗,成为民族意识自觉的先声。
在新旧思潮更替的朝鲜朝后期社会背景下,与主流话语对照处于弱势地位的李钰诗论,在接受清代性灵派思想的基础上,既在传统儒学框架中构建,又对主流“性理”文学观进行反叛,在结构化的固有文体中生成俚谚、文馀等新兴文学类型,以解辖域的语言观念、融贯旁逸的普遍联系和民族集体的独特价值,回应了历史转折时期文学对于自我突破的关切,承启着朝鲜中世文学到近代文学的过渡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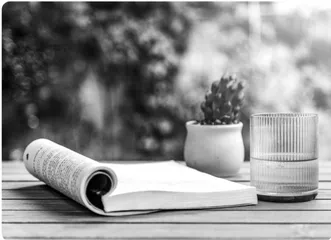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wxji202512112.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