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病同行是怎么通过汽车股赚30倍的
作者: 崔鹏在众多行业领军人物中,最有趣的群体是哪一个?
要我说,是车圈的。
那些车企掌门人,一边忙着制造汽车,丰富我们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还会整各种活丰富我们的精神文明。他们几乎个个文可提笔万言讲演带货安天下,武能装疯卖惨捧杯喝酒骂大街。
他们有一个特点,爱和别人结成战略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里有同行,有上下游,有金融机构,有体育俱乐部,遍布五行八作。另外,他们也爱和人吵架,会因为用的电池不是一个路子的事儿来吵,因为充电方式不一样吵,因为车门朝上开还是朝两边开吵。
他们最近一次吵起来则是为了欠账的事。
这里所谓的欠账,其实主要指的是车企对供应链企业的欠账。
造车产业链里似乎有这么个规矩,整车品牌商先从配件商那儿拿货,然后可以隔相当长的时间再结账。拖欠这类账的能力最强的是比亚迪。从去年年报看,它的总负债约为5847亿元,看起来真的挺吓人的。但其中主要是这种供应链欠账,在资产负债表上记作应付票据和其他应付款。它真正欠银行和债主的有息负债只有大约286亿元,还不到总负债的5%。然而比亚迪把配件商的平均结账周期拖到了接近6个月。
其实,整车品牌商欠汽配商钱,而不是反过来,并非来自法律规定或者有关部门的指令,这是汽车生产这个链条中的上下游不断博弈的结果。之所以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一个关键原因是汽配商太多了,市场竞争使得他们不得不同意赊销。而且很明显,这种欠账对汽车厂商有好处。但就像我们前边说的,车圈的人特别爱吵架,哪怕是对同行都有好处的事,他们也要分成不同派别,欠账少的会鄙视欠账多的,账期短的会指责账期长的。
指天誓日要全体同行把账期缩短到60天的车企管理者有点像评书里提到的码头时代天津的混混,后者在和同类发生矛盾时会先从自己腿上割下一条肉,扔在对方面前,意思是“你敢吗?”。
而被逼迫的一方就像《骆驼祥子》里的虎妞她爸爸刘四爷跟人吵架时候的做派:前腿弓,后腿绷,大拇指指着自己的秃脑门,“上这儿来找便宜?我往外掏坏的时候还没有你呢!”—刘四爷是开人力车行的,也算是车圈的老前辈。
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这轮争吵似乎开启了一场压缩供应链负债账期的运动。可这事真的对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有好处吗?未必。
有的评论者似乎认为恒大爆雷正是因为对自己的供应链企业大额欠账,所以现在所谓的比亚迪的迪链、长城的长城信链似乎也都成了坏东西。
但这很可能是把事情的因果搞反了。恒大爆雷真的是因为拖欠供应链账款吗?肯定不是啊。它最重要的问题是一方面融不到资,另一方面房子又卖不出去。
现在的很多大车厂的供应链金融平台,就是起到了为车商提供融资的作用,抑制这些平台的功能,然后还限制车厂在零售端的自由定价权(不许整车品牌商随意降价),这两项加起来才真正增加了车企爆雷的概率。
在这场关于账期的吵架中,有人特别推崇特斯拉的供应链60天账期,并拿海外大车企来对比,因为它们的此类账期都在60天左右,似乎60天早就是一种“国际惯例”。
这种看法有点莫名其妙。欠账周期这种东西哪有国际惯例。海外汽车厂商不能把账期拖那么长,是因为它们在和上游供应商的博弈中无法取得强势的地位。如果能拖延,我猜它们也会那么做。
汽配商和整车供应商是硬币的两面,缩短账期的确会让汽配商得利。但如果从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来看,还是让市场决定让谁拿更多更恰当。竞争过度,导致一些汽配商被淘汰,本身是很正常的事。而汽车厂商如果因为账期挤压出了问题,反而会连带引发社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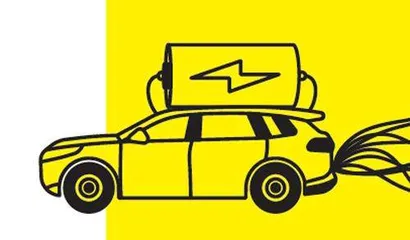
当然了,说了这么多,汽车厂商相互攻讦,汽配商和汽车厂商之间的博弈变成社会热点,原因可能是同一个:买车的人没那么多了。
由于新能源汽车普及和自动驾驶技术迭代,人们很可能忘了一个事实,汽车业,即使新能源汽车逐渐占据主流,仍然是个强周期行业。就像人必然会死一样,一个强周期行业必然会迎来周期顶部,然后开始下滑。这个顶点具体会出现在何时非常难预测,不过,车圈掌舵者们吵架的激烈程度应该是个指标,他们互相指责谩骂得足够激烈的话,周期性的显现大概就不远了。
说到这,扯两句闲话。
还记得前几年的地产巨贾吗—为什么说前几年呢?因为现在除了王石偶尔会羞涩地出来卖卖燕窝,其他人就像冬天的鼹鼠一样,根本不露面了。可是无论地产行业处于高峰还是低谷,他们都没有互相攻击过,反而,圈子里有谁遇到困难的话他们会集体出手相帮。不同圈子之间的气氛差距真大啊。
说回投资吧。投资者应该怎么应付汽车这类强周期行业的公司呢?
全盛时期的彼得·林奇曾经给过一个不错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大概是,在汽车公司的股价处于高位时不要购买,那样做是有点危险的—汽车股现在的股价就属于危险范围吧。
1980年代初,美国车被石油危机和日本车挤兑得不行,克莱斯勒公司眼看就要破产了,彼得·林奇趁着这个节点买入了克莱斯勒的股票。其后的5年间,林奇在这只股票上赚了1500%。
为什么能赚这么多,林奇总结了三个要点。
第一,这家汽车公司要具有大而不倒的属性。“大而不倒”,不是说大就行了,它还要不倒—这句不是废话,这种例子在钢铁行业就有。有的钢铁公司,其工厂宛如一座城市,在周期底部时,这种公司亏损严重,但由于其社会价值,它是不可能倒闭的。这种公司适合投资者在其股价非常低的时候投机获利。
第二,这家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本来是相当出色的,它的情况变得很糟,只是因为周期性—这样的公司即使最后没能从周期性的泥沼里爬出来,被收购的几率也很高。
第三就是公司的股价足够便宜,甚至远低于其净资产价格。当年的克莱斯勒就是如此,林奇的买入价格是6美元/股。另一位厉害的投资者安德烈·科斯托拉尼也参与了那场投机,且买入价格更低,只要3美元。
科斯托拉尼除了是个伟大的投资者,还和我一样,是个专栏作者。我俩不一样的是,他是得了精神病以后才开始写专栏的—令我欣慰的是,并不是写专栏导致了他罹患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