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史背后的三张面孔
作者: 曹俊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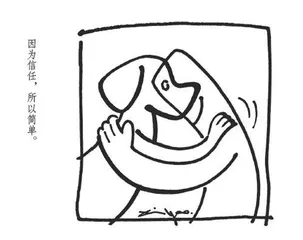
在生态危机接踵而至的时代背景下,以及对“人类世”(亦译“人新世”)概念的广泛讨论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以一种整合视角,思考人与地球的关系。近年来日渐兴盛的“大历史”“全球史”和动辄纵贯万年以上的人类“演化史”书写,正是其中引人注目的重要探索。著名的环境史奠基者,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最杰出的旗手—唐纳德·沃斯特(中文名:唐沃思),试图借助孟子口中的“食色之性”,复活其早年提出的“行星史”概念,从人与其他物种共享的内在自然(inner nature)出发,阐幽发微,推衍广大,对二十万年以来人类走出非洲、发明农业、建立国家、发现美洲、开启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历史进程背后的根本性驱动力,展开了别开生面的思想构建。
唐沃思的行星史,不同于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要去描绘会讲故事的人,也不同于大卫·格雷伯的《人类新史》,要去强调有能动性的人,而是去呈现要吃饭、想择偶的“自然之人”。书写这样的自然之人,又不同于贾雷德·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想要凸显人猿的差异,还不同于伊恩·莫里斯的《人类的演变》,主要探讨文化价值观的由来。他要做的是,抛开前人不离其宗的“文化”,剔除自然演化的“差异”,寻找物种演化上的最大公约数,书写始于肠胃和性腺,经于生产和繁殖,终于人口和资源的“新自然史”,旨在挑战当前充满自负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人新世话语,极富思想张力。然而在这样一种对人类历史的再自然化过程中,唐沃思又难免矫枉过正,以致其论证逻辑潜藏着诸多难以弥合的矛盾,呈现出多样分歧的思想面孔。
并非达尔文的“达尔文”:性和内在自然
最为重要的一张思想面孔无疑是达尔文。过去的一百五十多年以来,物种演化论被扩展为解释宇宙万物起源和发展的理论基石。但争议之处在于,是否也要把人包括进来?如果说人文学者总是倾向于把人从自然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化的例外,那么行星史则希望将演化论贯彻到底,把人类的自然性从层层包裹的文化外衣中翻出,并以此作为人类历史演化的主要驱动力。为此,唐沃思认为,需要“将人类与地球的其余部分进行更充分的达尔文式整合”。
虽说是达尔文式的整合,唐沃思所要发掘的,却是达尔文“鲜少注意过”的性行为和繁殖力,并为其赋予新的概念—内在自然。所谓内在自然,是“人类体内的驱动力”,一种与其他物种所共享的“生理需求与渴望”,尤其体现为对食物和性的欲望。内在自然在不断演化中指导我们的行为和思想,文化是独立于内在自然的后天习得,目的在于协调内在自然与外部环境关系。在他看来,不是文化,而是每一个人最熟悉却又最避而不谈的性,才是历史进程的首要驱动力。
在挑明了达尔文极力遮掩的性驱动力后,唐沃思将人的历史视为一部以生存和繁衍为目的的自然经济史,并勾勒出一幅由“肠胃和性腺驱动”的人类演化图景:史前人类走出非洲,艰难地移民扩散,是“因为他们生育了太多的宝宝”;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也是被“内植于人类自然中的强大繁殖本能所驱动的”;欧洲人之所以发现新大陆和开启工业革命,则是“在同一片土地有如此之多的人口需要喂养”。换句话说,在二十万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总是一副随意发情、乱生宝宝和始终饥饿的模样。
对此,考古学家布莱恩·海登恐怕要举双手反对。他提醒我们,史前人类从来不是只为食色所驱动,农业也不总是因为人口压力而出现。相反,他们懂得巧妙将人口控制在与资源相适应的水平上。这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花大力气种地以糊口。如果看一看最早驯化的植物,诸如增加食物风味的辣椒和制作酒饮的谷物,就大概明白了,发明农业似乎不只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请客吃饭”!通过宴飨,史前人类可以积累用于超越竞争对手的奢侈食物,从而获得声望和权力。这些例子,或许可以表明,往往是人性中的复杂追求,而非一再重复着的内在自然,才促成了人类历史复杂性的跃升。
不同于达尔文将道德视为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唐沃思把包括道德在内的文化,视为内外自然互动中的“变异体”。文化在演化上没有善恶对错可言,一切都是为了适应。于是,作为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逐利文化进行尖锐批判的环境史学者,如今他却“不再对资本主义做出对错与否的褒贬”。他今日眼中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变成他自己曾经批判过的魔鬼,反而带来了理性和有效实现“性育分离”的现代医学实践。于是,当唐沃思不遗余力,把人类演化史塑造成由内在非理性冲动主导的历史之际,恰恰隐含了他最大的价值判断:不加控制的内在自然并非那么美好,它终会带来人口扩张和地球萎缩;相反,理性才是人类自我救赎的关键,而这样的理性正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带来的。
由于未能澄清内在自然如何演化、文化如何协调内外自然,最终,文化在行星史的书写中,成为独立于人的“另外一种物种”。文化与内在自然的脱节,使本身无法逃离文化属性的人,也无法完全属于自然,这偏离了达尔文的本意,也偏离了其在《人类的由来》中,对自然—文化关系的盎然兴趣和道德坚持。唐沃思所谓的“达尔文式整合”,代表的是现代生态学以来的新达尔文主义,以一种看似科学中立的态度,在让文化批判有意识缺位的同时,实则隐藏着更深的价值判断。
反马尔萨斯的“马尔萨斯”:教条化的人口压力论
在把人口压力与资源限制之间的博弈作为人类演化史缩影时,一张大大的马尔萨斯面孔也随之浮现出来。不过,唐沃思与马尔萨斯有着基本分歧。马尔萨斯反对进化论,他以上帝的旨意来解释人的性渴望,并机械地设想,人在环境好的时候,会秉承上帝意愿,不断繁殖直到环境盛不下。唐沃思则认为,性驱力是自然演化出来的,且演化的方向不可预测。一个例子便是如今在发达的国家,即使有优越的环境,生育率反而大大下降了。
不过,在剔除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神学主张,指出了其所未能预测的当今人口现状后,唐沃思仍是一个十足马尔萨斯主义者。他同马尔萨斯一样,认为任何历史进程和文化现象,都根植于现实的物质性土壤,而人口压力又会破坏这种土壤。而且,由于过于强调性驱力,他同样也将人口压力一股脑都怪到了“生育了太多宝宝”之上。当他将人口简化为仅仅关乎“数量”和“生育率”的同时,却忽视了“死亡率”“流动性”等同样重要的人口统计维度。
作为一般性常识,人口增长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共同决定的。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从狩猎采集、传统农业到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依次走过低—高、高—高、高—低三个阶段。在高出生率的农业时代,人口只是缓慢地增加。只是到了第三阶段,随着死亡率有了明显下降,个人预期寿命不断增加,人口基数加大,才促成了人口的指数增长。唐沃思显然把死亡率遗忘了,把构成人口绝大部分的主体遗忘了,只把新生的宝宝视为了洪水猛兽。
相较之下,马尔萨斯首先考虑的反而是死亡率。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他主张通过提高死亡率来抑制人口。正如达尔文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大自然母亲也总是一边鼓励生育,一边以“死亡”的方式,通过提高代际之间的新陈代谢率,解决种群压力问题。相比之下,人类演化的独特性不在生育率的提高,而是死亡率的降低,由此导致人口的新陈代谢率放慢,结果是人类社会日渐呈现老龄化趋势。于是,占据越来越多生存空间和资源的,不是唐沃思讨厌的宝宝,而正是与这位作者一样的长者。
然而,“死亡驱动”毕竟是一种残酷的方式。因而在第二版中,马尔萨斯主张以更人道的方式,通过降低出生率抑制人口规模。唐沃思也同样感叹,文明不可丢弃,不如“少生些孩子”。当他将希望寄托于现代女性觉醒,开启低生育率时代,从而摆脱人类困境时,从中体现的恰恰是《人口原理》的主张:贫困由生育太多所致,也可以由控制生育来克服—这是一种典型的富人看待穷人的眼光。由此,唐沃思的论证逻辑与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并无二致,他本人也就从原先自称的独立于阶级身份的“局外人”,变成了人类历史的“局内人”了。
唐沃思并非不想摆脱马尔萨斯的主张。在行星史书写的伊始,节育不是唯一摆脱资源困境的方式,人类还可以通过迁徙,流动到别的地方去。正是看到了这种人口的自然流动性,他在书中勾勒出了一幅现代智人在人口压力下离开非洲、向全球迁徙扩散的史诗画面。不过,如行星史后来所未挑明的,自农业出现之后,人类逐渐被固定在土地之上,人类流动性也不断降低。当农夫的生存空间无法继续扩张之后,人类便让渡了自身的自由,用国家的“蛋壳”把自己罩了起来,其流动性随之进一步丧失。
“大转折”出现在美洲的发现。唐沃思认为这一“第二星球”无比重要,只是着眼于其作为“新”空间,如何缓解了欧洲的人口压力。他彻底忽略的是,空间的拓展以人口流动性为前提,流动性又以文化实力为前提。欧洲人凭借航海技术,流动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从而造就了繁荣。相比之下,更多区域的人群,流动性和生存空间反遭进一步挤压。还有一小部分人,尽管流动性提高了,处境却更加悲催,那就是行星史中并未提到的非洲人,他们被迫卷入到三角贸易中。由此可见,人口压力与生存困境的产生与纾解,都与流动性息息相关!由文化实力带来的人口流动性的分岔,也将人类引向不同命运。
当唐沃思批评达尔文轻信了马尔萨斯,轻信人口与环境之间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他本人也和他所批评的一样,将矛头指向“繁殖的内在本能,而非特殊的社会环境”了。人口增长只是拉低了人均生存资源,但人口流动性降低和分岔却带来结构性生存困境。将人类困境简单粗暴地归为生得太多,实乃为某些文化因素开脱罪责。当然,唐沃思对文化批判的悬置,也有其良苦用心。在他看来,人类内部的历史,无论多么惊心动魄,都只代表一种物种的历史。而在这颗行星上,还有无数物种与非物种的历史有待书写。
深深隐藏的“伽利略”:悬置的蓝色行星
同方兴未艾的大历史一样,唐沃思的行星史,也试图串联起宇宙史、地球史、生命史和人类史,为万物作传立书。他为之感慨,如今还有谁不是历史学家呢?在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于大历史研究一路高歌猛进时,历史学家却在后现代思潮的引领下,日渐丧失了对宏大叙事的兴趣,钻进了社会史、文化史等微观历史研究中,不自觉地成了人类中心主义者。唐沃思呼吁历史学家重新找回对大历史的发言权,并超越以人类为中心的窄叙事—历史并不一定是人的历史,还可以是行星万物的历史。
正如《欲望行星》中文版封面所展现的,行星史就是对地球这颗蓝色星球的凝望。仔细打量,其中还深藏着第三张面孔—伽利略。生活在十七世纪的伽利略,发明了能放大三十二倍的天体望远镜,并确认了金星相位、木星卫星、太阳黑子、月坑和土星环,堪称行星史研究的鼻祖!他通过行星研究,有力地证实了太阳不是围绕人来转的,这无疑是冲击人类中心主义的壮举。他还从地面看向宇宙,为现代人开启了一种观看行星的方式。一九七二年,阿波罗十七号拍下了从外太空看地球的照片,又在现代人脑海中植入了“蓝色行星”的模样。自此,我们学会了像伽利略观察其他行星一样,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姿态,观察我们置身其中的地球。
不过,采用这种伽利略式的,我们称之为“科学”的观看之道,恰恰隐匿了或许是行星史书写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人文关怀的丧失。唐沃思将抽象的人类整体降到动物的位置,但作为观察者,又为自己保留了“人”的身份。他所看到的人,与威尔逊所观察的蚂蚁,并无二致,人会种地,蚂蚁也会。说实话,这种观看之道令人不安,甚或带来某种虚无—人类创造的文化不值一提,这就把人存在的意义消解掉了。当具象的人和万物生灵一道,都被看成抽象的“物种”,生命自身的体验,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此种种,自然都被抹去了,蓝色星球反而呈现出伽利略望远镜中那种无生命的冷漠。
这种视角的可疑之处,还在于抹去了自然演化本身所形成的差异。比如,唐沃思将“性”视为男女平等的合谋,认为“女人与男人同样为内在欲望所驱动,希望拥有更多孩子”。然而,主体的经验差异却带来另一番故事。《海蒂性学报告》表明,对女性来说,无论是为了欢愉还是为了生育,性都意味着更多的痛苦。女性往往很少获得来自男性方面的性高潮,性生活也让女性容易感染各种妇科疾病,带来身体上的长期折磨。一旦怀孕,更是面临十月怀胎的挑战、难产的风险以及养育孩子的艰辛,这些几乎都是加诸女性身上而男性不必承担的。因此,没理由认为人人都有相同的内在自然,女性生育也绝非只凭内在自然的召唤。
抹平差异、忽视体验的行星视角,使唐沃思失去了曾经的批判锋芒。通过将生态问题简化为人口问题,将性驱力视为导致人口问题的始作俑者,他把批判的靶子指向了内在自然。由于内在自然是人类共有的,因此,没有人是圣人,也没有人是罪人,责任是每个人的,这就抹平了人类内部的不平等。又由于内在自然是演化所赋予的,演化又是超越善恶的,如此我们既无法指责其他物种繁衍生息的本能,也很难指责自己。结果,看似批判了所有人,那些关键性的少数便被有意无意地豁免了;通过归因无法被批判的演化法则,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批判。
尽管蓝色行星的模型存在于每个人的观念中,熟悉到我们在每一次微信的启动画面中都能看到,但它依然是陌生的,脱离了人的日常感受。保持对蓝色星球的“离地”观察,无疑提供了一种大局观,指出了人与地球在自然演化上“冷酷无情”的事实关系,但也容易滑向虚无主义,逃避伦理价值问题。为此,我们需要留住人文性,留住人在星球上的生命体验。如布鲁诺·拉图尔在《着陆何处》中所呼吁的,以一种“在地”“切身”的视角,离开虚空、回归大地,反而能更真实地体验到“行星”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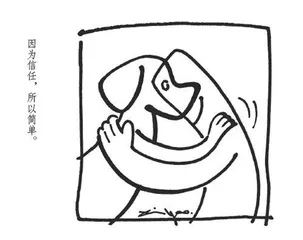
地球的独特之处在于生命,生命的“欲望”在于生存和繁衍。通过对欲望行星的刻画,唐沃思展现了人类生命的内在本性,从而不仅扩展了环境史研究的时空深度,还将人与地球关系的讨论,下探到对生命、物质和自然的底层思考中。这样的思考背后,始终或明或暗地浮现着达尔文、马尔萨斯、伽利略等人的面孔。然而,无论是达尔文式的物种演化视角、马尔萨斯式的人口资源视角,还是伽利略式的蓝色行星视角,都涉嫌将人类历史过度自然化,将人还原为“只是为了活着”的动物,这何尝不是一种“偷懒”呢?人不仅追求“活着”,还追求“活着的意义”。就如看不见的臭氧层成就了地球的生命,看不见的意义成就了人的生命。或许正是忽视了“意义”在人类演化中扮演的角色,到头来,这部行星史也似乎缺了那么点意义。
(《欲望行星:人类时代的地球》, 唐纳德·沃斯特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二0二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