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孤独
作者: 陈仪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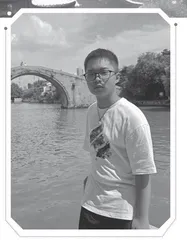
作者自画
文学,一个浪漫的名词,在我的心中构成了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里,天有仙狂醉,白云来揉碎;水有龙潜月,波涛成彩笺。我从小便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内向敏感的我,用无声之文字,承载生活中的细微之思。一草一木,仿佛在随风舞动灵魂;一水一石,仿佛在透露时光含情。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作家,在文学的殿堂中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
公元805年到815年,在永州的湖面上,总有一叶小舟,随风悠然飘荡,从湖滨到湖心,四时如一。十年之间,这里的湖水波澜不惊,鸟兽无处寻觅,天地之间,只有滞缓的棹声,只有船上佝偻的渔翁,只有那个自命不凡的柳愚溪。
读懂柳宗元的《江雪》并不难。诗歌的情感分外强烈,孤独自字里行间喷薄而出。天是孤独的,鸟是孤独的,在千万孤独中,浮出一叶小船,满载痛楚,满载迷离。当孤独的天地之间,徒剩一个孤独者,江湖再苍茫,似乎也一眼可看见边界。
初唐的陈子昂也有这种孤独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然而,陈子昂早已将自己投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寰宇之中,与其说孤独,不如说,那是一颗独有的热心在自愿淬炼。柳宗元终究与其不同,湖之上,雾霭沉沉,似不可逾越,使得他无法跳脱,无法跳脱命运束缚。
柳宗元祖上世代为官,母亲饱读诗书,从小与母亲一起生活的他,与母亲谈文论道,吟诵《离骚》。他将成为屈原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梦想,发愤图强。
二十岁考中进士的他,认识了一生的挚友刘禹锡,后被任命为校书郎。儿时的他早已认识藩镇割据的战火纷飞,权力的纷争使百姓如蝼蚁般深受迫害。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经历了几年官场生活后,更是直视大国萎靡的阴暗面,心中满是悲愤和急切。灵均(屈原的字)的诗语引领他寻找一种救世的责任。他眉头微蹙,灵感在心中翻涌,似乎生出一种决心,抑或是一种预感,他要像屈原一样,做成一番大事业。
柳宗元和刘禹锡加入了王叔文的队伍,他们打击贪官、宦官,取消进贡,罢宫室五坊使……百姓不再被搜刮掠夺,民心略安定下来。这时候的柳宗元,宛若一个英雄。
俱文珍等人的政变,使这位青年英雄落入命运的低谷。王叔文死,二王八司马的团队也彻底解散了,柳宗元被贬到偏远的永州不久后,那个为他启智、给他鼓励的母亲,去世了。在永州,他的理想、他的亲人全都离他而去。一夜之间,他似乎成了一个垂暮的老人。青春和志向似乎不复存在,大抵,世间再无意气风发的柳子厚,徒剩潇潇暮雨里垂钓的柳愚溪。
愚溪愚溪,何其澄澈;乱我心兮,何其愚钝;水影游兮,掬水而行;涤我心兮,何其明丽。
永州的十年里,柳宗元游山玩水,写下《永州八记》。他总爱独自垂钓,然而,鱼线也总是毫无动静。柳宗元斗笠下一双迷茫的眼,瞥见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似乎他自己才是寒水里的鱼,被命运的钓竿捉弄着。他常想:水中的游荡又是否有意义呢?但他不愿离去,他属于暗流的正义,千万孤独里,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使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在永州,柳宗元遇见了一位捕蛇者。这位苍老的捕手,宁愿面对被毒蛇侵袭的危险,也不愿意被沉重的赋税所摧残。于是柳宗元写下了著名的《捕蛇者说》。
奸臣当道之日,腐朽与虚伪笼罩着大唐,安史之乱的阴霾几十年未消散。战争频繁,赋税沉重,百姓连苟活都成了奢望。现实是荒诞的,失败是在所难免的,但若因为失败便放弃与现实的对抗,那么屈子“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绝又从何提起?若因为孤独与困顿便与荒诞妥协,那救世的英雄是否成了虚假的笑柄?像朝廷内趋利避害不顾人民的官员那样为政,柳宗元做不到;如五柳先生那样拂袖隐居,柳宗元也不想做。他从小便铸下英雄的灵魂,他的热情从未泯灭,在最孤独的时候,他没有哭;他的泪水滚烫,一旦流露,便是浴火涅槃的岩浆。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柳宗元竭尽全力治理柳州,使柳州百姓安居乐业。819年,柳宗元终于收到回京的圣旨,然而他的身体已无法支撑,同年,柳宗元在柳州去世。
柳宗元的一生,同其好友相比,实在不算明艳。韩愈官至宰相,倡导古文运动,又教书育人,功绩显赫;刘禹锡逍遥自在,不曾被苦闷扰乱心胸,乐观开朗。柳宗元则在政治上没有巨大的建树,只有一次失败的政变,我们对他的印象,总是一个孤独的背影,扑朔迷离。然而,他的心路却令人动容,他的人生似乎一直郁郁不得志,但他的灵魂却从未被命运打倒。他或许无数次在水中寻找自己的故乡,回忆少年的得意,终于明白盛年不再来。他承认命运的荒诞,他以沉默与荒诞做孤独的抵抗。他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萎靡不振,一次又一次向山巅挪移。哪怕行动微不足道,但直到生命尾声,他仍在践行着自己一生的理想。
长安,柳宗元思念长安;从长安走向孤独,蜕变如此痛苦,但若褪去懦弱与荒谬,长安的孤独便不再悲哀,那是数千条涓涓细流,单枪匹马穿行,终将汇成汪洋湖泊。
创作感言
灵魂安静后,岁月还会流过许多年代。柳宗元的孤独隐匿在尘埃之中,芸芸众生的孤独则在时代的角落里繁衍生息。我动情于柳宗元空对岁月而对往昔风华求之不得的无奈。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有一句话: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只有直面孤寂,与其达成一个体面的协议,才能超脱平庸与悲哀。柳宗元不同于唐代其他诗人,他独自行走,就像是西西弗斯,用一身荒凉实现了自己烂漫的理想。我很庆幸能用手中的笔诠释这伟大的孤独。
同学评价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和陈同学相识快八年了,在我记忆里,他一直是一位文学少年。为人也好,处世也好,总是淡定从容,不慌不忙。以陈同学的阅读量,几乎没有同龄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因为丰富的阅读量,精神世界也随之丰满。“与其花十年时间培养一位摄影师,不如把相机直接交给一位诗人。”即使有些心中无法诉说的想法,他也有千千万万种方式去表达:可以是一张藏满故事的相片,亦可以是寥寥几笔勾勒出的画卷。用他自己的话说,“其实我写作本身是因为内向,然后呢比较孤单,有好多想说的,有好多想要留住的,只能付诸笔端了”。读他所作的诗歌与文章时,我常会感受到一丝沉郁萦绕。不同于那些热血、励志,更多的是平静甚至破碎……我个人也很喜欢陈同学的文风,用最浪漫的口吻去描述最缥缈的现实。在结尾,我想说,他无须被修饰,放心大胆地——做自己就好。哪怕仅是那个最朴实无华的他,也被大家喜爱着。
——魏沁妤
柳宗元向往的不仅是长安城,还是大唐长治久安的梦。于是,他长久安顿在孤独中,和自己对话,和孤独对话,和长安对话。
在陈仪颉的笔下,柳宗元的一生不再是生疏的文字,而是一部人生史。其实不光是柳宗元,中外的历史、文学名人,陈仪颉几乎都“打过交道”,这归功于他日常的文学积累和他的文学天赋。陈仪颉同学是个内向的人,但他用笔将自己内心的波涛汹涌写在字里,将一件件令人回味的往事道在行间。面对作家,有人附庸风雅,他和作家的交流则是发自内心对文学的向往和追求,是两个灵魂的碰撞,是后浪和前浪的交汇。他的微信公众号“儒新文学新生代”中的一句话“给文学一点耐心,圆你一个文学梦”是脚踏实地的执着与渴望,是对文学梦想的追求与热爱,是他写给自己的预言。“儒新”,“儒”者,读书人也;“新”者,初始者也。他名副其实,文采斐然,是我的偶像。我祝他在未来的文坛上留下自己的足迹,早日实现文学梦!
——吴悦慧
▲陈仪颉
访谈录▼
新作文:你对写作的看法是什么?
陈仪颉:我从小性格内向,而心里总是很敏感,许多想说的话都如鲠在喉,只能付诸笔端。我认为写作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在人世与幻想之间破土生长,成为暂时逃避现实、重塑现实的圣地,王尔德所言极是:“我们都是阴沟里的虫子,但总要有人仰望星空。”一切都触手可及,或坚硬,或虚无,或只有一层朦胧的雾。我蜷缩在自己狭小的书房时,从未经历千人千面的悲喜,却能在笔端享受生命情感带来的出生、撕裂、湮灭和超脱。写作从不是把灵魂束之高阁,大谈风花雪月;在自我书写的温柔与光明中,采撷一点色彩,为苍白的生活添一点烂漫,这便是目前写作对我的意义了。
新作文:为什么选择写柳宗元?为什么用“长安孤独”这四个字做题目?
陈仪颉:本篇文章是我观看《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后完成的感悟。选择柳宗元是因为我能共情到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空对古今山海的孤寂。之所以叫作“长安孤独”,是因为柳宗元的故乡在长安,柳宗元意气风发时的理想埋葬在了长安,但后来那里成了柳宗元一生遥望而回不去的地方,浸透着他的孤独与哀愁。而柳州则是柳宗元脚踏实地、施展抱负的寄身之处。从长安到柳州,记载了柳宗元于寂寞不甘中超脱的人生沉浮。
新作文:是否喜欢历史?在创作中你参考了哪些资料?对于历史人物的写作,你有何心得?
陈仪颉:的确很喜欢历史。写作期间主要是写体悟,也查阅了一些柳宗元的生平介绍。这类历史题材的写作,我认为应该先学会与那些遥远的人的时代共鸣,而不要与历史产生距离感,古今的孤独与迷茫、悲愤与痛楚等情感都是相通的。只有用柔软的心去揣度那些纵横交错的故事,才能看清浩荡丹青里藏匿的人性光辉。
新作文:对同样喜欢写作的同龄人,有哪些想说的话?
陈仪颉:多读书,多积累。读书是提升文学素养的最好方式。从多到精,不求博览,但每一次阅读都应该有思考有深度,摈弃一些表面的浮华。对写作怀有纯粹的热爱,关键是要沉下心来,相信文字的价值。引用木心先生的一句话:“文学是好玩的。你爱文学,文学也会来爱你。”
新作文:想对《新作文》说的话。
陈仪颉:感谢《新作文》给了我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让我在探索文学的道路中获得价值感和成就感。希望《新作文》能给予热爱写作的同学更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