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和鹞子与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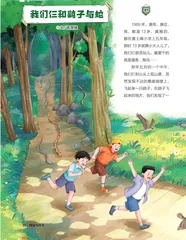

01
1969年,唐亮、唐庄、我,都是13岁,属猴的,都在黄土嘴小学上五年级。那时13岁就算小大人儿了。我们仨很贪玩儿,最爱干的就是摸鱼、掏鸟……
那年五月的一个中午,我们仨到山头上观山景,忽然发现不远的悬崖峭壁上,飞起来一只鹞子。在鹞子飞起来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枚红颜色、麻嘟嘟的蛋——那无疑是一枚鹞子蛋。鹞子是懒惰吗?借助山崖上那个比一本书大点的石窝窝,就把蛋下在那里面了,而且连一根柴草也没铺。我们望着那孤零零的鹞子蛋,一阵欢喜。
忽然间,我们又发现了一条蛇,从山崖的一侧正向那鹞子蛋急匆匆地爬过去。我们仨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让蛇吞掉鹞子蛋!我们想起了山民吓唬老雕、老鹰的方式:如果老雕、老鹰叼着野兔或野鸡飞向空中,就冲着天空叫喊:“掉喽,掉喽!”那猛禽就会把口中的猎物松开。于是,我们仨便也叫喊着:“掉喽,掉喽!”我们的声音传递到山崖上,山崖发出了回音,可那条蛇还是逐渐拉近了与鹞子蛋的距离。这时候,唐亮说:“瘸子打猎——坐着喊,不管用,得动真格的。”于是我们仨不约而同地捡起核桃大小的石块,向那山崖投掷过去。但我们也算是手下留情,不愿意伤害那蛇,只是采取“敲山震虎”的方式,将石头抛到悬崖峭壁上。石头与山崖相撞,碰出了火花,还真把那条蛇吓唬住了。它没被我们的石头击中,却在惊吓中滚落悬崖,掉入了草丛。鹞子蛋没被它吞入口中,我们仨忍不住拍手叫好。
之后,我们差不多天天中午都到那个小山头上看鹞子蛋。
一个星期以后,那石窝窝里不知怎的冒出三个鹞子蛋来。再后来,我们就不知道那鹞子窝里到底有几个鹞子蛋了。因为那只大鹞子已经开始抱窝孵小鹞子了,它一刻也不离开那个石窝窝。我们仨望着它,它也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它也许知道我们是够不着它的,所以有一种安全感。它大概不知道,我们曾经把一条欲吞掉鹞子蛋的蛇吓落了山崖。
又过了不知道多少天以后,我们发现石窝窝里多了三只白花花、毛茸茸的小鹞子。我们眼瞧着两只大鹞子不断地叼着蚂蚱、小鱼之类的食物,去喂它们的孩子。那萌萌的小鹞子张着大大的嘴巴,似乎有多少食物也不能满足它们的食欲。
我们仨望着那大鸟喂小鸟的情景,看得没个够,下午的课都迟到了好几回。三只小鹞子渐渐地褪去了白色的奶毛,长出了花里胡哨的羽毛。小鹞子更可爱,也更能吃了。大鹞子反反复复叼着食,去山崖上喂它们的雏儿。那时候,我们仨的坏主意就已经打定:把小鹞子据为己有。我们够不着那鹞子,也没有攀悬崖绝壁的本事。最后是我出的馊主意,我们弄来一根差不多五米长的枣木杆子,硬是将石窝窝里的鹞子捅了出来,坠到了山崖下的草丛里。小鹞子一只也没有摔坏,我们把它们捡起来,每人分了一只。那两只大鹞子围着我们飞来飞去,喳喳地叫着,肯定是想从我们手里夺回它们的孩子。
小鹞子被我们养得羽翼丰满,尾巴展开来像扇子。我们玩鹞子、驯鹞子,每天乐此不疲。起初,我们把鹞子放在桌斗里,老师不管。后来,那不老实的鹞子满教室乱飞,老师就不让我们把鹞子带进教室里了。
02
那年七月间,我们村南山梯田里种的玉米和土豆不断被野猪糟蹋,不是啃了就是拱了,队长发动村民打野猪,还有奖励。于是我们仨结伴去南山,想夹野猪。山里人把夹猎物的铁夹子统称为狐夹。我们仨各自挎着一盘狐夹,带着自己的鹞子,说说笑笑地向南山的高处走去。
我们走在山道上,忽然发现一条蛇,横着盘踞在被野花、野草挤窄的山路上,纹丝不动。好大的蛇!有镐把粗细,不见首尾。我们被它吓了一跳,不禁“哎呀”一声,停住了脚步。
开始,我们不想惹那条蛇,只是想让它给我们让一条路,于是采取了打草惊蛇的办法。我撅了一根六道木棍子,敲打着那些葱茏的花草,可这蛇根本不在乎,还是赖在那里。我随口说了几句顺口溜:“好狗不拦道,蛇也别挡道;拦道就打你,赶快给腾道。”唐庄说:“你光在那儿瞎说,这能管用吗?”果然,那蛇还是不走,这下可把我们给激怒了。唐亮说:“咱们仨都把鹞子放出去,让鹞子捉拿那拦路的长虫。”
我们放出了各自的鹞子,鹞子却没有奔蛇去,而是奔树上的鸟去了。三只鹞子,一个目标,都去追那只白桦树上的小黄鹂。
蛇还横在路上,没有让道的意思。
我们仨就弯腰捡石头,向那蛇的周围投掷过去。石头一块块落在蛇的身旁,蛇竟岿然不动。
我们又捡起石头,恨不得直接向那蛇投掷过去。然而,那石块都快把蛇埋住了,蛇还是不让道。但我们知道,那蛇不是死蛇,因为它的身子偶尔会动弹一下——见它如此死皮赖脸地占着道不走,我们又将大大小小的石头投掷过去。这个时候,那蛇似乎才醒过来,它扭动着身子,抬起了头,非常恼怒地冲我们猛扑过来……
更吓人的是,从距离它不远的一块大石头下,忽然之间钻出了若干条蛇,急速地向我们爬过来、冲过来。
蛇是找我们报仇的吗?据说蛇有复仇心,得罪不起。我们是得罪了蛇头吗?还是得罪了蛇王?听说蛇头被得罪了,便会聚来群蛇,进攻得罪它的人们。我们分明是要遭到蛇的攻击了。望着那些“涌”来的蛇,我们吓呆了,头发都立起来了。我们知道什么叫三十六计走为上,什么叫惹不起,躲得起。于是甩掉肩上的狐夹,惊叫着向山下跑去……
由于是下坡路,我们仨几乎是连滚带跑地向山下逃窜。这个时候,被我们仨遗忘的三只鹞子纷纷追了上来,落到了我们的肩膀头上。它们没叼着黄鹂,也不像是刚吃过黄鹂。
我们埋怨那鹞子:白养活你们了,怎么就不帮我们擒拿群蛇?
谢天谢地!那蛇并没有追上我们,也没有咬到我们。
03
落荒而逃的我们仨,不敢再到南山去。在那草木葱茏的季节,蛇在山里频繁出没,我们谁也不敢去拿那扔下的狐夹。
回家后,我们和大人们说起在山上碰到群蛇的情景。牛倌说,那是我们惊扰了“蛇开会”。蛇也是会聚会的。那天,蛇一定是在开秘密大会。那条拦路蛇,是在坚守岗位,为开会的蛇“站岗放哨”。
听了这话,我们不禁哈哈大笑。那牛倌的解释,让我们半信半疑,又觉得很好玩儿。
转眼山黄叶落,花花草草枯萎了。只有枫树的叶子、橡树的叶子,没有全落下来,依旧红艳艳地挂在枝头,像一面面飘扬的小红旗。那些野玫瑰的树棵子上,挂着比小辣椒还好看的果实,吃起来是甜的。那天,我们仨终于鼓起勇气上了南山,不是奔着叶子和果子去的,而是去南山上找我们丢下的狐夹。
我们还是带着各自的鹞子。那鹞子更成熟、更机警,也长本事了。它们可以抓到兔子、野鸡了,但没见它们抓到过蛇。
没走多远,我们就见到眼前有一堆乱石,还发现了一条蛇蜕,只是不知蛇在何处。蛇到哪个山洞、石洞、树洞里冬眠去了吗?
此时此刻,我们还心有余悸。我们仨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一眼就看到了当初我们甩掉的三盘狐夹,它们被落叶覆盖着,狐夹的链子也变得锈迹斑斑。
这个时候,我们的三只鹞子各自叼着一只刚捕获的松鼠,接二连三地向我们飞来。
我们仨背着毛主席的诗词:“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美丽的南山,真好。
我们的年少时光,真好啊。
可年少时光再也回不来了。写这篇散文的时候,我已经成了老年人。那鹞子、蛇,都到哪里去了?好在,我们仨现在都在一个微信群里,可以联络彼此。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dfyz20250604.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