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幕:现代版批注, 喧哗式狂欢
作者: 钟伟建初遇弹幕实属偶然,在追看《甄嬛传》时,我误触屏幕的一角,瞬间,字符便铺天盖地涌入眼帘。我恍然大悟,为何人们将此类字符流称为“弹幕”—那些争先恐后弹出的字符,如密集发射的炮弹,像凭空织出一张幕布铺满了显示屏。
依我看,就功用而言,弹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注解型弹幕,它们针对视频内容进行解读与补充。例如,有弹幕指出“皇后和华妃的耳环都是东珠”,原来东珠极为名贵,一般只有皇后才戴,华妃的嚣张跋扈可见一斑。如果没有弹幕提示,绝大多数观众都会忽略这一细节。二是感想型弹幕,它们针对视频內容表达个人的嬉笑怒骂,畅所欲言。比如,当甄嬛初受宠,收到了皇帝丰厚的赏赐,碎玉轩主仆欢天喜地时,弹幕里出现了一条:“像极了我收快递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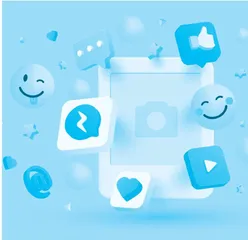
捧腹于网友的才华之余,我总感觉弹幕似曾相识。细而思之,我发觉弹幕其实古已有之,若剥离科技这一元素,彼时的弹幕名曰“批注”。
大体而言,如今的注解型弹幕便类似于古时读书人的“注”,起着促进理解作品的作用。以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为例,从汉代的鲁、齐、韩、毛四家诗及郑玄的笺注,到唐代陆德明所释音义,再至现代高亨、程俊英、孔祥军等诸位先生的点校本,在历朝士人“弹幕”的层累下,今之学人所见《诗经》已然不是春秋时期的白文本,而是广罗诸家注解后的丰富版本。此时的“注”已融入作品本身,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古时之“注”观照今之“弹幕”,又何尝不是如此?纷至沓来的弹幕与影像共同打造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剧场,文字与形象、文字与剧情、文字与文字间的多重交互产生了种种错綜又新奇的意义。弹幕这种即时性评论往往被现场情景吸收,并不知不觉地补充了现场。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于1992年在其著作《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中提出了“参与式文化”的概念。他认为,以全体网民为主体的Web2.0网络平台,通过网民积极主动地创作媒介文本,可以创造出一种公开、包容、共享的新型媒介文化一—参与式文化。弹幕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它让观众不仅仅充当被动的“接受者”,还成了可以参与和评论的“创作者”。弹幕的出现改变了观众的介人结构,在原本的“观看”和“欣赏"活动中加入了“参与”和“创作"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內涵。
而感想型弹幕则近似于古时的批”,多用于表达观者的个人感受,以金圣叹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为例,他所发的“弹幕”中就有大量自我情感书写式的倾吐。如看到畅快处,便不遗余力猛夸:“写得妙极”“写得好”“妙妙”“绝妙”这与如今常见的“666"(口语“溜溜溜”的谐音)、“tql”(汉语词语“太强了”的拼音首字母缩写)、“yyds"(汉语词语“永远的神”拼音首字母缩写)等弹幕如出一辙。感想型弹幕基于内容与自己产生共鸣,故而只求一吐为快,最好能玩个“梗”,让更多的人在会心一笑中产生共鸣
感想型弹幕与古时之“批”一样,具有强烈的自我性与抒情性。批语即便仅一二词或两三语,但自然随性,又不乏风趣幽默。在现实生活中,直接的人际交往常常带有不稳定因素,人们要想获得情感满足,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借助互联网的遮蔽功能,可以倾诉和宣泄自己的情绪,可以抒真情、说真话,而无须付出代价,无须为此背负情感债务。这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爱自我表达与自我表现的需求,也是弹幕备受大众追捧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弹幕还具有真实性和人性价值。
传统意义上的文艺批评家往往有一个令人仰视的头衔,他们博学、深刻、犀利。精英主义往往以系统的知识为资本,以传统审定的经典为圭桌,满口“子曰诗云”,高高在上。然而,精英主义囿于学院高墙,网络则开拓出了一个开放的广阔空间。弹幕打破了以往的话语垄断,人人都有权坦陈自己的意见或情感,无须引经据典、妙语连珠,也不必羞涩地附加“不揣浅陋”“抛砖引玉”之类的自谦之辞。大众所渴望的痛快无关经典和权威,只求“我的表达我做主”,还因“我的在场优于我的所讲”。弹幕轻而易举地满足了大众的这一共同愿望:一种大声表达的愿望,一种渴求被听见、被看见、证明我来过的愿望。
于是乎,弹幕便可被视作一场生气勃勃的、众声喧哗的狂欢。这与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所说的“狂欢节”如出一辙人们打破层级壁垒和礼仪约束,尽情欢乐,平等交往,过着充满欢笑的“第二种生活”。人们观看弹幕、使用弹幕的过程就像自己参加了盛大的嘉年华或狂欢节;人们将自我情感诉求和价值立场诉诸弹幕,同样带有很强的娱乐精神和狂欢色彩。“弹幕族”在满屏字符的视觉景观中,体验着集体在场的欢腾,获得了众声喧哗式的情感满足。
狂欢固然可喜,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全民沉浸于弹幕的喧哗中时,“深度”已然被偷换为“速度”,“质量"业已被“数量"堂而皇之地取代。“弹幕”一词本身便形象地表明了表达碎片化的状态:电光石火间发出的只言片语,随机抖的一两句机灵,还有相当一部分表态式的感叹…碎片琐屑注定与全局之气度绝缘。尽管弹幕被归入“评论"范畴,但弹幕文化仍与传统的文艺批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尽管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擅长的评点式文学批评与弹幕存在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但文本的细读、品鉴、沉潜、揣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操作程序。全民狂欢的代价就是弹幕悲哀地被贴上了“重复”“低俗”“无厘头"等标签。带有明显即兴意味的弹幕符号,很难有真知灼见与严肃的反思。众声喧哗的表象下,也缺乏思想激荡的潜流。说到底,弹幕虽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消遣娱乐形式和特别的情感表达路径,但就其本质而言,迄今为止,弹幕文化仍是一种拒绝深度思考的“浅文化”“俗文化”,甚至是“伪文化”。当大量低质的字符飞过屏幕时,已然对观者主体纯粹的视频欣赏行为造成干扰,弹幕文化的加入有时反而剥夺了视频这个主文本的文化价值,这无疑让人“观”不偿失。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狂飙突进,弹幕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与人们相伴而行。面对日益勃兴的弹幕文化,思考如何使之有序运作并产生新质文化生产力方为应有之义。技术工具的价值取决于使用者,当每一位网络参与者都能怀有理性和智性去运作、去发声时,弹幕文化才能真正成为网络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钟伟建,浙江省温州中学语文教师,教育硕士,中学高级教师。曾主持省级课题,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致力于高中语文读写交互教学实践研究,指导众多学生习作荣获奖项或被知名报刊发表。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zwtg20250406.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