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语言可触摸
作者: 江弱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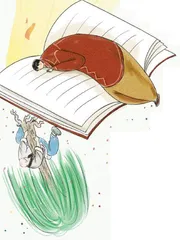
我们读莎士比亚晚期的悲剧作品,读出了土布的坚韧、粗毡的质朴。读他早期的传奇剧呢?绢一般柔滑,绸一般细致。我们读杜诗,共同的印象是“沉郁顿挫”。“沉”如果是一种深度,“郁”就是一种厚度,而“顿挫”不光是节奏起伏变化,还意味着有很多的关节部位,就像老树的枝干。如顾随说的:“老杜是壮美,笔下要涩,摸着如有筋。”“涩”就是不平滑,有阻力。“摸着如有筋”是什么样的感觉?你看看鲁迅写的《秋夜》的开头就明白了:“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后园墙外有两株枣树,这样一个平滑的句子硬生生被打了两个结,就显得特别拗,但力度就体现出来了,质感和纹理也体现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水浒传》里的一段文字。第七回写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树前,把直裰脱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缴着,却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将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
张大春在《小说稗类》里说,这四个“把”字,一个“用”字,一个“将”字,是为了“补强动感”。他假设语文老师会觉得累赘而给改一下:“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树前,脱了直裰,右手向下,倒缴着身,左手拔住上截,一趁腰,便将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他认为,如此一来,简洁是简洁了,“智深”这个主语的负担却太重,拖不动后面的一大串动作,弄成尾大不掉。
可是我不这样认为。施耐庵意不在此,他要写的其实是鲁智深的“粗人偏细”。
别以为花和尚一味鲁莽,他在江湖上行走,非常机警,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拳打镇关西那一回,他把郑屠脸上打成油酱铺、彩帛铺、全堂水陆的道场,打得脸变了色,没了入的气。鲁智深知不妙,一边嚷嚷“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边大步走掉。
金圣叹批曰:“鲁达亦有权诈之日,写来偏妙。”
这倒拔垂杨柳一节,写的便是鲁智深不敢掉以轻心。“相了一相”是打量了一下,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心里先有了个基本盘的考量。后面每一个“把”字,都在试探点踩得准不准,劲儿吃得着吃不着。每个环节他都在掂量,在寻找着力点,测试可行性,也暗示了垂杨柳并不好拔,万一拔不出,会被众泼皮嗤笑。这段文字虽然一气呵成,却故意放慢了镜头,分解了动作,好比足球比赛中射门一瞬的慢镜头回放,令人感到势大力沉,才看得真切过瘾。不慢放,显不出劲道。这就叫“笔下要涩,摸着如有筋”。
(林冬冬摘自商务印书馆《诗的八堂课》一书,阿砂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