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时代,学习语言值得吗
作者: 李若衡Cindy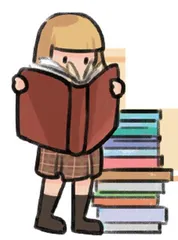
我是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专业的大四学生。学校要求每个文科生学习一门小语种。通常,国际生可免除该要求,我却选修了西班牙语。为此,我受到了不少质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学西班牙语,而不是去学更“实用”的学科呢?但事实上,西班牙语——这个看似“无用”的小语种,却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大用”。
打开小语种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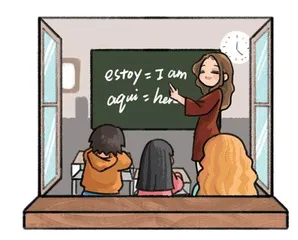
我从高中开始学习稀有小语种北拉科塔语,大学期间又学习了西班牙语、满语、纳瓦霍语(美国最大的原住民群体所使用的语言),以及克丘亚语(南美洲重要的原住民语言)。
我最开始对原住民语言感兴趣,是因为这些语言在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中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对自然灵性的尊重与敬爱。2018年,我在深圳读书时偶然听说美国有一个叫立石部落的原住民群体。出于对陌生文化的好奇,16岁的我和妈妈两个人背上背包来到这个部落住了一个月。我从部落带回了半箱书,还被“种草”了一个北拉科塔语学习的在线平台,在掌握北拉科塔语的基础后,我开始动手把一本印第安人的人类植物学著作《编结茅香》翻译成中文。
上了大学后,我也一直在学习小语种。西班牙语老师告诉我们,签到时说的“到”,翻译成英文是“I am here”,西班牙语则是“estoy aquí”。其中“estoy=I am,aquí=here”。西班牙语的语法设置非常有趣,很多时候可以省略主语,从谓语的语法变形中,就可以看出主语是什么。
虽然是西班牙语课上唯一的亚裔学生,但我从未感到孤独。大学期间,与我要好的朋友都是上西班牙语课时的同桌。我们合作过几个研究项目,从秘鲁的纺织品,到哥伦比亚的棕榈油工业链,再到拉丁舞如何构建社区的概念。我们也一起熬过了很多个备考的夜晚、参加了很多场拉美酒会、经历了很多被点名却回答不上来的尴尬时刻,当然也有取得成果后的喜悦。这是大学里很快乐、很纯粹的学习时光。
在语言里发现附近

很多人质疑我,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在大学专门选修一门小语种是在浪费时间和资源。不少我认识的语言高手也认为,小语种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来掌握。但我认为,学习语言不仅要记忆文法和词汇,还要走进社区与人打交道。
在我们学校的社交晚会上,我通过英西双语混用的方式,认识了很多拉美留学生。还有一次在纽约坐火车,一位墨西哥女士因为不会说英语,显得很焦急,担心错过自己的火车。尽管我的口语表达不清晰,但我听得懂她的问题,于是我耐心地向她比画着说“el tren de rojo”,意思是让她赶紧去找那条红色线上的火车。
其实,学习看似远在“实用学科”之外的小语种,对人的影响就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因为学习西班牙语,我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学校的拉美宿舍区,我的邻居来自墨西哥、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家。我们会买最好的龙舌兰酒,会伴着夕阳穿过普林斯顿大学洒满阳光的街区,去买温热的墨西哥卷,也会一起开车到离学校很远的地方散心,忘掉所有烦恼。
2024年,我开始修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上第一门印第安艺术史课程,课程的重点是讨论墨西哥原住民群体那瓦族的艺术品。我的第一个研究对象是墨西哥城阿兹特克后期,被西班牙殖民军占领时所创作出的门多萨手抄本。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门多萨手抄本专门有一个部分讲述那瓦族人怎么惩罚不听话的孩子,让男孩子参与农活,让女孩子参与家庭工作。虽然这些图画式的语言可能不足以概括那瓦口述语言的千分之一,但通过这些泛黄的草纸,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几百年前阿兹特克帝国的人们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的清晰规划。
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拉美文化的炽热,也认识到了文化核心的脆弱性。一门语言足以支撑起一种文化。同时,对语言的热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追求,这与科技的发展无关。
我想,“斗胆”挑战小语种的每一位学生,都在为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做贡献。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语言的学习是潜移默化的,无论是清晨西班牙语课上品尝的一杯墨西哥热可可,还是夜晚与朋友分享的一杯焦糖柠檬龙舌兰酒,甚至是古巴教授在结课时给我的一个大大的拥抱,都足以激励我把这门语言继续学下去。我希望自己能影响更多人去热爱和重视不同的语言。
(飞也摘自《青年文摘·彩版》2024年第15期,Raven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