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什么,就写什么
作者: 闫红作为一个副刊编辑,我发现很多来稿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写得很抽象、很不具体。
抽象写作更需要功力,写出“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种金句,需要“撮其要、删其繁、比方出来”的本事,非大师不能有。抽象是需要看尽千帆、心有所悟、灵光乍现,再以极其高超的语言艺术锻造出来的,一般写作者做不到,一抽象就变得面目更加模糊。
普通写作者能做的就是具体。并不是说要你去采访,但你必须有具体的感受。有首歌叫《无名的人》,就是对一个群体的具体感受,我觉得送给泥瓦工也可以。
且来看看歌词:“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哭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湿透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
词作者用“没名字”“没有新闻”“没有评论”来表述默默无闻,用“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来写辛劳,用“哭笑着吃过饭的人”“赶路的人”“养家的人”建立一条通道,让这些“无名的人”和大众产生更深的连接。虽然生存状况有所不同,但说到底,大家都是同类。
接下来,场景被继续推进:“你来自南方的村落,来自粗糙的双手,你站在楼宇的缝隙,可你没有退缩。”这一句有一种唤醒的效果,让我想起在摩天大楼上擦玻璃的“蜘蛛人”,正午时分戴着工帽蹲在路边吃盒饭的人。他们背井离乡,在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城市缝隙里谋生,他们的表情里可能会有畏缩,但他们是真正的勇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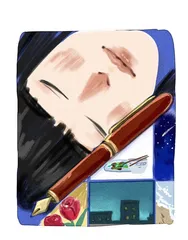
而对回家过年的期盼是这勇敢的根源:“我来自北方的春天,来自一步一回首,背后有告别的路口,温暖每个日落。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再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
你看这是多么动人的具体场景,如在眼前,仿佛能看到主人公听到被呼唤名字回眸时的喜悦。能写得如此具体,是因为词作者对于“无名的人”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把他当成平行世界里的另一个自己。那种悲悯是平等的、入乎内出乎外的,没有一丝优越感,才会感人至深。
张爱玲是金句王者,她能把抽象的东西写得很好,但触动我的,是她那些具体的感知。比如《半生缘》里,曼璐和祝鸿才做局,囚禁了曼桢,想让她给祝鸿才生孩子。为了封母亲的口,曼璐给了母亲一笔钱。张爱玲写母亲后来见到世钧,“非常激动,恨不得马上告诉他。她心里实在是又急又气,苦于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见到世钧,就像是见了自己人似的,几乎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就在这时,她摸到了曼璐给的那笔钱。一般人最多就能写到这里,写她摸到钱就改主意了。但是张爱玲把这笔钱写得非常具体:“那种八成旧的钞票,摸上去是温软的,又是那么厚墩墩的方方的一大沓。钱这样东西,确是有一种微妙的力量。”
这真是神来之笔,神在“八成旧”“温软”“厚墩墩”“方方的”这几个词。这笔钱实质就是顾太太卖曼桢的钱,如果是新的、硬的,就非常刺眼刺心,有钱的锐利感,会让人起防范心,良心会被折磨。
但它是旧的、温软的、厚墩墩的,就体现出钱可亲的一面,让人不能抗拒。
我看到这里,总想张爱玲一定是非常顺滑地写出这句的,因为硬想是想不出来的。把一个母亲出卖女儿的心理过渡写得水到渠成。
张爱玲写钱写得很神,写老师给她那笔钱,包起来,搁在桌上,“像一条洗衣服的黄肥皂”。很少会有人用“黄肥皂”形容一包钱,但正是别人都不会这么想,才出离套话。你再一想,可不就是那样吗?好像那钱就在手边,更感到钱的分量。
这就是写作的笨方法,想要写得好,就要“看到什么,就写什么”。
(朵朵摘自《新安晚报》2024年8月20日,阿砂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