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生活世界
作者: 王小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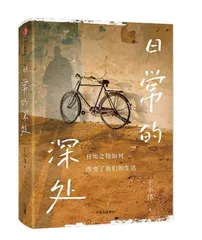
技术哲学家唐·伊德曾写过一本书,叫《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书里提到了创世神话: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最初是赤身裸体的。后来,他们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意识到不着寸缕是羞耻的,开始用无花果树叶做衣服。从那时起,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堕落到了尘世。
伊德用这个故事想要说明,从那一刻起,人类不再能够直接用身体与世界进行互动,而是以人造物(衣服)为中介。当亚当和夏娃摘下无花果叶子做成衣服的那一瞬间,人类进入了一个以技术为中介的世界,不再能徜徉在伊甸园中了。
在中国的古代叙事中,伏羲女娲的创世神话也有类似的情节。伏羲和女娲的造像是蛇身人面,赤身裸体的。在我们的造物文化中,伏羲察天象做八卦,再参八卦造器物,这就是所谓的“观象制器”。各种人造物的原型,都脱胎于此。技术人工物实际上是对天道的一种现实化。之后的人,都要通过器物来体会天道了。
这两种叙事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描述了人的生活世界从天到地、从神圣到世俗的流变。过去的农民还能通过身体直接与世界进行互动。他们在土地上春耕秋收,依靠自己的身体劳动。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掉地上摔八瓣儿。身体和土地接在一起,懂得什么是万物生长。
现在,我们的身体有哪些还与世界直接相通呢?早上起床时,你可能是被手机的闹钟唤醒。起床后,会打开手机看看天气和新闻。接着,你可能会坐车或骑自行车去学校,很少有人会步行前往。
很多人生活在有空调或暖气的房间里,这些房间的温度由技术调节。看世界的时候,需要戴上眼镜,甚至是VR头显。用餐时,可能会叫个外卖,它由复杂的食品工程技术和物流技术加持完成。你上网打游戏,戴耳机听歌,与同学们交流,这些也往往通过社交软件展开。回顾一天的生活,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不是身体与世界的直接互动。我们的视觉、触觉、听觉都经过了技术的调节,之后才接入生活世界。这意味着什么呢?
科技的发展无疑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就之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仅显著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也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老一辈常说,他们那一代人五六十岁时已经步履蹒跚。那时候,科技支持有限,身体需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常常导致健康问题。
如今五六十岁的人还被视为中年人,预期寿命大幅增加了。这些进步显然有部分归功于科技。不过,事物总有两面性,科技的发展既有利也有弊。我们的身体被各种技术建构,虽然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便利,但也不是没有成本。
哲学家阿尔伯特·博格曼认为,过于便利的生活实际上会简化我们对生活的看法。我们将生活工具化,总想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回报,一切都围绕便利展开,这可能会削弱生活的意义感。
大家都学过《愚公移山》这篇课文。愚公移山非常辛苦,有人认为他很愚蠢,所以才叫他愚公。愚公的故事放到今天来讲,就会是另一个版本。现代社会科技发达,我们可以用火药炸开山体,用机器移走碎石,如果山不是太大,不出月余,就能实现愚公的梦想。在科技时代,我们不太能写出《愚公移山》的故事,我们的版本是《工程师大显神威》。
从移山的效果上看,现代科技的效率显然更高。但为什么课本里没有“火药炸山”的故事呢?这一定是因为《愚公移山》这个故事中,除了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和所使用的工具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人文内容。这一内容在现代科技的介入下被解构了。这个人文内容就是人性中的坚韧品格。如果因为现代技术的无处不在而失去了这种坚韧的品格,我们就会感到非常遗憾。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175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叫《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对道德的影响》。这篇文章为他赢得了法国第戎学院征文比赛的一等奖,卢梭从此声名鹊起。在这篇小文中,卢梭提出,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并没有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甚至可能导致道德的退化。
卢梭犀利地指出,科学和艺术的繁荣使人们更加追求舒适、奢华和虚荣的生活,反而忽视了对德性的培养。此外,科学的发展还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知识的积累被少数人所垄断,从而使普通民众被排斥在外。
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当然不认为卢梭说得都对,他也从未把自己的观点当作真理。卢梭凭借杰出的智力和敏锐的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用以审视一切事物中所包含的矛盾和否定性:如果科技发展没有经过任何批判和深刻的反思,就可能招致科学盲信,也可能对人性造成腐蚀和破坏。
我们拥抱科技,并且善于利用科技成果,但对于科学技术,或许需要发展出更加细腻的感知力。在日常生活中,在无数科技加持的活动之外,可以多多尝试那些还能让我们的知觉直接与世界相通的活动。
除了每天看电视、玩手机,盯着各种屏幕,我们还可以拍拍朋友的肩膀,在小路上闲逛,嚼一根狗尾巴草。如果这些都很难办到,还可以伸出手,摸摸自己的脸庞。这些感受,都是我们最为原始的生活印象,它比我们原先想象的要珍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