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本书打开18岁
作者: 姚贝尔工作多年之后,再遇到《围城》,仍能记得18岁那年,在高中毕业的炎热的暑假里,我窝在房间的沙发上看完了这本书。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陌生人”,但似乎又很熟悉,仿佛在我们那个海边的小镇上也能见到。那一年,我马上就要离开那里,去看外面的世界,带着对人性懵懂的认知。
如果用一本书给自己的18岁贴上标签,你会选哪一本?
做一个具体的人
姚贝尔学生/18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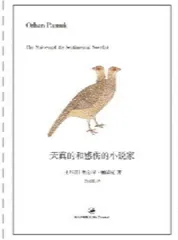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译者:彭发胜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的18岁,是天真的和感伤的18岁,此时的我,是一个极具张力的矛盾体。这一修饰语借自今年读到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天真的"部分与自然融为一体,它率真,不假思索,不矫揉造作,做事不会顾虑后果,不理睬别人的评论。它拥有孩童一般的天真烂漫,对一切事物充满热忱。丰子恺认为:“人类本来是艺术的,本来是富于同情的。只因长大起来,把这点心灵阻碍或消磨了。”我常常在想,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逐渐脱离了这种“天真的状态"?18岁想要"天真"尚且可以,那么随着时间流逝,“天真”会不会消失殆尽?“天真"没有办法装出来,当一个人刻意地去表演"天真"时,就不天真了。于是我决心去寻找"天真”。徜徉在网络空间时,我得到的是一种空虚,而书和电影却为我的生命增添了真实的分量感,于是“天真"失而复得,感伤也变得有质感、更深沉。书和电影是我的第二生活,而第二生活反作用于第一生活。
17岁我看了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18岁我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就这样,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门有关光与影的艺术。
世界影像泛滥,我们走在街上,可以透过商店的橱窗观看自身。街道上的每一块透明玻璃都有一个摄影者,像狮子一般到处游荡,寻找它们可以吞噬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摄影呢?《论摄影》中说:“现在是怀旧的时代,而照片积极地推广怀旧。摄影是一门挽歌艺术、一门黄昏艺术。"摄影使得我渴求美的影像,细致地观察生活。生活中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它们隐藏在各个不起眼的角落。在它们变质与腐烂之前,我必须把"当下"冻结起来。摄影时我的内心充满着自豪感一一自诩为一位时间与空间的雕刻师,再不济也是个创作者。

与"天真的"相比,或许我生命中"感伤的"部分占比更大。若是给"感伤"赋予一个视觉形象,那么它一定是一位沉郁而又痛苦的现代诗人,它写诗的时候是纠结与痛苦的,始终担心风格与技巧的各种问题。它忐忑不安,质疑自己感知到的一切事物,不断地审视与反思自我与他者、自我与世界的关系。18岁有太多的烦忧、焦躁与惶惑,不只是学业上的,还有人际关系和人生方向上的。
我的一个好朋友迷茫地对我说:“每当我发现热爱的事情或者向往的职业,然后去查资料了解它,就会有一堆过来人或局内人让你祛魅,他们不停地唱衰,告诉你这很难、不现实,或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纯粹。”为什么?理想和现实真的如此割裂吗?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梦想?
我常常会害怕让别人觉得“你真是个无聊的人啊”,因为我确实是这么看待自己的,感到生命中常怀一种贫瘠感与枯竭感,很大一部分时间既不天真也不浪漫,经常会“接不住"他人传递给我的情绪,也无法为他人提供一些积极向上的情绪价值。但我在努力让自己的心宽阔起来,看到自己也看到他人。我看到一个个具体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忙碌的人,是关心鸡毛蒜皮的人,是关心世界局势的人,是会幻想和有梦想的人,他们如此灵动、鲜活。
这么小的文字容量只能抓取我18岁的几个模糊片段,但这几个片段已经足够了。18岁这个节点从来都不是连贯的、有秩序的、情节性的,而是像不停加载的、时而顺畅时而卡顿的一帧一帧的电影画面。这部电影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隐喻,你费力地解读它,它却距离你越来越远,而你真切地去感受它,反而豁然开朗了。
18岁的我还有点盲目乐观,时常抱有“侥幸心理”。
不管怎么样,太阳照常升起,18岁的诗与梦还有实现的可能,我们一直在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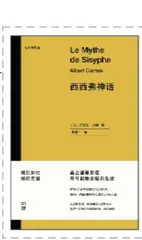
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译 者:袁筱一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黄家光 教师/34岁/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在迈向成年的那一年,很多书绘制了我的心灵地图。很难说哪一本是决定性的。就像一个修行者,每天都在那里重复着一些相似的修行,却在有一天获得了某种突破,但他不知道是哪一天成就了自己。因为不是某一天,而是每一天。所以在顿悟与渐悟中,我似乎更亲近渐悟。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zxtb20250406.pd原版全文
在此写下一些我前行路上的路标。最深刻的痕迹来自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我们也许都知道这个故事,一个触犯神灵的人被处以极刑,每天要将一块巨石推向山巅,但总在最后一步功亏一。他不可能成功,这就是永恒的惩罚。加缪逆转了这个故事的意义,而不是故事的结局。即使我们觉得生活没有了绝对意义(人终有一死),还是可以像西西弗一样,认认真真地去过。“他爬上山顶的斗争本身就足以让一个人的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这段话,支撑我走了很久。身处高中时,总觉得漫长、昏暗、荒谬。后来的生活,不论学习,还是工作,也总会在受挫时显得无意义而荒谬。但认真生活,却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幸福。这本书就放在我高三摆满课本的书桌上。
另一本书是《伊利亚特》。特洛伊战争的故事,诸神与英雄们的故事,阿喀琉斯、阿伽门农但它对我的意义与其说来自内容,不如说来自我与它的关系。在高中最后的冲刺阶段,有好几个月的清晨,我顶着暗夜残留的寒风,成为最早一批到学校早读的学生。我叛逆的心作祟,并没有读课本,而是读《伊利亚特》,直到早读正式开始,我才拿起课本。把《伊利亚特》读完不久,我高中就结束了。我在大一的时候坚持早起,在学校的小湖边又把荷马史诗的另一部《奥德赛》读完了。那是一段串起我从高中到大学的线索,也是我走向成年的线索。我体会到了与古典世界的联系。不久之后,我的兴趣就转向了现代哲学和现代文学。但对古典文学的阅读也一直保留到今天,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自己是一个可以坚持下去的人。
在18岁的书单上,还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曾把里面涉及的诗词全部背下来了;还有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正红旗下》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规则》,以及《庄子》老子》
我总觉得,很多事,不管经过多少的曲折,兜兜转转,好像还是在18岁那年的延长线上。比如在这个阳光温煦的下午,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正在读《致后代:布莱希特诗选》。
作者:蒲松龄出版社:中华书局
“聊斋故事”:有没有“意思
塞林 杂志主编/54岁/教育媒体从业者
常听人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意思自明,无须多言。可是“少读‘聊斋'”,年纪轻轻就读满纸的鬼狐故事会怎样呢?却从没听人说起。
我在读中学时,能够接触到的书很少。读《聊斋志异》,完全是饥不择食的结果。读完家里的那些"演义"和"探案集"后,只能用一种回罔吞枣的态度去啃文言文写的"聊斋故事"了。
故事就是故事,文言文也挡不住故事的魅力:有个“人"喝醉了,竟然身子一倒,变成了一株菊花(《黄英》);还有一面神奇的镜子,狐女把它送给某个相爱的书生,当书生用功读书后去看,镜子里出现的是一张盈盈欲笑的脸;废学几天后,镜子里的佳人却面色惨淡,只肯给一个背影了(《凤仙》)…
“聊斋”里的鬼狐大多数不可怕,有的还挺可爱,诙谐幽默的也不少。比如有个狐仙,跟主人好了以后,平时有客人在时,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有一天,主人办宴席请客,狐仙隐身跟大家一起饮酒笑谈,几个经常与狐仙戏谑的客人分坐左右。狐仙说讲个故事博大家一乐吧。客人怕被戏弄,就说讲故事可以,但不许骂人。狐仙答:“我只骂狐,不骂人。"她讲了一个狐出使的故事,国王问她是谁,答是狐。又问"狐”字怎么写?答曰:“右边是一大瓜,左边是一小犬。”话音刚落,哄堂大笑。 (《狐谐》)
坦白承认,我当年只喜读故事,对于蒲松龄写在后面的“异史氏曰”,一概跳过。
那些故事,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挺迷人,还留着一个未被祛魅的隐秘角落。在这个角落里,嫦娥会降临人间(《嫦娥》),花妖会憔悴而死(《香玉》),鲤鱼会相思人骨(《白秋练》),蜜蜂会托梦求救(《莲花公主》)…
后来,我兜兜转转做了少儿期刊编辑,我发现很多优秀的少儿读物都是如周作人所说的那样:“有意味的没有意思。"这里的“没有意思”,并非指无趣,而是指没有我们成人认知框架里那种现成的甚至"直给"的“意义”。读一本书,最好的审美体验来自“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康德)。再说了,当我们尽情地吮吸了书中那些故事的趣味、甜味以后,“意义"或"意思”的这条尾巴嘛,其实自己会跟上来,想甩还甩不掉呢。
忽然想起一段往事。20世纪80年代,眼见拉美魔幻主义文学大兴,汪曾祺就说,咱们中国古代也有丰富的魔幻现实主义资源,他想改写几篇"聊斋”小说(后来也确实改写了几篇)。有人问:改写魔幻小说有什么意义?汪曾祺悠悠地回道:
你所说的“意义”是什么意义?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zxtb20250406.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