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果飘零 灵根自植
作者: 江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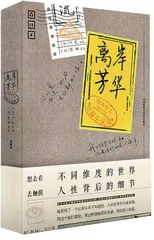
摘要:《离岸芳华》是桂籍华文作家江岚主编的一部海外华文短篇小说集,2019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收录张翎、陈九等人的近作13篇。这些作家中,除赵淑侠之外,其余都是改革开放后由大陆走出国门的“新移民”。他们虽然身处海外,创作重点却放在书写曾经的“大陆经验”;即便故事发生在异国他乡,其中的逻辑与情感仍然是东方式的,整体上体现出一种植根于中国文化的自足感和自信心。
关键词:《离岸芳华》 中国意识 民族认同
20世纪60年代,唐君毅先生写了一篇题为《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的文章。他说:“至于对此中华民族之文化之树之花果飘零,则我自顾己身,同兹命运……梦魂虽在我神州,而肉躯竟不幸亦不得不求托庇于此……唯盼共发大愿心,正视吾人共同遭遇之悲剧,齐谋挽救,勿使吾人沦于万劫不复,则幸甚矣。”[1]这段话既是对海外华人(裔)生存状态的描述,也流露出一种主体身份认同(self-identity)的危机感。从当时的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来看,同样有着这样的特征。“20世纪50至70年代,以吉铮、丛甦、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欧阳子为代表的小说创作,形成了这一时期北美华文文学的主体风貌:其基本主题集中在以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人因‘流浪’(离散)而导致的文化冲突……”[2]其中,於梨华更是被称为“无根一代的代言人”。反观《离岸芳华》中的作品,作家们虽然也写离散的痛苦和文化冲突下的不和谐感,却鲜有身份认同的焦虑,反而体现出一种深沉的中国意识及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
翻开这部集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扉页上的一段话:“湾里布满离岸流,海浪会不停地朝远离海岸的方向推。我觉得我有好几辈子可以活,直到离岸流把我的灰带走。”这段话引自凌岚作品《离岸流》,起到点明全书主旨的作用。“离岸流”,比喻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海外华人(裔);“海浪会不停地朝远离海岸的方向推”,喻示着他们如“花果飘零”般的命运及散居世界各地的生存状态;在“我觉得我有好几辈子可以活”这句话中,“我”显然不是指个体有限的生命,而是指“我”所属的中华族群及其强大的文化生命力,让人不禁联想到“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经典诗句。
中国意识的彰显
“中国意识”一词用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最早或见于饶芃子、杨匡汉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中。
“中国”一词在种种语境中,意义在种族(race)、民族(nation)、国家(state)之间滑动,再加上经常与“爱国主义”“祖国”之类情感意味极浓的词语互用,含义变得模糊、微妙。“中国意识”这样一种表述,也许能涵盖“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祖国”“传统”“现代”“炎黄文化”等词语群所包含的诸多种族本能与拯救理想。[2]
从根本上说,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在双重或多重文化语境中生活并思考的。在此背景下,自觉地运用汉语写作,本身即反映了作者对中华文化的亲和与依恋,是“中国意识”的文本体现 。从《离岸芳华》的内容来看,“中国意识”最突出的表现是对“现实中国”的关注,张翎《都市猫语》、施玮《校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都市猫语》写的是都市小人物的生活。男主角叶茂盛是出租车司机,女主角赵小芬是洗脚妹,两人素昧平生,因在同一个城市打工、合住一套廉租房而相识,展开了一段短暂的“同居”生活。笔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视角讲述着他们谋生的艰难:“‘抽了烟,日子好过些。’女人说到‘好过’两个字的时候,咧嘴笑了。茂盛发现她的门牙已经染上了一丝黄渍。”内心的孤独:“手机活着,他就活着。手机死了,他就成了个四面是水的孤岛,连岸的影子都找不到。”生理上的压抑:“女人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纸包,塞到他手里:‘一会儿再打开。难熬的时候看一眼,说不定好受些。’……茂盛打开纸包,是一条内裤——那条黑色的、缝着蕾丝、钉着一朵红玫瑰的内裤。”同时,小说也真实地再现了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例如,便捷的电子支付方式:“加上支付宝里的三千块钱和微信钱包里的一点零钱,那就是他在这个城市里的全副家产”因资本涌入而“卷”得厉害的出租车市场:“这阵子满街都是载客的车,滴滴、优步、神州……百样千般,的哥的生意清淡了很多”[3];如此等等。
叶茂盛和赵小芬代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阶层——外来务工族。作者对该群体的关注,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共情(empathy)心理的自然流露。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新移民”作家,大多是知识精英,文化水平与城市打工族有着天壤之别。但同样作为外来“移民”,他们也有着举目无亲、孤独无依的感受,甚至更加强烈。“这地方过日子,媳妇就是半壁江山。美国几亿人咱认识谁,谁认识咱呀?”[3]于是,当他们在海外站稳脚跟、回望大陆时,猛然发觉打工族身上仿佛有着自己的影子,一种共情、同理之心油然而生。
《校庆》描绘了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的众生相。故事发生在国内某偏远县城,背景是县中82届高三(1)班毕业生参加校庆举办的一次聚会。聚会当天各色人物陆续登场:有看淡世情、临近退休的老校长和左右逢迎、心有不甘的副校长(当年的班主任)倪鸿书,学生中有仪表堂堂、无耻贪婪的县教育局长高陆云,柔弱善良、内心坚韧的孤儿院院长李梅,外表儒雅、人格卑下的县文化馆副馆长秦怀远,一心从教、不问世事的县中学教师区萍,投机致富、乐善好施的矿老板陈三铁,落魄潦倒、童心未泯的流浪诗人王一,外表光鲜、孤独无依的海归吴韵梅。作者不仅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还交代了他们彼此间的关系:高陆云要替小舅子(全县有名的黑心包工头)揽下县中新教学楼工程,倪鸿书为此惴惴不安。区萍本是倪鸿书的学生,眼看自己当年深爱的班主任蜕变为卑微的小官吏,她心中满是鄙夷。陈三铁一直暗恋着班花吴韵梅,他与李梅的结合不过是出于同情与呵护,现在人到中年两人的婚姻似乎也走到了尽头。吴韵梅与秦怀远是当年班上公认的一对,但秦怀远为了前途,大学毕业后与县文化馆馆长女儿成亲,吴韵梅也远走异域。如今秦怀远离异、吴韵梅新寡,两人均有意再续前缘。众人中唯有王一孤傲不群、了无挂碍,席间毫无忌惮地嬉笑怒骂。
故事的格局并不大,人物的工作、生活也大多局限在小县城。不过,校庆和同学聚会都是极富中国特色的全民社交活动。82届高中毕业生即人们常说的“60后”,他们大多事业有成,儿女也已成人,但同样有着如高陆云、秦怀远、区萍一般种种困扰和烦恼。这些精心设定的故事背景和主要人物,使小说有了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意义,可视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家园记忆的呈现
“中国意识”另一个层面上的表述,体现为小说文本与“家园记忆”间的内在关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回家变得十分便捷,过去那种由于政治或经济原因造成的难解的乡愁,对“新移民”来说已成为历史。但也正因为经济的发展,祖国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记忆中的家毕竟是越来越远了。于是,思乡之情不仅因空间的距离而强化,也因时光的流逝而累积,唯有通过文学创作,借助各种文化意象去构建故乡图景,以此来纾解乡土情怀带来的焦虑和忧伤。
张翎是浙江温州人,她的作品《玉莲》写的是“我”童年时的保姆玉莲,故事中充满“我”的家园记忆。如写夏天的雨,“是那种江南特色的不成点也不成条的淅淅沥沥的雨,码头的泥浆厚厚重重地黏着我的鞋底”;写四月天的街景,“从街头到街尾都是阳光,照得人遍体酥痒,沿街的夹竹桃树一夜之间就绽出了满树的红点”;写日常饮食,“玉莲的菜篮子里放着一条肥大的金灿灿的黄鱼,一大捧包在荷叶里的满是污泥的白蚶,两根碧绿的黄瓜”;写玉莲的声音,“软软的,让我想起家里过年时蒸的桂花糯米糖糕”;写玉莲害羞的模样,“像是在生宣纸上滴了一小块丹朱,慢慢地洇开去,从双颊洇到额头,再洇到脖子”。[3]就在这细腻又充满江南情韵的笔触中,作者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还乡之旅。
谢凌洁是广西北海人,其作品《辫子》写的是少年“秧子”的故事,寄托着作者对故乡的思念。秧子生活在一个名叫“湾仔”的热带渔村,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古朴自然、近乎原生态的气息:“从半坡看‘湾仔’,最好坐在小叶榕的气根疙瘩上。当地人说,榕树有几百年了,杆子粗壮,枝叶婆娑”;“大清早,村口的雾团着在地上打滚儿,秧子跟在牛屁股后面,看着他的牛和雾赛跑”;“地上满是牛屎,黑乎乎的,有一股青草和粪便混着的味道,把人呛得难受”;“他到村外的田垄里去,那里有空旷的田野和绿油油的菜地”;“秧子在草屋里抓蟑螂、蚂蚁,玩够了,就躺在草堆上,睡着了”。[3]这满是乡土气息的描写,凝成了一幅阔别多年却又记忆犹新的家园图景。
在陈九《纽约春迟》中,故乡是胡同:“钱粮胡同我那时天天走,里面有条小巷正对隆福寺后门,可以抄近道儿”;“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没住过胡同能算是北京人?”故乡是香椿芽炒鸡蛋卷春饼,外加绿豆粥:“按说现在正是香椿下来,老鲍,还记得咱北京胡同的香椿芽炒鸡蛋卷春饼,外加绿豆粥,什么劲头。”故乡是又脆又甜的冬枣:“还记得咱胡同里的枣树吗?我们纳兰府北院儿那棵枣树,专拣下霜的时候结枣,号称冬枣,又脆又甜”。一个个老北京意象,以满是京味儿的乡音娓娓道来,回忆中“我”又找到了内在的生命之源,“纽约的椿树很多,全是臭的,从来没遇到一棵香椿,难怪人家说一方水土一方人。”“美国这鬼地方不光没香椿,还没枣树,怎么咱中国有的它都没有。”[3]
个人化的意象是独特的,构成“我”记忆中的故乡图景;而那些具有东方符号意义的人文景观、服装饰品和古典诗句,等等,则唤起了海外游子们对故乡的集体记忆。如陈谦《我是欧文太太》中的“阳朔西街”“围巾两头中国灯笼式的须结”“狐狸的大尾巴看上去有点像水墨画上洇出的小花”;凌岚《冰》中的“山重水复疑无路”“千年一瞬,白驹过隙”;曾晓文《卡萨布兰卡百合》中“透露出东方的精致和风情”的“紫色丝绒绣花拖鞋”“她唱的是京剧”。[3]其实,这几部小说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写“家园记忆”之作。但是,文本中那些饱含中国文化意义的语词,植根于东方古典的美感经验,无不指向一个更悠远、更广博的“故乡”。对于那些从未踏足故土的华裔来说,或许这就是故乡、家园的全部含义吧。
身份认同的思考
“主体身份认同”是西方早期启蒙哲学提出的一个概念,思考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将到哪儿去?关于这些问题,上述作品通过对现实中国的关注和乡土情怀的表达无疑已给出了部分答案。但是,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下,关于故乡的记忆是“块茎”(rhizome)式的,它是海外游子的一种感觉,介乎于真实与不真实之间。与此相应,主体身份的认同也不再恒定不变,而是被解构为残缺不全的思想碎片。因此,就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来说,《离岸芳华》的另一大亮点体现为作者对主体身份的思考和认同。
比如,陆蔚青《楚雅如的寂寞》。小说讲的是加拿大华人威廉和楚雅如的情感故事,威廉“虽然叫着洋名,其实是个第二代的华裔”,楚雅如“倒是有着一个中国名字,却是个由里到外都西化了的中国女人”。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两人感情的发展并不顺利。小说的结尾写道:“威廉和楚雅如都陷在寂寞之中。他们坐在对方的对面,无言地寂寞着,因为爱情那矛盾而复杂的多面性。天空最后一丝光正在飞走。其实按照光速计算,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那光源自身早已消失了。”[3]或许,雅如就是那“最后一丝光”,“正在飞走”象征着她和威廉日渐疏远的关系。威廉眼中“光彩照人”的东方女人雅如其内在早已改变,就像那光源已消失的“最后一丝光”。这样看来,那“无言的寂寞”不仅是情感上的,更是文化上的,是难以融入欧美文化、社会的困惑与孤独。
又如,赵淑侠《美女方华》。方华是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女性,前两任丈夫都是飞行员,抗战中为国捐躯。1954年,她只身来到奥地利维也纳学习声乐,后来嫁给长自己20岁的史顿赫教授,现以史顿赫太太的身份住在养老院。方华是“芳华”(美好年华)的谐音,小说以养老院实习护理玛丁娜的视角讲述着史顿赫太太(老去的方华)对青春韶华那近乎痴狂的留恋。“原来她看到年轻的方华在沿河的小路上走着。那方华穿了一身浅紫色的连衣裙,雪白晶莹的肌肤,浅笑盈盈……史顿赫太太不禁神迷,从心底产生倾慕之情……无论她怎样召唤,那方华都不睬不理,只是兀自淡笑着在河岸上徘徊。”这年轻的方华是史顿赫太太的幻觉,是她的青春记忆。留不住的年轻方华固然象征着一去不返的青春,但对侨居海外多年的史顿赫太太来说,或许还意味着那记忆中早已模糊了的“我”,那在时光中逐渐被解构的主体认同。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在弥留之际拒绝承认史顿赫太太是方华。“‘那是方华,史顿赫太太。你就是方华,方华就是你。'情急之余,玛丁娜倏地灵机一动,换个方式激一激,满心期望能收到效果。可是那史顿赫太太自始至终都无变化,一直两眼空空地对着天花板喃喃不绝地念叨:‘那不是方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