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怍”之意从何而起
作者: 谷妙妙 时曙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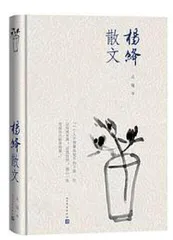
摘要:《老王》是杨绛的一篇散文名作,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和平和的语言塑造了生活贫苦却始终保持善良的老王形象,和心怀善意却对老王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我”的形象。本文首先对散文《老王》中人物形象展开了剖析,并对语言进行了品读,进而分析散文在深层意蕴上对个体“幸运”与“不幸”的思考,解析叙述者“我”对老王的愧怍之情的复杂性。
关键词:《老王》 杨绛 愧怍
《老王》是杨绛1984年创作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被选入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全文围绕作者一家与老王的交往展开,通过回忆老王窘迫的生活状况以及作者与老王之间相互交往的场景,展现了特殊时代背景下老王与作者一家弥足珍贵的友谊,凸显了孤苦寒微的老王纯朴、善良的品德,表达了作者对‘小人物’人性之美的讴歌,对不幸者的悲悯关怀,对自身的反省以及对命运的慨叹。”[1]“实用性阅读与交流”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新创设的发展性学习任务群之一,旨在引导学生“通过整体感知,把握散文内容,体会其中的思想感情;并能对文章主旨、人物形象、语言特点等做出明确的赏析和评价,进而形成独特的阅读体验。”[2]在细读本篇文章时,不能仅仅解读文本的表面,还要潜入文本深处,抓住文章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语句,结合语境进行具体的分析,品味杨绛散文“沉定简洁”的特点,品析“愧怍”的深层含蕴。
《老王》的人物分析
“老王”的形象解读。一是地位低微和命运悲惨的老王。从身份地位看,老王是三轮车夫,单干户,没组织,只能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维持生计,社会地位低且收入不稳定。孤苦伶仃,没有亲人,“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从生活条件来说,住在一个荒凉破败的胡同里,院子破破烂烂,只有几间塌败的小屋,生活条件艰苦,而且那里并不是他真正的家。从生理上来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就看不见,导致乘客不愿坐他的车,进一步影响老王的生计。老王的职业、身份地位等决定了他在生活中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身世孤苦,命运悲惨。
二是知恩图报和为人善良的老王。作者的女儿送鱼肝油治好了老王的眼疾,这让老王感激了一辈子。他给邻居家送冰,愿意给“我”家代送,且车费减半。“文革”期间,作者一家被贴上了“反对学术权威”的标签,旁人避之不及,老王却冒着生命危险在默存生病时送他们去医院。尽管老王自己贫困潦倒,但不愿收取车费。老王临终前忍着疼痛给“我”送来了香油和大鸡蛋,只为了报答“我”家对他的情谊。从这“三送”可以看出老王的知恩图报,他始终未改淳朴本性,虽然生活贫苦却始终保持善良。老王对其他人同样怀着良善之心。“在三轮车被取缔载客后,有位老先生愿意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害怕乘客会掉下来,就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了半寸高的边缘。”即使自己的生活千疮百孔,老王也不忘帮助他人、关心他人,困难之际仍存仁义之举。
“我”的形象剖析。一是故作冷漠的叙述者。“老王”是一个用于指代年长男性的非正式称呼,文中的“我”对车夫始终仅以“老王”相称,在交往过程中从未提及他的全名。这似乎表明了“我”对老王的某种忽视或冷漠。此外,“我”谈到老王凄苦孤单、无依无靠的人生处境时,说“据老王自己讲”,这暗示是老王主动透露了自己的身世,并非“我”主动询问。在老王生病期间,“我”也未曾主动看望,甚至在老王临终前送香油和鸡蛋时,第一反应也是吃惊而非关心。接过老王的东西,“我”没有邀请他进屋坐,而是转身去拿钱,即使老王明确表示不要钱,“我”还是坚持给了。老王离开后,“我”没有去搀扶或送别,只是冷漠地看着。直到十几天后碰到老王同院的老李,“我”才想起询问老王的近况。在得知老王逝世后,“我”也没有追问具体情况或丧事安排等问题,这进一步暴露了“我”的冷漠态度。孙绍振认为“冷漠是最根本意义上的丑”“我”对老王的冷漠似乎与老王的老王淳朴善良形成对比。
二是充满善意的知识分子。冷漠和疏离之外,“我”又始终保持着对老王的善意的帮扶和无声的关注。散文开头第一句“我常坐老王的三轮”,开门见山地表明老王是一个车夫,“我”是顾客,一个“常”字则可以看出“我”经常照顾老王的生意。“我”明明知道老王身体残疾,天黑可能会看不见东西,但是仍然选择坐他的车,可见“我”对底层小人物的善意。“我”对老王的关注和同情,不仅仅是出于个人情感,更体现出知识分子对那个时代所有弱势群体的关怀。
三是敢于剖析自己的反省者。在文章的结尾处写到,看到没动用的香油和鸡蛋,“我”一再追忆自己和老王的对话,反思自己是否给老王造成误解和伤害、与老王交往中的金钱交换是否恰当。多年过去,“我”依然在道德和情感上不断地进行自我剖析,为自己最初因身份差异而产生的俯视心态,未能真正理解老王的情感世界,对老王的关爱不够真诚和深入而感到不安和愧怍。
《老王》的语言分析
杨绛的散文语言简洁、幽默,文章结构看似“随意”却又颇具匠心,杨绛不刻意追求文章的技巧,总是用平淡质朴的文字给人深思。[3]
《老王》多用白描手法,文章的情感渗透于字里行间。开篇写她经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说着闲话。”简单的语句勾画出了“我”与老王的日常交流情形,表现出二者身份上的天差地别,也凸显出了“我”和老王之间存在隔膜的原因。
《老王》语言的平淡凝练还体现在对句式的使用上。“多用短句,使文章看起来短促有力,口语化的语言给读者以质朴的感受。”[4]如“他靠着活命的只有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这句话没有华丽的装饰,紧促的短句和平淡的叙述中暗含深厚的情感,蕴含着作者对老王的深深同情。“有个哥哥”,让人感到一丝温暖,紧接着“死了”,温暖立马变得冰冷;“有两个侄儿”,似乎又给人一点希望,接着“没出息”又使人陷入无望,简单的话语将老王孤独无助、无依无靠的悲惨命运渲染到了极点。
《老王》语言幽默诙谐、嘲讽之中带着优雅。在文章中,杨绛巧妙地运用了对比和诙谐的手法,将作者和老王发生的旧事娓娓道来,如写“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这里“前任”一词常用于更为正式的场合,但在这里却带有一种诙谐幽默之感,能够让读者感受到老王的艰苦,同时也能体会到作者对老王的尊重。再如“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作者使用了略加调侃的语言,既表明了老王所处的境况,又讥讽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同时抒发作者对老王这一类人的同情与关心。
丑中见美。“在刻画老王的人物形象时,没有用‘诗化’的语言来描绘,而是将老王的相貌描写得十分丑陋。”[3]如“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面如死灰,眼上结翳,形如僵尸。”用极富表现力的动词和夸张性的比喻刻画出了老王病入膏肓、萎靡不振的形象,将老王孱弱、僵硬的身体状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也引起了读者的怜悯。孙绍振认为:“这样刻画老王的形象从美学的角度上来说是更为深刻的,其一,内心的美在外表丑陋的反衬下,更令人惊心动魄;其二,美的品质是平凡的,自然的,可以用平实的,非诗化的词语来表现美。”[6]
《老王》一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展开叙述,使读者感到亲切真实。文章语言质朴、幽默、细腻,塑造了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老王和叙述者“我”的形象,引起读者对老王的无限同情,传达了作者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善意和对自己、对社会的深刻反思。
《老王》的主旨解读
作者在文末写道:“这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想要真正读懂《老王》,就必须理解“幸运”与“不幸”的真正内涵,理解谁是“幸运”之人,谁是“不幸”之人,理解“愧怍”之情因何而起。
幸运与不幸。谁是“幸运的人”?谁是“不幸的人”?“幸运的人”似乎是“我”,虽然因时代原因遭到迫害,但勉强可以度日,还有家人在侧,更有幸遇到善良的老王。可是结合纪实性散文中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杨绛夫妇被贴上“反对学术权威”的标签,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甚至被剃了阴阳头,女婿也因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自杀了。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就是莫大的不幸。可是杨绛笔下的“我”,却显得平和从容,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那谁是不幸的呢?老王是不幸的。老王的不幸首先体现在老王的身世上,孤苦无依,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其实老王的不幸不仅包括生理方面的不幸,更包括精神方面的不幸。老王有一只眼是“田螺眼”,瞎的,因此遭到了各种凌辱。非议说这老光棍年轻时不老实,害了疾病,瞎了一只眼。其次,在老王的眼中,他把“我”当成了朋友和恩人,即使在病入膏肓的情况下仍然强撑着身体的不适,给“我”家送来了香油和鸡蛋。然而“我”在和老王的交往中始终保持着距离,老王的善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和相应的尊重。
愧怍。“愧怍”即因为做错事或未尽到责任而感到惭愧。“我”为什么会对老王感到“愧怍”?原因有三。第一,在“我”眼中,“我”和老王是“主顾关系”“我”坐老王的“三轮车”,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知识分子对底层人物的一种同情与怜悯,而老王却把这种同情理解为了友情甚至是亲情。双方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错位。多年后,当“我”明白了老王深沉而真挚的情谊时,油然而生“愧怍”之情。第二,老王临终前拖着“直僵僵”的身子送来香油和鸡蛋时,“我”并没理解老王的用意,不但没有让老王进家门,还坚持付钱。当老王去世后“我”才领悟到老王拿着的香油和鸡蛋是来表示感谢的,而“我”却用钱去“侮辱”了老王,心中难免充满了愧疚与懊悔。第三,“我”作为知识分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看着成千上万的平凡的人物遭到社会的迫害,无法担负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因此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愧怍。
正如孙文辉所说:“面对每一个不幸的人我们都有愧怍,只是杨绛首先把自己浸入愧怍之海中,用‘隐者’的心态去思索。”[6]其实,杨绛的“愧怍”本质上是知识分子对底层小人物真善美背后所表现出的愧怍之意。《老王》是一篇富有反思意义的讴歌人性之美的作品,通过展现的个体“幸运”与“不幸”,引发读者去讨论人情人性、人的价值和人的意义。
作者单位: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参考文献
[1]温儒敏,王本华主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2]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3]宋宇.《老王》教学课例比较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21.
[4]李淑红.似水胜酒,古味虽淡醇不薄——从《老王》看杨绛散文语言的平淡之美[J].语文教学之友,2010(08).
[5]孙绍振.贴近发现“愧怍”的自我[J].语文学习,2007(04).
[6]吴芸芸.反思三重境——杨绛《老王》的文本解读[J].中学语文,202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