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诵法》出版创作动因、核心内容与学术价值
作者: 高国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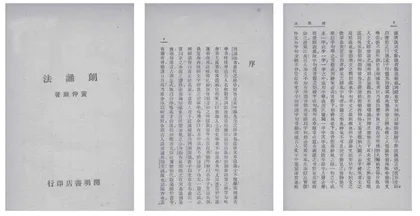
摘要:朗诵是随着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的推进、白话新诗的出现而衍生出来的一种口头传播与表达方式。黄仲苏1937出版的《朗诵法》不但接续、辨析中国传统诵读方法的指要,而且拓展、诠释现代中国诵读发展的新维度,为传统诵读的现代化转型架起一座桥梁。通过对该书作者、创作动因、核心内容、学术价值进行深度理析与总结,对通过经典诵读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有声出版物的创作,提升朗诵的美学境界,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关键词:朗诵法 诵读 借鉴与参考
诵读自古以来就被作为传统的读书方法和文化传承的手段而被学人士子广泛使用,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与提升。而朗诵是随着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的推进、白话新诗的出现而衍生出来的一种口头传播与表达方式。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巨变时期,也是各种思想与文化相互碰撞的历史阶段,“诵”与“读”的实践与学术研究也非常活跃,相关著述颇丰,粗略统计,相关论著就有300多篇(部),被称为“当代绝学”的《朗诵法》不但接续、辨析中国传统诵读方法的指要,而且拓展、诠释现代中国诵读发展的新维度,为传统诵读的现代化转型架起一座桥梁。
《朗诵法》概况
1936年7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黄仲苏所著《朗诵法》一书。这是现代以来我国第一部全面总结朗诵方法的专著。全书共分18章,从发音、呼吸、中国文字特性、文法、音节、风格、姿势、表情等方面讲述朗诵方法,书由钱基博作序。
关于作者。黄仲苏(1896—1976),原名黄玄,笔名更生、醒郎,安徽舒城人。1918年与李大钊等人组织中国少年学会,1921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文学院,1924年8月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曾任《少年中国》《少年世界》主编,国立武昌师范大学、省立南京东南大学、私立上海大夏大学和私立光华大学教授,上海市政府特别秘书,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1931年曾出任墨尔本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光华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及中文系资料室主任,从事世界文学史、英文现代散文写作等教学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著作有《朗诵法》《法兰西近代文学大纲》《陈迹》《音乐之泪》等。
创作动因。一是少年私塾古文教育与学校国文教育对诵读不同态度的困惑。诵读是中国传统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是一种通过声音对文字、思想、情感、精神和人生进行感悟的行之有效的、千年传承的学习方法。“愚少时,从周士芳先生读书。先生为讲解《左传》,并纵声朗读,抑扬顿挫,甚有情致。心好之,刻意仿效,居然酷肖。”新文化运动前期,反对古文与旧体诗,反对诵读文章,“年十六,去家塾,入学校,功课既多,终日营营;而教师之授国文课,但重讲解,不事朗诵,遂发吟哦。然未尝一日敢忘先生之所嘱咐也。”一些所谓的“士子”鄙视国文诵读,“以为不足学,实则未尝一读”,在授课时,很多经典的值得记忆成诵的作品“仅以一讲一看而了之。”二是欧美诵读的现状及中国当下的现实比较。黄仲苏曾留学欧美,与诗结缘,翻译、介绍外国诗歌、撰写诗文评论。“留学欧美时,曾习外语教学法,观其教授吟咏讽诵种种方法,似有所悟。”“西方作者,无不于诵读下功夫。一篇之成,必开朗诵会以质正于名家。”回国以后,从事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时发现,古籍中很少有关于诵读的研究,而且此时白话文教育又摒弃传统诵读教学。“因于音韵训诂方言等学,略窥门径;乃进而求古籍中所载关于朗诵之理论及记述,所得又百数十条,然终未见有言及读法者。岂古法之失传,抑今人之忽视朗诵耶?”黄仲苏在绪论中告诉我们“可知吟、诵、咏、讽之要,在能领会诗文之意境,风趣、情感与思想。”但是,“今人之只知看而不重读,或读之而不得法,未能解得其中神味与妙旨者,皆不免于‘望城而止’之识耳。”这是他撰写《朗诵法》的根本原因。
出版时代背景。一是中国文人的诵读传统自辛亥革命后开始淡出学子视野。诵读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学习方法,从先秦至清末,从未断绝。鸦片战争以后,西学渐入,改革风行,对中国固有之传统冲击甚大。在1904年1月政府颁行《奏定学堂章程》时,对吟诵古诗还比较重视,参加科举考试就必需读诗诵经,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绝大多数年轻人对读诗诵经失去了热情,1912年1月19日,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废除公立小学读经科课程,同年五月又废除中学读经,并同时废除各级师范学校读经。虽然接受过旧式教育的一些教师还在努力维护“诵(美)读”“吟唱”的教学地位,但总的看来,语文课堂里“读”风趋于衰落,“讲”风渐渐强劲起来。虽清末之士人意欲起而振之,或结社联吟,或撰文呼吁,或躬身示范,大力强调传统吟诵在创作、教化等各方面之作用,但终将难挽颓势。
二是“白话文运动”冲击传统诵读的赓续。在当时否定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下,私塾的废止、新学堂的改革、白话文教材的推行确实给传统吟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旧式的国文教学最为五四运动以来所诟病的,就是专重诵读。这种看轻诵读的风气,使一般中学国文教师耻于范读,学生也以诵读为可耻的事,于是学校里只讲不读。”朱自清先生曾生动描述了当时诵读的尴尬境况,“五四以来,人们喜欢用‘摇头摆尾’去形容那些迷恋古文的人,摇头摆尾正是吟文的丑态,虽然吟文并不需摇头摆尾。从此青年国文教师都不敢在教室里吟诵古文,怕人笑话,怕人笑话他落伍。”诵读式微,使中国的学人从此失去了由声音所创造出的独特世界,也使得其理论领域一直如冰封的厚土,乏人开垦。
三是随着广播的出现,“听”使得以口语表达为主的诵读重新进入众人视线。1923年1月23日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声音”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如果说在推进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文学发挥了难以估量的核心作用的话,那么,以“听觉”作为媒介的文学传播就应当成为构成这一历史进程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而且,在不断更新的技术手段的支持下,人们对文学所传达的“现代”意识的接受,不只是“看”,而主要借助于“听”。随着广播的不断普及与广播节目的日益丰富,名人的演讲、诗词的朗诵等,让通过声音表达文字的朗诵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技术”让朗诵焕发出新的生机。此外,中国文人几千年传承的读书方式至此面临着衰歇的危机。对于这样的情势,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些有识之士倾力提倡传统吟诵,不忍见到这份文化遗产日渐消亡。
《朗诵法》的核心内容
《朗诵法》除绪论与结论外,共18章,从四个维度阐释朗诵之法。
从生理科学的维度解析发音方法与气息运用。包括发音机关之解剖、发音机关在语音上之作用、发音与呼吸、发音之错误及其纠正方法四个部分,“要在使习朗诵法者得了然于发音机关之位置,及其在语音上之作用,并解释呼吸与发音之关系,且说明发音之错误及其纠正方法,俾得辨别抗喉、矫舌之差,攒齿、激唇之异。盖亦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微之本意也。”科学揭示了朗诵创作者准备阶段对呼气器官、气息调整、吐字归音的处理等内在逻辑与制衡关系。
从汉语言文字学与语音学维度讨论音韵、国音及地域时代之区别。包括中国文字之特性、四声与五声、双声与叠韵声韵之拼合、语音与地域及时代、国语标准音之重要等五个部分,“吾国标准音虽经规定,唯推行未广,而国人狃于积习,每诵诗文,辄喜用故乡土音。此于个人研究,固无不可,然习久不察,则于教课,或公开集会时,朗诵古今诗文,及个人创作,颇感困难,且于国语之推行亦为碍殊多。此或为吾国古代朗诵法失传,而至今犹无人提倡之一重要原因乎?故习朗诵法者不得不谙习国语之标准音;否则,朗诵法之推行终难以普遍也。”通过汉语语音演变历史的梳理,提出朗诵应该统一使用“北音”,有利于推广与普及教育,符合当时推广国语及后来推广普通话的国家语言政策。
从创作的维度去诠释朗诵声音特色、作品体裁与风格表达的呼应关系。包括朗诵实践指导、腔调之构成及其作用、标点符号、文法、音节、体裁、风格等七个部分,前十章于发音、吾国文字特性及读音等已略加解释,且说明其对于朗诵法之重要矣。这部分主要从朗诵实践出发,根据文章的体裁确定朗诵风格,通过标点符号、音节及声音特色实现作品与声音的高度契合,彰显有声语言作品的艺术特色。
从非语言符号系统的维度拓展现场朗诵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研究。包括姿势之纠正、表情之商榷两部分内容,由于朗诵已经从读书的自我天地发展到面对受众的表达,因此,姿势与表情就成为关注之点,“朗诵姿势,宜端庄,勿拘泥;宜舒适自如,行所无事,切勿做作;无论坐或立,皆应抬头,挺胸,举目四瞩,切忌摇头,摆身,弯腰,曲背诸丑态。”除姿势需要有一定规制外,面部表情应与朗诵的作品相契合,因为朗诵“则公众观瞻所系,其表情状态,大有可讲究者矣。”当然,对于姿势与表情的研究,当时也有不同看法,“总而言之,本书为一般学者不可不阅一读物。著者于第十七及十八两章中,讨论姿势及表情,盖一旦于朗读诗时舞蹈之,恐有反将原文意义失真之处。”
《朗诵法》的学术价值
“中国诵读虽讲究,然不多不传其法,又无专考究,故讽诵者往往各自为声。有读之不得其法者,其咿哑啁哳;颇难为听,且全失篇中神韵。”而《朗诵法》一书不仅对朗诵的分类与方法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而且对发音与呼吸也作了相关阐释,其学术价值受到充分肯定。钱基博撰《序》称:“《朗诵法》者,当代之绝学,而吾友黄仲苏先生之所著也。”总而言之,本书为一般学者不可不阅一读物,可称空前之作。这可说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朗诵方法的著作,书中虽也论及语体文的讲读方法,但主要谈的还是古诗文的吟诵方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诵与读内涵的古今阐释与四类“朗诵腔调”范式确立。在古代“诵”与“读”是有区别的,黄仲苏比较二者不同说:“此盖明言诗书可诵,而典礼则仅供阅读而不必诵者也。古人之所谓诵者,今人则曰读; 而古人之所谓读者,今人则称之为默读,为阅读,为看。”从黄仲苏先生的阐述来看,在论及到诵、吟、咏基本内涵的不同及诵读、吟读、咏读三者功能的区别的同时,黄先生还是给我们指明了一个研究方向:那就是近义单音词由于其产生的时代与背景不同,因此在表情达意时肯定有所区别;由近义单音词组成的复合词肯定也带有其母体的某些基因,这些复合词在表情达意时也肯定有所区别。
黄仲苏先生在《朗诵法》中“审辨文体,并依据《说文》字义及个人经验”确立了四大类“朗诵腔调”,具体范式:一曰诵读,诵读之而有音节者,宜用于读散文,如诸子、《四书》《左传》《四史》以及专家文集中之议、论、说、辩、序、跋、传记、表奏、书札等等。 二曰吟读,吟,呻也,哦也。宜用于读绝诗、律诗、词曲及其他短篇抒情韵文如诔、歌之类。三曰咏读,咏者,歌也,与咏通,亦作永。宜用于读长篇韵文,如骈赋、古体诗之类。四曰讲读,讲者,说也,谈也。说乃说话之“说”,谈则谓对话。宜用于读语体文。
诵读,依黄先生所言,“诵读”的对象是诸子、《四书》《左传》《四史》以及专家文集中之议、论、说、辩、序、跋、传记、表奏、书札等等,也就是说“诵读”的对象不包括诗词曲等韵文。毫无疑问,这一观点是很有道理的,理所当然地得到朱自清先生、陈少松先生等人的赞同。
接续传统诵读技艺并对朗诵进行理论总结与提升。作为一种读书方法,诵与读是为学习经史子集诗词曲等韵文服务的,这种客观现实,造成了历朝历代的人们只把它作为学习工具,却从来不把它视为研究对象;而诵与读的传承在那种文化技术条件下,所依赖的只能是父子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不可能有其他传承渠道。虽然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文人传承弘扬的诵读教学法,衍生了“因声求气”“涵泳”等术语,但其诵读体验多侧重于作文玄机与古典韵致,还不能够达到现代的审美高度,作为一种学习技能,还停留在泛泛强调与印象式的比喻上,缺乏科学性。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言,他看过许多有关诗论、词论方面的著作,其中许多地方都谈到“吟”“啸”的,但没有一部著作谈及如何吟、如何啸的。正是前人极少论及诵读与吟咏的具体方法,没有论及诵读与吟咏的理论依据。这两种客观事实造成了诵与读在流传的过程中只有技术层面的传承,没有理论层面的研究。而黄仲苏的《朗诵法》突破中国文人只专注于对书面语言的研究,而很少有人研究用声音将“词章妙语”表达出来的窘境,上接桐城派诵读理论,下续现代朗诵科学指要,为传统诵读的现代化转型架起了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