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高龄老人居家照护服务利用与政策优化:基于群体差异的潜在类别分析
作者: 贺小林 梁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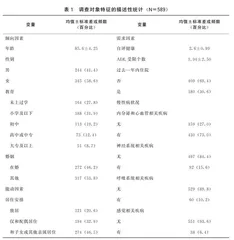
摘要:城市高龄老人居家照护服务状况直接关切到老人的生存质量,是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的根本基础。基于上海市高龄老人居家照护服务调查,运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对城市高龄老人群体的居家照护服务利用类型、结构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将高龄老人居家照护服务分为全方位医养型、养护结合型、家政型、无正式照护型四类。研究发现:学历、ADL受限个数、居住状况、性别、过去一年健康状况等因素对高龄老人居家照护服务利用影响显著。亟须根据高龄老人的服务需求类型,完善照护服务供给体系;推进医养结合服务,提升高龄老人居家照护服务精准匹配程度;促进无正式照护服务型老人的服务利用比例,改善高龄老人生存质量。
关键词:高龄老人; 居家照护服务 ; 优化策略 ; 潜在类别分析
一、引言
2020年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50%。”[1]2021年末我国65岁以上人口突破2亿,占14.2%,已经全面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随着高龄老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快速增加,高额的医疗费用和照护费用支出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国际相关研究得出的“接近死亡效应”在我国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由于高龄老人慢性病和残疾风险更高,其长期照护成本高且死亡前易产生高额医疗费用。”[2]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乃至健康高龄化,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健康长寿成为社会政策关注的终极目标。为此,《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各地根据财政承受能力,制定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对健康、失能、经济困难等不同老年人群体,分类提供养老保障、生活照护、康复照护、社会救助等适宜服务。”[3]当前我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加快老龄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与服务类别的供给,但福利政策的瞄准影响着福利效率,服务利用的分层尤其是城市高龄老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服务利用情况直接关切到老人的生存质量,是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的根本基础。
上海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超大城市之一。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16-2020年,上海户籍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60岁以上户籍老人由2016年的457.79万增长到533.49万人,老人人口占户籍总人口比重由31.6%增长到36.1%。预计到2025年,全市60岁及以上常住和户籍老年人口分别将超过680万和570万。”[4]人口老龄化、少子高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纯老化交织共存的复杂局面,将进一步加重养老服务尤其是高龄老人养老服务的负担。我国城市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整体需求水平较高,尤其是医疗护理和生活照护兼顾的医养结合服务、居家照护服务成为当前养老政策关注的核心和重点。完善居家照护服务,是上海乃至国家在快速老龄化背景下为应对“老有所养”基本服务需求做出的重大制度安排。在有限财政供给背景下,城市高龄老人群体服务利用呈现何种结构特征?对于哪些居家照护服务需求最为迫切?哪些因素会影响其服务利用?这些事关城市高龄老人养老服务质量的关键问题亟待回应。探究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完善深度老龄化时代我国城市高龄老人居家照护服务体系和政策架构,构建与城市高龄老人群体需求类别相匹配的居家照护服务,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上海围绕高龄老人的养老问题,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方案,从服务体系和制度保障方面进行了规范引导。早在2006年上海就出台了相应政策,将城市高龄无保障老人纳入社会保障。2009年7月,上海开展“探索建立本市老年护理保障制度综合研究”,形成了“1+8”调研报告。2013年7月,在基本医保制度框架下,在3个区6个街镇进行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点,2017年,由徐汇、普陀、金山三个区先行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18年,上海市在原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和区域长护险试点基础上在全市全面开展长护险试点,推动社区居家照护服务。2019年,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率先试行社区长期照护服务的精准化供给和老年认知障碍的早期筛查和服务干预。小步快走的渐进式政策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针对城市高龄老人的居家照护服务尤其是医疗护理方面的服务依然严重不足。“在老人居家医疗护理问题上,需要社区、机构等社会化、专业化的多层次照护服务体系予以支撑。”[5]
二、文献综述
(一)高龄老人照护服务需求:刚性及其风险
相关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而现有治理模式及制度安排仍缺乏结构化和系统性的反应与适应,相应治理研究亦遭遇困境。”[6]长期以来我国倾向于将高龄老人养老的社会责任交给家庭去承担,照护费用及人力基本由家庭内部解决。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年龄结构不均衡与代际递减下家庭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独生子女成家后很难对双方年迈失能的父母进行照护。“高收费且参差不齐的照护机构如何规范,家庭无力负担时如何应对等问题走向社会的视野。”[7]“对城镇老年人而言,社会养老不但弱化了子女对老人的精神慰藉,还挤出了子女对老人的经济供养。”[8]高龄老人数量和失能状况的增多对居家照护提出了客观需求。“其中真实老年抚养负担和抚养期望过高的风险,尤其是高龄老人的抚养需求超过社会和家庭对高龄老人的抚养服务能力,形成过高的抚养老年负担,影响人民生活、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提高,甚至危及社会稳定。”[9]“中国当代家庭形态的‘现代’趋向显著,但亲子关系中的‘传统’行为仍很浓厚。随着生育率降低、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家庭存世成员纵向延长,横向收窄,三代存世普遍,四代存世明显提高,在老年亲代存世时,赡养、照护义务不容忽视,亲情关照更不可缺少。”[10]“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课题组进行追踪调查所取得的高龄老人分性别需帮助比例数据,推算出“2050年中国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长期护理人数将比2020年增长7.5倍以上”[11]。沈可等研究发现:“养老金是低龄老人主要的生活来源,高龄老人仍高度依靠子女的转移支付。90岁以下老年人照护支出的年龄趋势与医疗费用类似,然而照护费用在90岁以上的高龄阶段有明显的翘尾趋势,高龄老人对生活照护的需求非常旺盛。”[12]随着人口高龄化趋势的不断凸显,少量已有的研究关注到我国城市高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基本生活缺乏保障,存在着高风险,面临着生存危机。
(二)高龄老人照护服务利用:遮蔽抑或满足
从整体上看,我国高龄老人的服务利用研究尚未得到学术界和政府应有的重视,大多数调研未能将高龄老人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不少全国性调查中对于高龄老人的关注笼统地涵盖在65岁以上老人的统计范畴中,很少有关于80岁以上老人的专项研究,关于这一群体的服务利用情况基本被遮蔽。”[13]部分研究注意到高龄老人的服务需求,张广利等基于生活质量的视角对城市高龄空巢老人社区照顾的研究,“发现其在日常生活照护、医疗陪护、生命安全以及精神慰藉等方面都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性。”[14]寿莉莉、朱即民对上海市高龄老人生活现状进行了多因素分析,认为:“高龄老人的养老应由政府经济供养、社会医疗保障、社区生活照护、亲人生活慰藉综合施策。”[15]张文娟、李书茁的研究表明:“代际支持对高龄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水平和心理状况影响显著,对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日常照护和经济支持进行。”[16]罗艳、丁建定基于2005~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随着福利社会化改革推进,服务利用分布对高收入老人更有优势。以补偿家庭照护资源不足为目标的政策则保护了低收入老年人的服务利用机会。”[17]郭瑜、张寅凯认为:“制度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对代际关系与养老预期变迁具有重要影响。养老保险逐渐成为中国城镇老年人经济独立的基石,协助达成当代老年人分而不离、重心下移的体谅式养老方式,也成为影响城镇老人服务利用的重要基础。”[18]与此同时,“中国的老龄社会治理发生在快速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城市化、人口流动和全球化过程中,包含如何构建一个整体性的老龄问题回应机制。”[19]对于城镇高龄老人居家照护服务利用的回应与满足,也是制度化、整体性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高龄老人照护服务选择:模式以及问题
社区居家照护服务模式在满足老年人医疗和养老需求,提升老年人的健康,降低社会养老负担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人口老龄化、非正式照护方式的失效以及疾病谱的变化,我国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的照护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家庭养老是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的具体体现。也是家庭内部个体之间出于不同的身份认同、利益需求和情感关系进行协商的结果。”[20]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在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三种模式中,社区居家养老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是一种更为理想的养老模式。[21][22][23]其中,社区医养结合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形势,强化居家养老服务的必然需求。在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互不衔接的现状下,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的多种合作,以家庭医生、社区日间照护中心和家庭病床为切入点,打通“医养”机构之间的双向转诊渠道,使其优势互补,提供约定式、互动式、跟踪监测式服务是解决老年人医疗和养老问题的最佳模式。[24]有学者经过精算和政策仿真,认为在社区医养结合的政策配套中,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具有可持续性和政策推广意义。[25][26]但当前我国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普遍遭遇建设资金不足、法律法规不健全、服务序列未形成、服务供给部门壁垒未打破、服务所需的人力资源匮乏,支付保障体系缺位等瓶颈问题,养老体制的结构性失衡突显,老年照护服务资源不足且效率不高。因此,追求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的整体效应,应先使医疗和养老充分分化并形成功能上的细致分工与有机耦合。[27]需要分层分类提高养老服务目标瞄准率,基于需求来构建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在需求-供给框架下实现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的精细化管理与无缝隙服务,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推动社会办医疗机构参与家庭病床服务。[28][29][30]“在养老服务提供过程中,要坚持老年人的需求导向,严格按照精准分析得到的需求结果主动为老人对接服务。”[31]
(四)高龄老人照护服务评估:特征及其影响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老年人照护需求满足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刘婕等对上海市同批居家高龄失能老人的健康状况、家庭照顾状况、家庭和社会支持情况等进行跟踪分析后发现:“同批高龄失能老人呈现生活自理能力变差、生活需要协助完成需求加大、经济供给能力减弱、家庭和社会关系趋于一般、社会支持能力较弱、亲属照顾者照顾压力增加等新特点。”[32]白晨、顾昕考察了高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病残趋势、健康不平等以及社会养老保障与服务在改善老龄健康上的政策效果。“高龄老人长期‘带残生存’的问题不容忽视,自理能力与认知功能受损对总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突出。女性、低收入等弱势群体更容易陷入长期多维健康贫困,医疗服务可及性与社区养老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长期多维健康贫困的发生风险。”[33]袁笛、陈滔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调查(CLHLS)个人和社区数据,采用多层模型探索收入、非正式和正式照护资源对老人长期照护需求和需求满足的影响,研究发现“低收入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较高、满足程度较低;非正式、正式照护资源供给能够降低老人长期照护需求,改善老人需求满足状况;正式照护资源中养老资源的增加能够缓解低收入对照护需求满足的负面影响,缩小不同收入老人需求满足差距”[34]。纪竞垚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中国居家老年人家庭-社会照护模型,认为:“精准匹配社会照护资源需考虑老年人主观能动性及健康状况、照护类型、家庭经济资源禀赋等微观因素,宏观层面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照护政策等作用于个体行为时,需结合城乡发展实际并注重供求对接。”[35]
以往研究丰富了学界对于高龄老人服务利用的认知,为完善高龄老人居家照护服务提供了依据,但也存在着对高龄老人居家照护服务利用与精准供给之间的拓展研究空间。比如,现有研究未充分展现正式照护服务类别及其潜在利用情况,对高龄化背景下中国老人居家照护及服务利用绩效的考察仍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在研究焦点上,重“制度”轻“服务”的情况比较普遍,已有文献多聚焦高龄老人服务利用的制度建设,关注高龄老人本身及其服务内容的研究(特别是社区居家照护服务)还不多。“事实上,相比于不断完善提升的长期护理保障制度,能否提供充足可及的正式居家照护服务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往往更加直接且重要。”[36]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对服务利用的度量普遍关注老人的社会学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忽视了高龄老人实际服务利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既不能完整展现高龄老人居家照护服务利用的真实情况,又容易掩盖生理、心理及认知各维度在正式与非正式照护服务利用之间的“替代或遮蔽效应”。综上所述,以往对高龄老人居家照护服务的研究,较少涉及老人服务利用类别的真实情况,对高龄老人居家照护服务的潜在类别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