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兴办慈善五大动因
作者: 罗一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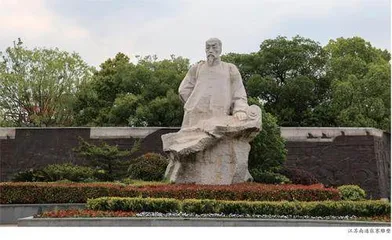
张謇生平成就三件传世嘉业:实业、教育、慈善。他说:“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时,惟赖慈善。”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曾称赞张謇是“爱国企业家典范”,并到南通博物苑张謇故居陈列室参观,考察了解张謇创办实业、发展教育、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称赞张謇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
家风和传统文化的传承
张謇出生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农耕世家,张家几代人都讲仁义,做善事。张謇的祖父张朝彦,年少时走过一段弯路,被不良亲友诱赌,输光了家产。后来浪子回头,重振家业,并乐善好施,被乡邻称为“真好人”。他对曾接济过张家一斗米的李老太始终感恩,李老太的儿子离世后,他担负起了赡养的义务,“饷斗米终其身”。
张謇的父亲张彭年,继承了祖父的秉性,作为张家第一个能读书识字的人,对儒家“仁爱济人”的理念认知更为自觉。有一年,家乡海门大旱且有蝗灾,稻米奇缺、奇贵,家人“剥蚕豆和麦屑而食”。家门面临大路,常有人来讨饭。张彭年和妻子只吃半饱,以省下食物救济他人,并表示“救一人是一人,救一刻是一刻。”他还训导张謇兄弟:你们知道挨饿的滋味吗?我半饱时还要把饭给别人吃,子孙但有饭吃,不可吝啬。当江南各州县被太平军攻陷,来海门避难的人很多,张彭年对有求者“必周恤之”。这些都给童年的张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张謇的母亲临终前的遗言便是“有钱,以偿夙负,振贫乏”。
可以说,家风熏陶和家长的言传身教,洗涤了张謇幼小的心灵,养成了他慈悲为怀的品性,奠定了他兴办慈善的初心宏愿。
张謇自幼便开始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除了家风家教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家风家教的灵魂),是促使张謇终生奔波在慈善之路上的基本动因。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轴,儒学思想以“仁”为核心,“仁者爱人”则是“仁”的精义所在。作为深谙儒学经典大义的一代大儒,张謇必然会对儒家以“仁爱”为根基的慈善思想心领神会,身体力行。张謇的慈善思想和作为,出自他的悲天怜人和宅心仁厚的高尚情怀,最终则来源于儒家的博大精深的仁爱思想。他非常信奉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他看来,要体现“恻隐之心”的“仁”,就必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必须“爱人”,“视天下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之溺犹己溺”。而要“爱人”,必须济人;要济人,则必须付诸慈善。因此,他搞慈善已不是为了一般的做好人、行善事,而是出于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内在追求。做善事,不图名,不图利,不图回报,只图心安理得,“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他坦言:“慈善事业,迷信者谓其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
中华文化博大深广,丰富多彩,除了儒家以外,佛教和道教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流。张謇的慈善思想,也从佛教、道教中汲取了不少营养。他认为,佛教主张慈悲度世,布施助人,道家讲究超然物外,修己利世,均可看作是中国慈善思想的源头活水。他明确指出:“若因果报应,道家之求长生者,须积善之功,周人之急,济人之穷;释家云,布施为第一波罗蜜。”
除了直接传承于传统文化,张謇的慈善动因,很大程度上,还来自受传统文化浸润的绅士和平民的慈行善举的激励。
绅士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经济和文化均欠发达的小农村落中,依靠科举功名和知书识礼,获得身份认可和族群尊重,成为地方精英和民间领袖。他们对上可向官方转达民情民意,对下可向民众传达官方的意图和规训,并兴办最基层的治理和建设事宜。他们是在正式的封建行政机构仅设到县一级的情况下,官方非正式在乡村治理的代理人。有学者指出,乡村绅士的职责主要有八类:一为慈善组织和民间团体筹款;二调解纠纷;三组织和指挥地方团练;四为公共工程筹款并主持其事;五充当政府与民间的中介;六为官府筹款;七维护儒学道统;八济贫。实际上,这包含了狭义的和广义的各种慈善公益事项。正因如此,绅士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慈善事业的带头人和主导力量。
为了践行儒学理念和赢得民众敬重,绅士们不遗余力地推行慈善事业。他们平时“经营乡里”,力促助益民生,灾荒年则开仓赈灾,恤贫济困。前不久,笔者走访了费孝通、陆定一等名人故里,发现苏南的绅士家庭都具有建“义仓”、办学堂的传统。并在乡规民约和家谱家训中,着重强调仁爱慈善思想。张謇的家乡亦是如此。南通如皋的沙元炳,是张謇的同科进士和事业伙伴,沙家是如皋的首富,“救灾歉,恤贫困,除强暴,扶孤幼,凡有益民生之事,无不力为倡导。”
对绅士们造就的传统慈善之风的耳濡目染,以及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担当,促使张謇坚定不移地跋涉在既艰辛又光荣的慈善道路上。正如他自己所说:“兹事具地方慈善事业性质,邦人君子当并不忍听其绝。”
传统文化的感召力、渗透力特别强。不仅社会精英绅士阶层深受其影响并竭力予以传承,就连普通平民乃至贫贱之民,也会自觉不自觉的奉行传统文化中的慈善观念。在神州大地时时处处涌现出的“凡人善举”,构成了中华慈善的又一绚丽景观。张謇最为推崇的平民慈善家,就是最终被清政府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的“千古奇丐”武训。
武训因自己不识字受财主的欺辱,发誓要让贫苦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读书,便以乞讨为生,逐渐积累起钱财,办了多所私塾学堂,使许多穷人家孩子读书识字。用张謇的话说,就是“幕天席地,四大皆空,是真丝毫无所凭藉,然一意振兴教育,日积所乞之钱,竟能集成巨资,创立学塾数所”。张謇最佩服武训的就是“以强毅之力行其志”和深广的慈善博爱之心。张謇从中获得了许多启发和激励。
西方慈善理念的吸纳
张謇虽是由传统文化哺育的一代儒生,但为了使国家尽早富强繁荣,他对西方文明的各种可取之处都努力学习借鉴。对于为何搞慈善,如何搞慈善,他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亦从西方慈善理念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成分。
统观张謇兴办慈善的历程,可以看出,他在1884年结束幕僚生涯,回乡备考和“经营乡里”时,就做了一些收野尸、赈灾民的善事。后来,又在1904年后创办了南通育婴堂等慈善项目,但真正大规模兴办具有现代意义的慈善机构,如养老院、栖流所、戒毒所、济良所、贫民工场、育哑学校等,却是在1912年以后。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与一位西方人的劝导和刺激有关。
这位西方人就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被清廷赐予头品顶戴)。他是一位在中国生活多年、在中外均有重要影响的“中国通”。他认为,中国文化未来的出路在于综合融会古今中外文化可取之处,建立一个兼容并包、广泛吸取和专精一学、触类旁通的新学。
1912年4月,李提摩太在与张謇攀谈时,提出了一个鲜明而尖锐的观点:“中国非真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此比练海陆军为强。究竟能有几省能行否?”这番话使张謇既振聋发聩,又羞愧难当。他当即表示,目前在全国普及尚难,但个别地方可以作些尝试。李则说:“有两三处做模范即善”。于是,张謇暗下决心,要在地方自治(包括慈善事业)方面做“模范”,为中国人争口气。
张謇在与李提摩太攀谈后的第二天,便写下了《感言之设计》,在南通原有基础之上,全面规划设计实业、公共卫生、普及教育、慈善四件大事。关于慈善的设计是:“推广慈善则育婴堂除幼稚园之增设自任外,须增建初等小学五所,平屋二十五间,连具须七千圆。小平工厂七间,连具需须三千圆。改建宿舍楼五十一幢,连具须二万圆。养老院连工厂器具须一万五千圆。残废院年工厂须一万五千圆。育哑学校须一万五千圆。贫民工厂须三万圆。妇女工厂须一万圆。合计十一万五千圆,核银七万七千七百两。”另外,他对已办或将办的慈善机构,都仿效西方模式,改进管理制度和方法,促其转型升级。
西方慈善理念的影响,也促使张謇将中国古代传统认知与西方近代观念相融合,从而进一步认识慈善的重要意义,并增强自觉推进慈善事业的动力。他认为,“老幼孤独不得所,大乱之道也。墨家者流以养三老五更为兼爱,孔子志安老,孟子申之”,“慈善与国家社会之说之通于政,近世欧美人之言也。比年耶教会设安老院于上海,安老云者,犹孔子意”。在这里,张謇将孔孟之道与西方近代理念相比照,说明两者都以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高度看待慈善,都应予以重视和践行。
其实,早在此之前,张謇就留意于西方的慈善作为。他在1903年出游日本时,便考察了若干具有西方色彩的慈善机构。看了盲哑学校后,感到“使人油然生恺恻慈祥之感”。回国后,便向地方政府建议兴办盲哑学堂。1904年,他重建南通育婴堂时,也是受到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主办的汇育育婴堂的启发,并相应地移植了他们的一整套制度和方法。“复与同人力去普通婴堂腐败之陋习,参用徐家汇教会之良法,开办一载,活婴千余,成效昭然。”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尝试。1912年以后,南通才出现了全面兴办融中外文明为一炉的近代慈善事业的高潮。
1914年12月,张謇为南通医学院题写校训:“祈通中西,以宏慈善。”这既表达了他对中西医结合培育医学人才的殷切期望,又反映了他融合中西文化理念兴办慈善的基本思路。
构建“新新世界”的需求
张謇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求者、开拓者、示范者,他所有的作为,都是为了构建一个“新新世界”,使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而他所有的事业追求,都是围绕构建“新新世界”的需要而展开。慈善事业亦是如此。
具有世界眼光和进步文明观的张謇,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看作是“文明村落”,他的“新新世界”的理想,就是也要把中国建成与先进国家比肩的“文明村落”,“此或不辱我中国之志”。而慈善,在张謇看来,则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不行现代慈善,就无法迈进现代国家的门槛。因此,必须大兴文明之风,大办慈善事业,大力促进全社会的文明转型。在这里,张謇已经把慈善的地位与作用,提升到促进文明,改良社会,乃至救亡强国的高度来认识。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才会对兴办慈善有无比的自觉和执着。
张謇关于构建“新新世界”的设想,首先付诸南通的地方自治。他认为实业、教育、慈善是地方自治的三根主要支柱,缺一不可。其中,实业是根本基础,教育是积极充实,慈善是必要补充。“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于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唯赖慈善。”在张謇看来,慈善虽然仅处于后列的辅助补充地位,但对于构建一个完整的文明社会,却是必不可少的。“王政不得行,于是慈善家言补之,于是国家社会之义补之。”就社会结构和社会分配而言,如果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不能以慈善的途径予以关照,社会成员就不能共享社会财富,社会就有很多缺憾,就无法构成真正的文明社会。同时,还会引起社会动乱,“老幼孤独不得所,大乱之道也。”正因张謇把慈善看作是地方自治和构建“新新世界”之必需和必然,他才会用毕生的精力和财力兴办慈善事业。
在张謇的心目中,“新新世界”是一个社会和谐、人民安康的世界。但他所处的时代,恰恰贫富悬殊,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他认为,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靠慈善。他为当时社会病症开出的药方是“安富”、“振穷”、“恤贫”。
所谓“安富”,就是为实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让企业家安心经营,让富人安心赚钱。所谓“振穷”,就是依靠经济发展,振兴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所谓“恤贫”,就是利用民间慈善和国家抚恤,使没有能力工作挣钱的贫民,也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张謇主张,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对正常人“广设生计”,“皆有所效以资其生”;对残疾人“亦有所安以恤其苦。”这样就可以“调剂贫富”,“根除社会上之不平等”。他衷心希望并大声呼吁“将来国家若能明定法令,使富人帮助穷人,则尽善矣”。
为了实现人人各尽所能、各有所安的和谐社会,从而建成现代化的“新新世界”,张謇主张慈善也应由传统走向现代。他认为传统的慈善救助偏重物质上的帮济与扶助,突出以“养”为主,而从构建“新新世界”出发,传统慈善应顺应时代潮流,实现跨越式转型,实施物质和精神救济扶助并重,“养”与“教”相结合。因此,张謇后来在创办慈善项目时,竭力践行“教养并重”的理念。一方面对贫弱残缺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一方面对其进行知识传授和技能培训,并着力培养他们成为心灵健康、人格健全的正常人。他特别强调“救济之行的目的,即在促其自新,扶其自立,俾由被救而达于自救,故礼义廉耻之诱导,职业技能之训练,较之衣食住所之供给,关系尤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