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萌芽与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潮
作者: 刘学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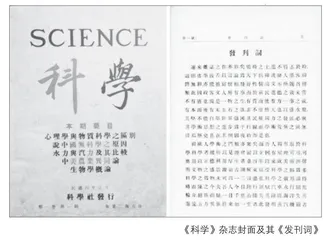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同中国科技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从近百年中国思想启蒙运动来看,新文化运动以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向封建旧文化宣战,更是在中国思想界高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这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科学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在中国得到空前的普及和推崇。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正是萌芽于五四时期科学思潮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早期共产党人大多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都接触和学习过西方科学技术,他们在文化意义和哲学高度上对科学及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的思考,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萌芽,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也对近现代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科学救国”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
中华文明历史上下五千年,以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为标志的“四大发明”,见证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可以说,15世纪之前,中国在科技上的发展水平曾领先于西方。正如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所说:“我们必须记住,在中世纪时代,中国在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内,从制图学到化学炸药都遥遥领先于西方。从我们的文明开始,到哥伦布时代,中国科学技术常常为欧洲人望尘莫及。”
明末清初,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通过传教士零星传入中国,但被统治者视为“奇技淫巧”。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中国被迫接受西方坚船利炮和欧风美雨的无情冲击,开始了吸收接纳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历程。“科学救国”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股经久不衰的社会思潮,其基本要旨就是通过提倡、研究和发展科学技术以实现救亡图存和强国富国的目的。
20世纪初期的中国,虽然有了机器、轮船、枪炮甚至是有线电报和无线电台,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并未在中国大地生根,中国科技水平远落后于西方。
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大力进行民主与科学启蒙,带头反思近代中国一系列民主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们意识到,无论是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无力进行一场广泛的科技革命,更无力发动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
科学是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之一,与民主并重。作为新文化运动兴起标志之一的便是以“科学”冠名的《科学》杂志的出现。1915年1月,留美学子任鸿隽、杨铨、胡明复、赵元任等人鉴于“科学在现今世界的重要,与我国科学的不发达现状”,创办了我国最早的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其《发刊词》中全面论述了科学在增进物质文明、破除愚昧迷信、增强人类健康和提高道德修养等方面的社会功能。由此,《科学》杂志正式举起科学的旗帜,并将其作为价值信仰的对象,科学主义思潮逐渐发展开来,开创了在中国传播科学的新时代。
早期共产党人高举起科学大旗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正是在深刻领会科学的实用价值及广泛意义之后,才倡导将科学与民主并列为新文化运动两面大旗的。陈独秀虽然一开始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但自1898年进入新式学堂杭州求是书院后,在这里学习了天文学、地理学和造船学知识,逐渐接触到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形成了唯物主义科学观。
1915年夏,陈独秀着手筹办《青年杂志》。同年9月15日,《青年杂志》正式出版,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在创刊号上,陈独秀用饱蘸革命热情的笔墨写出《敬告青年》一文,鼓励青年冲破思想牢笼,积极宣传民主与科学,号召青年要做“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一代新青年。他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样,《青年杂志》一创刊,就高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一年后,《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追求科学、崇尚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和价值评介。陈独秀在《随感录》中写道:“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他认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在他看来,科学和民主都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将来的一切思想行为,“必以科学为正轨”,“人类将来之进步,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
李大钊早年在永平府中学堂读书时,除学习经学外,还学习了外语、历史、地理、博物、物理、化学等课程,初步打下自然和理化知识方面的基础。1913年至1916年,他留学日本,系统学习和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包括近代自然科学。他认为科学与人类社会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盖人类之智慧无涯,斯宇宙之利源未尽,重要以科学的精神求索真理,必然能够使人类早日登于文明幸福之境”。他认为,科技的发展进步对人类影响十分深刻,“印刷术、火药、罗盘针三大发明,是古人所不知道的。这些发明变更了全世界的情形,先文字,次战争,最后航海,引起了无数的变迁,影响及于人事,没有比这些机械的发明再大的”。李大钊接受西方科技知识与科学思想后,产生了强烈的革新意识并较早在中国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呐喊声中,科学启蒙成为五四时期的一股强烈的社会思潮。各类科学团体相继建立,科学期刊大量发行,科学在社会上日益受到关注,学习和研究科学的风气也逐步形成,科学救国思想在社会上流行一时。有人统计,五四时期有79种杂志以“科学”字眼命名,而卷入这场宣传科学潮流中的报刊有400种以上。仅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统计的162种报刊中,刊载了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评论、介绍、通讯、科学史和专著等文章就有660篇。如果加上科学专刊,五四时期发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不下千篇。其中著名的除《新青年》外,还有 《新潮》 《少年中国》 《曙光》等。不少知识分子把科学不仅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而且作为一个价值体系来接受。创刊于1919年1月1日的《新潮》杂志,主张“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而“为未来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同年7月1日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也确定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1920年1月1日,该会发行的《少年世界》进一步规定科学的价值,认为要“本科学的精神”,去“草拟一个具体的改造中国的方案”。这些刊物所宣传的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研究,但更重要的是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早期共产党人的科学素养
五四时期提倡科学、弘扬科学精神,成为一股波澜壮阔的社会思潮,从而促使国人在思维方式、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上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它不仅震撼和冲击了封建迷信观念和儒家伦理传统,更是支撑起以民主和争取个性解放为内涵的新文化价值体系,促进了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毛泽东、李达、周恩来等,他们的青年时代正处于近代西方科技思想在中国引发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年轻时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接触和学习过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初步形成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这为他们日后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通过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和亚当·斯密的《原富》等反映18世纪、19世纪西方科学技术成就和民主主义思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西方科技著作,完成了其现代科技思想的启蒙。
出国留学在当时成为共产党人接受系统科技教育的重要渠道。周恩来在1922年8月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发达实业之大计在此,由此乃能使产业集中,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而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他还阐明,资本主义的危害“不在他利用科学,乃在他闭塞工人的知识”,革命成功后,工人阶级的政府要重用“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学术”。
还有很多早期共产党人学习过科学知识,有着深厚的科学素养,甚至抱有“科学救国”的梦想,后来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比如,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李达留学日本时学习理科,恽代英、刘少奇和张闻天等都有过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经历。
老一辈革命家徐特立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他的求学历程和教育实践中与自然科学结下过不解之缘。他年轻时通过刻苦自学,掌握了数理化基本知识。五四运动后,42岁的徐特立毅然决定赴欧洲勤工俭学,研习自然科学。1921年,他考入巴黎大学,潜心攻读了2年的数理化课程。之后,他又去比利时待了半年,赴德国待了4个月,攻读天文学、生物学等课程。他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有较高造诣,而且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国后,徐特立参加了革命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自然科学教育方面作出卓越贡献,延安时期曾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他主张教育、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建设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培养了几代科学技术人才,并建立了初步的系统的科学技术教育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邓小平、李达、聂荣臻、李富春、徐特立、刘鼎等都在青年时代远涉重洋,追求真理,培养了良好的现代科技素质。实际上,许多早期共产党人都有过“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后来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转向革命救国的方向。但对科学的尊重、对科学精神的汲取仍是他们思想意识中的一种底色。据统计,到1922年7月,中共党员共195人,在海外学习的有23人,其中留俄8人、留日4人、留法2人、留德8人、留美1人。到1923年6月,旅欧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已达80余人。这些留学海外的党、团员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代科技文化的熏陶。以上这些早期共产党人的经历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崇尚科学的光荣传统。从党的诞生之日起,始终高举科学的旗帜,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也无不诉诸科学的名义。
五四时期汹涌澎湃的民主与科学思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重要思想前提。早期共产党人大力宣传科学,其中包含着对科学知识、科学研究及物质文明的提倡,但更主要的是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科技思想也随之传入中国。最早译成中文的马恩原著是《共产党宣言》序言(即《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由民鸣译,1908年发表在日本《天义》报上。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此外,《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经典》《自然辩证法》,以及含有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这一著名论断的《卡尔·马克思的葬礼》等译著陆续出版。这些译著中包含较多关于科学技术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肇始,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主要的思想渊源。
“科玄论战”与新科学观
五四运动后,1923年,中国思想理论界发生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史称“科玄论战”。从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来看,“科玄论战”的发生不是偶然,实际上是东西方思想大碰撞的延续。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则认为,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这场论战其实是一场文化保守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之争。到论战后期,早期共产党人参加了这场论战。1923年11月前后,陈独秀发表《〈科学与人生观〉序》《答适之》,瞿秋白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现代文明的问题与共产主义》等文章。他们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论述了科学与人生观、自由与必然、科学与社会革命等之间的关系,对论战产生的根源及实质进行了总体分析与评价,体现了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
在“科玄论战”中,陈独秀、瞿秋白等用马克思唯物史观对玄学派与科学派的观点进行分析,从而形成了论战的第三方。瞿秋白在论述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时指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但同时,他对唯科学主义也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认为,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但不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间,陈独秀也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像物质世界一样,精神世界也是有客观规律并且这个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像自然科学一样,对精神世界的认识也是渐进的或曰逐步完成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即社会科学对精神领域的认识也是逐步的和发展的;社会科学就是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实证、形式逻辑等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并正确把握其规律,当然也就能够正确认识人生观。他认为:“其实我们对于未发现的物质固然可以存疑,而对于超物质而独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质的什么心(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什么神灵与上帝,我们已无可存疑了。”他还强调:“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早期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提高了论战的层次和水平。在这场论战中,陈独秀、瞿秋白等大力宣传唯物史观,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阐述了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新科学观,为人们确立真正科学的新世界观、新人生观指明了方向。他们站在唯物主义高度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和发展规律作出的精辟分析,为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17JJD77014),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