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转战湘南的艰辛历程看朱德的卓越品质
作者: 余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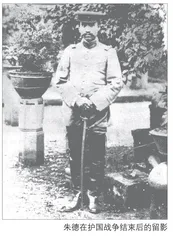
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失败后,朱德在广东饶平县茂芝全德学校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史称茂芝会议),作出“部队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为起义军余部指明前进方向,开启了转战湘南的序幕。在陈毅、王尔琢等人协助下,他先后开展“赣南三整”、统战范石生、“粤北练兵”,初步解决了军队改造、战略战术转变、物资补给等棘手难题,凝聚了军心,提升了士气,保存了革命火种。这场艰辛的转战,极大地考验、锻炼了朱德,彰显了他在危难关头的卓越品质。
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南昌起义主力失败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前途顿显黯然,悲观情绪弥漫余部,彷徨者、逃跑者、叛变者比比皆是。对革命逆境的态度和作为,成为考验革命者信念坚定与否的试金石。朱德作为指挥官,始终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在茂芝会议上誓言要把余部带出敌人的包围圈。
在赣南安远县天心圩,部队由茂芝会议时的2000余人锐减到七八百人,正处于军心不稳、士气低落、濒于瓦解的危险时刻,他召集军人大会,斩钉截铁地表示:“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只要有十支八支枪,我还是要革命的!”并鼓励众人说:“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接着,他指出:“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火热赤诚,鼓舞了部队的斗志,使部队将士在黑暗和绝望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在困难中认清了方向,增强了信心。
在赣南崇义县上堡,他满怀信心。1927年11月初,他率领起义军余部在崇义县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开展军事整训。这一带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的防区。杨如轩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期的同学,是他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时的老部下,二人既有同窗之谊又有战友之情。于是,朱德给杨如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希望杨如轩把上犹县借给他练兵3个月,并表示,“练一团人,就可以活捉蒋介石”。
杨如轩接到信后,虽未给出正面回答,但也没有派兵前去骚扰,实际上默许了朱德借地练兵的事实,但他对朱德“活捉蒋介石”的目标却不以为然。揆诸史实不难发现:彼时,朱德所部只有七八百人,国民党军光是杨如轩这一个师就可以将他们就地围困乃至消灭,更何况蒋介石的背后还有上百万的国民党军队。朱德要援兵没援兵,要补给没补给,要根据地没根据地,说出这番豪言壮语正是源于他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信仰如磐的初心力量!
朱德的坚定信念,不仅体现在以上方面,还体现在他对范石生思想言行的影响上。上堡军事整训后,鉴于起义军物资和装备供应十分困难,同时为隐蔽目标、积蓄力量,朱德与陈毅、王尔琢商量,并经党组织讨论通过,决定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的范石生合作,结成反蒋统一战线。
合作期间,朱德不时与范石生讲述中国革命前途等问题,使其在言行上发生转变。比如,范石生过去说到孙中山都叫“孙大炮”,现在则称孙先生;过去缄口不言的“赤化”二字,此后却常常挂在嘴边。他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后,还推荐给下属阅读,并强调“马克思的学问很高深,辩证法更不易懂,你们青年人脑子灵活,细细琢磨会懂的”。
范石生在与朱德合作前后,思想言行上表现出的这种反差,表明其受朱德影响之大之深。合作前,范石生在给朱德的信中写道:“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途不可量矣!”此言虽含有较为正面的期望,但也相当模糊。可是在合作被迫结束、朱德率部离开之际,范石生则去信表示:“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直言共产党能够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并赠送给朱德所部上万银元。
从天心圩的演讲,到与国民党军中两位同学的通信乃至合作,朱德以坚定的信念影响着身边的人,改变着合作对象,不仅挽救了革命火种,也影响和感染了对手。
无限忠诚的坚强党性
什么是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那么在这场艰辛的转战中,朱德无限忠诚的坚强党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他都时刻不忘党员的政治身份,始终能够站在党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始终对党忠诚为党分忧,千方百计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守住了人民军队的“军魂”。
在茂芝会议上,面对余部在主力失败后孤立无援的险恶环境和解散部队的悲观主张,他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表示:“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危急关头,朱德首先想到的是党员身份,想到的是对党尽责、革命到底,展现出忠诚为党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
他在会上主持通过的4条意见中,第一条是“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以便取得上级指示”;第四条则强调:“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更要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自由离队拖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的严重事故发生。”这就是朱德,即使面临敌军5个师兵力的压境合围,他首先想到的仍是寻找党组织并获取指示,想到的是发挥党团员等的先锋作用,排除万难、安定军心,巩固党对军队的领导。
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其间,朱德也在赣南地区适时地对部队进行了各种整顿,为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进行了有益探索。
在天心圩,他开展思想整顿,统一认识,振奋革命精神,扭转了部队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在生死攸关、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把部队带出绝境,继续跟党走。
在大余(位于赣粤边境),他开展组织整顿,派陈毅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实行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加强党在部队基层的工作;选派优秀党员到连队担任指导员,加强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从而使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团结成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
在上堡,他又着手整顿纪律并进行军事整训,逐步消除了军队中残留的旧军队习气,严肃了军纪。
朱德在赣南的这些整顿,从思想、政治、组织、纪律等不同层面凝聚了军心、增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涵。正如萧克上将后来所言,这些整顿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意义是一样的,都在探索并实践建立新型的革命军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与范石生的合作中,朱德自始至终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组织的独立性。首先,在上堡酝酿合作时,他没有乾纲独断,而是主持全体党员会议,讨论制定合作前提:保证在原建制不变、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前提下与之合作。其次,在汝城与范部代表谈判时,他将上述前提作为合作条件,明确表示:“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照我们的决定办,不得干涉。”在双方最终达成的合作协议中,第一条就是对这些条件的确认,即“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
后来,起义军余部在驻防或行军时,照样打土豪、杀地主恶霸,范石生从来没有过问和制止。即便在汝城酝酿湘南暴动,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最后当蒋介石发现朱德藏身范部,要求范石生逮捕他时,范石生也不忘旧谊,及时通知他率部撤离。起义军余部没有受到阻击,实现了“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
从茂芝会议到武平战斗、“赣南三整”,再到与范部合作,起义军余部始终能够于沮丧彷徨中恢复信心、于挫折险阻中愈加奋起,于统战合作中保持独立、听党指挥,根本之处就在于其领导者朱德有着无限忠诚的坚强党性。
身先士卒的担当精神
在敌强我弱形势与悲观沮丧心境的交织作用下,起义军余部一旦遭遇不利作战环境,稍有不慎便会招致重大伤亡乃至全军覆灭。能不能冲破重重险关,关键就看指挥官能否敢于担当、发挥带头表率作用。当年,起义军余部之所以能够在进军湘南的过程中逢凶化吉、化险为夷,关键就在于朱德能够发挥领导干部冲在前、干在先的担当精神,哪里有困难有危险,他就在哪里发挥主心骨的作用。
石径岭战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茂芝会议后的第十天即1927年10月17日,起义军余部在武平县城外打了一场阻击战,然后被迫向西北方向转移到石径岭附近。石径岭位于闽赣边界地带,四周是悬崖峭壁,地形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行,却被反动民团占据。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起义军余部陷入走投无路的危险境地,一场仰攻硬仗似乎不可避免。危急关头,朱德一面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带领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峭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抢占了隘口,为起义军杀出一条血路。在他的指挥下,大家安全通过隘口,进入赣南山区,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
这一仗,朱德身先士卒,出奇制胜,使部队避免了强攻硬打,避免了重大伤亡甚至全军覆没的危险。对此,不妨与之前的武平战斗作对比。前面提到茂芝会议后,起义军余部曾在武平县城外与前来追击的国民党钱大钧部一个师发生激战。虽然最终击退敌军,但起义军余部伤亡惨重,由2500余人锐减至约1500人,战斗损失达1000人,是转移途中损失最大的一场战斗。对比之下不难洞见,面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石径岭,在后有武平驻军追击的情况下,这仅存的1500人要想强攻石径岭隘口,作战难度和惨烈程度极有可能超过武平战斗。从这个角度讲,石径岭战斗在整个“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转战中至关重要,正是朱德的身先士卒、勇敢担当,再一次挽救了革命火种。
当时年仅20岁的粟裕,参加了武平战斗并身受重伤,在战友的帮助下赶上部队,目睹了朱德在石径岭战斗中身先士卒的英勇一幕,受到很大鼓舞。半个世纪后,他仍记忆犹新:“经过这次石径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从长者到勇将的认知变化,是粟裕对朱德从外貌到内在的认知、认可过程。透过大家怀着胜利喜悦通过隘口的情形可知,粟裕的认知变化绝非孤例,而是朱德赢得起义军余部上下认可的一个缩影。
南昌起义军余部绝大部分来自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小部分来自前线战败撤下来的起义军和朱德任军长但人数实少的新组建的第九军。朱德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领导者,只是因为掩护主力南下作战需要,才受命担任临时指挥官的。他与部队将士彼此并不熟悉、在主力失败后人心涣散的情况下,最初领导起来也很困难。但是,枪林弹雨一路走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朱德都勇立潮头、冲锋在前,对大家相伴于危难,挽救于绝境。因此,他赢得了部队的信赖和崇敬。
除在石径岭为解决战斗危局而奋勇向前外,朱德在上堡整训时还曾为解决部队补给问题,奋不顾身、以身犯险前往汝城与范部谈判。在途经汝城县濠头圩时,朱德夜宿在一个祠堂里,不料半夜被土匪何其朗部包围。在土匪盘问身份时,朱德急中生智以伙夫身份骗过对方,土匪出门后他即从后窗跳出,脱离险境。朱德敢于担当、机智应对,最终与范部结成反蒋统一战线,为部队争取到充足补给和休整机会。如果说起义军余部因上堡借地练兵“才算稳住了脚”,那么正是在隐蔽范部的这段时间,才获得了补给和弹药,恢复了战斗力,渡过了补给告罄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同样,正是在这段休整时间,起义军余部养精蓄锐,巩固了“赣南三整”的系列成果,并在朱德的领导下初步实现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转变,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内打什么样的仗及怎样打仗等重大军事问题,为此后湘南起义的军事胜利奠定了基础。正如徐向前元帅后来所称赞的:“大浪淘沙卷万里,潮头难留几许人!他就是这‘几许人’中的一个。在茫茫雾海中,朱德同志不仅具有透视航向的超凡目光,而且具有破浪前进的巨大勇气。”
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湘南的艰辛历程,是起义军余部饱经磨难、重新振作并走向壮大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段革命最低沉、前途最渺茫、人心最浮动、个人最无助的艰辛转战探索中,朱德不仅经受住了革命风暴险滩的锻炼和考验,更以其坚定的信念、坚强的党性和勇敢的担当,几次挽救濒于瓦解、陷于危境的起义军余部,使之走出绝境、浴火重生,可谓居功至伟。此后,朱德先后担任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重要领导职务,与毛泽东等艰辛探索,率领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直至夺取中国革命胜利,成为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和举世闻名的军事统帅。
革命鲜有不经历重大挫折的,但越是艰险曲折,越能考验和锻炼革命者的政治品格和革命胆识。朱德领导的这段艰辛转战探索就是这样一段融挫折、惊险与人物品格、胆识及其互动较量于一体的生动历史,因而有值得后世反复学习、讨论、挖掘和传承的宝贵精神价值,虽时过境迁,亦历久弥新。
(作者系中共仪陇县委党校、四川张思德干部学院教师)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