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敌后抗战条件下的生产渡荒
作者: 陈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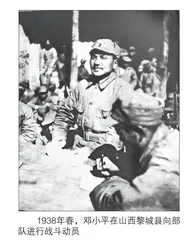
“华北各区因敌人破坏,战争影响,普遍灾荒及我们自己的生产工作很差,除山东之胶东、滨海及冀鲁豫一部分地区外,经济上都已接近枯竭点。”这是1943年12月3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的部分内容。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谈到,解放区“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从“普遍灾荒”“经济上都已接近枯竭点”,到解放区在应对严重灾荒中“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是历史性的转变。知史以明鉴,可以说,邓小平在这一克服严重困难过程中的思考和实践对当代中国仍具有宝贵的启示价值。
“局势愈紧张,我们愈要镇定,愈要掌握住政策”
1942年春,旱情初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就制订出助耕和开展生产的计划。根据地生产渡荒,最急需粮食,粮食遂成为敌我斗争的焦点。尤其是在敌我必争的华北,斗争日益残酷困难。仅在1942年春季“扫荡”中,日军就给华北根据地造成了严重侵害,太行区有6000余头牲口、近万石粮食被日军抢走。随着天灾加重,华北根据地当年小麦产量锐减。日军趁火打劫,10月份又实施“灌仓计划”,抢夺、摧毁根据地存粮,妄图瓦解八路军,达到其年内在华北囤粮7000万石的目的。①在敌人重重封锁、连番“扫荡”中生产救灾,成为我军的必由出路。邓小平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开展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②放弃对敌斗争,根据地建设无从谈起;停止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
1.发展生产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在分析八路军用简陋武器与强敌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何以能够创造持久抗战奇迹的原因时,邓小平写道:“也许为人们所忽视的,就是我们在敌后还是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正因为有了这一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六年之久,并且还能坚持下去。”③对于人们忽视经济战线与生产工作的问题,邓小平在1943年1月17日和蔡树藩、黄镇发布的《一二九师一九四三年生产工作训令》中批评了1942年生产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偏向:轻视农业生产,认为“出力多而赚钱少”;为图改善生活,而将政策法令置脑后于不顾,屡次走私粮食;生产成果须适当支配使用,反对浪费。提出1943年生产计划的基本方向是以农业为主,大力提倡农业生产,要订出生产标准和具体完成的措施以及生产节约的奖惩办法。6月21日,他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会议上,再次批评了忽视对敌经济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基本方针的倾向,强调务必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要把生产当作今后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为确保华北根据地生产工作的开展,会议作出《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8月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发布命令,对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形势,明确强调要把战胜灾荒作为1943年、特别是下半年的中心任务;命令各部队不仅要坚持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应加紧生产,厉行节约。12月1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北方局会议,再次明确指出,生产是明年(即1944年)的主要任务之一,必须组织、发动群众生产,才能改善生活。
2.明确“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成果,都是用血换来的”,还主张在战略上消耗敌人。“战略上是消耗敌人,消耗包括歼灭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不要损失自己的力量,打不必要的战斗,同时,一定要有顽强的战斗拼搏精神”④。1942年12月9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李达在关于反对敌人抢粮清乡对策的电报中提出:“‘扫荡’之敌无后续部队者,应找出其最薄弱之处突破冲击或从后背给以攻击。游击队要强化政治生活,严格纪律,结合民众,这样才能保存本身并发展游击战,否则将被日寇特务削弱、瓦解甚至被消灭。”要求干部适应敌强我弱条件下进行敌后斗争的特点,保持警觉。1943年7月14日,邓小平在作《内战危机面前的紧急动员》报告时指出:“我们对于陕甘宁边区的最好支援,是把我们敌后的每个阵地巩固好,把我们的根据地建设好,把我们的各种工作做好。局势愈紧张,我们愈要镇定,愈要掌握住政策,愈要防止‘左’、右的偏向发生。”认识上摆清消耗与消灭的关系,敌后根据地才能在坚持生产渡荒的斗争中,最大限度地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积蓄力量,最终在持久战中赢得对日军的胜利。
3.我们军队在技术上处于劣势,主要靠的是人的条件来弥补技术条件的不足。⑤邓小平用“窳劣”来描述八路军的武器,特别是在日军进行特种战争的严峻形势中,越发凸显了八路军武器的劣势。1943年6月9日,他和刘伯承、李达向中央军委的汇报中写道:“敌人为要捕捉统帅机关,经常不断地探测我每个无线电台机器声音、拍电手法、移动位置、如何改变呼号及波长。”“敌飞机经常扭住我军踪迹,连续飞行侦察,并速示指挥轰炸。”如何应对这样强大的敌人,他在之前1月26日代表太行分局作的《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报告中,总结的第一条经验即“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巧妙而尖锐,应切实注意加强下层,提高下级对敌斗争的能力”。太行区的灭蝗斗争,就生动体现了怎样以人的条件来弥补技术条件不足的抗争方法。蝗灾是华北抗日根据地遭受的自然灾害中最为严重的一种,蝗虫过后,庄稼、树枝、草叶顷刻被吃得精光。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群众灭蝗运动。由于灭蝗药物匮乏,邓小平提出组织军民人工灭蝗。军民使用的工具就地取材,有铁锹、扫帚、布袋等。据统计,太行区日均出动人数25万人次以上,总用工1000万个以上,人均约40天。统计的剿蝗成果为,10个县共刨卵、打蝻、打蝗1835万斤。⑥由于全区军民齐心协力灭蝗,使蝗虫造成的庄稼减产得到相当程度的降低。这次轰轰烈烈的剿蝗运动一直持续到1944年。当年夏季太行区获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丰收,收获小麦160万石,基本渡过了3年灾荒。
“减轻人民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
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⑦而能否减轻人民负担、增加人民福祉,反映在是否关心以及怎样关心人民利益上。1943年10月12日,在讨论宣传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时,邓小平指出,中央指示的重大意义是如何争取群众跟党走,这是贯穿于战后的问题,是同敌人争夺群众的问题,了解这一点,才会对十大政策积极执行。
政策制定后,干部是关键。邓小平曾提出:“管理问题很重要。会管理就会减少痛苦。干部以身作则作用大,主要是关心战士,个人模范,反对官僚主义。”⑧当年在太行区武委会任职的杨殿魁后来介绍根据地官兵一致的情形时说:“由于救灾,部队1943年的冬装到入冬才筹措到土布和棉花”,受限于困难条件,部队动员全体指战员把分发到的土布、棉花制成冬装,自做自穿,“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和大家一样穿的是深一片浅一片的灰土布棉衣”。
日军“扫荡”时大肆屠杀,无恶不作,根据地群众中出现了恐日心理。对此,邓小平提出要开展日本必败的宣传,增强赢得战争胜利的信心,“反对麻木,打击恐日病”。他还主张以做好青年工作来带动群众工作。地方武装、游击队是根据地民众就近的保卫者,要保证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对地方武装的管理要注意关系,避免正规军削弱游击队。通过武装抗争与抗日宣传相结合,缓解群众的恐日心理。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重重困难压迫下,机构庞杂造成的财政、物资供应负担与根据地民力条件的矛盾越发突出。邓小平在根据地机关、部队进行第一次精兵简政期间,主要从减轻人民负担方面强调了贯彻这一中央决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根据地的同胞比敌占区同胞的负担要轻得多。但是,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天灾人祸,生活也是困难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减轻人民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⑨1944年1月28日,邓小平就精兵情况,致电刘伯承、蔡树藩:1942年1月至4月底开展的第一次精兵,全军区共减少7487人,以当时每人每年1000元计(粮食在外),全年节省开支750万元。1943年3月至4月进行的第二次精兵,刘伯承和邓小平把重点放在进一步调整机构、整编机关、改进机关工作作风和提高工作效率上。配合部队精兵的党委、政府简政工作,到1943年8月,仅太行区县级以上政府工作人员就减少了80%,节省经费占比达38%。
邓小平主张,生产政策应奖励积蓄,“如果生产上鼓励人民积蓄,就能减轻人民负担”。晋冀鲁豫边区连续数年遭受日军的残酷封锁、掠夺,又经受多重自然灾害。亟待救济的灾民达35万人,大约占全区总人口的23%。还有从冀西、豫北和黄河以南国民党统治区逃过来的7万多难民需要安置。全区军民吃穿缺乏,部队、机关给养几乎无以为继,战士们常常衣食无着,饿着肚子与日伪军作战。面对艰困的局势,邓小平分析指出:“从整个形势来看,华北是熬时间,从长期着眼,积蓄力量,坚持斗争。实现这一方针,基本环节在于如何争取群众跟我们党走,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自己。”边区应当建立在人民保有积蓄的基础上,“不积蓄就经不起灾荒,更不能坚持长期斗争”。⑩由于发展生产中执行公私兼顾政策,允许一定比例的个人积蓄,对于扭转严重的生存困难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太行区有积蓄者一度达到9411人,积蓄总额167万余元;一年开垦荒地12万亩,其中个人开垦的小块荒地5728亩。⑪至1944年秋季,太行山遍地待收的庄稼呈现出走出数年灾荒的生机。
“要在政治上加强自己,不仅从意识上加强锻炼,而且要忠于职守,要了解各项政策,使军事与政治密切地结合起来”
日军实施远超出人民全部收入的人力、物力掠夺,造成沦陷区的连年歉收和严重灾荒。同时,又鼓动灾民到根据地抢粮,企图制造根据地与沦陷区严重对立的事端。邓小平指出:“敌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着的,是极其残暴的。”⑫侵略者对我实行的是总力战,我们对敌寇也必须进行一元化的斗争。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对此,邓小平强调要增强干部的能力。“要在政治上加强自己,不仅从意识上加强锻炼,而且要忠于职守,要了解各项政策,使军事与政治密切地结合起来”⑬。敌人掠夺沦陷区、游击区人民粮食,我们就组织、帮助人民采取包括武装抗争在内的多种方式回击日军的强盗行径;敌人要抓丁服劳役,我们就组织壮丁躲避奴役,并与群众联合打散集合起来的人丁。受严重旱灾、蝗灾、水灾等的影响,根据地灾民的生活比往常更为困苦,但是在边区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救济之下,依然保持着对自然灾害与侵略者顽强斗争的活力。邓小平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中写道:“我们的军队和政民干部,在灾荒严重的区域,成了生产的主力军,专员、县长、司令员、政治委员都亲率干部战士去帮助灾民种地,更给了灾民以很大鼓舞。”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关于反“扫荡”时免遭敌袭的对策中写道:“如必在敌占区或接敌区工作不好之地宿营时,则以村中有力之人员作抵押,担保不加害于我,但必须以礼貌待之,特别从政治上说服,教之以欺骗敌人的两面政策。”⑭应当说,利用有力之人员掩护我军包括游击队的隐蔽行动是在特殊形势下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具体方面。为持续开展政治攻势,争夺思想阵地,1943年2月28日,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发布《一九四三年敌伪工作方针》,要求每个县掌握一个伪军中队,并在其中建立党的支部。对国民党军队采取必要的缓和措施与权宜之计,是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又一方面。1944年10月,为方便冬季整军与生息民力,第一二九师释放阎锡山部俘虏200人,提议只要国民党第六十一军不联日反共,我愿谅解,各守原防,互不侵犯。
坚持正确推行减租减息政策。针对实施减租清债政策时,对地主打击过重,甚至由打击地主变为冲击富农的不良风气,邓小平强调区分和把握削弱封建与消灭封建的政策界限。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生活是一方面,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有条件维持生活,是政策不可偏废的另一方面。侮辱地主人格的斗争手段,有损于党的领导,既妨碍团结地主抗日,也妨碍争取落后群众对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参与。邓小平强调党的指导作用的正确发挥,有效防止了群众发动起来后出现的自流性。他指出,开展统战工作“应当抓住一批地方士绅,进一步开展伪军工作。对国民党不过分刺激,我们的态度不是骂它,而是希望它进步,强调团结”,坚持抗战。⑮应对敌后灾荒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斗争,有各阶层人民的积极参加,才能够有所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