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作者: 陈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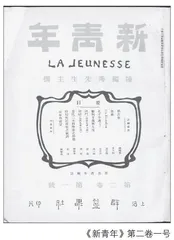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和共产国际援助等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其中,革命杂志《新青年》功不可没。
《新青年》引发的新文化运动解放了时人的思想意识,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1920年9月后,它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阵地,为党的光辉伟业写下红色序章,更为党的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四运动前的《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其时,辛亥革命给国人带来的短暂希望已经幻灭,陈独秀在《新青年》中高举民主、科学旗帜,号召国人向法国革命学习,揭开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新青年》的启蒙策略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启蒙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然而,由于中西文化对比的办刊策略未引起国人注意,《新青年》最初的发行量很少。鲁迅在1918年曾致函许寿裳,指出“《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直到《新青年》举起“批孔”大旗,青年学生才开始关注和追捧这份杂志。
1917年初,《新青年》随陈独秀来到北京。在北京,该刊举起“文学革命”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人们的思想由此得到极大解放,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回忆《新青年》对其影响时指出:“《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①可以说,如果没有《新青年》的启蒙,就不会有后来的五四运动,更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只是《新青年》虽肩负着启蒙使命,办刊方针却依然坚持“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片面强调反封建思想的宣传,对举国关心的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②
随着十月革命爆发,中国思想界发生巨变。正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③俄国革命的胜利,深深触动了《新青年》的编辑们,让他们看到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办刊方针遂发生重要变化。1918年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打破不议时政的陈规,公开批判自己原来的主张,提出对于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问题,不能“装聋作哑”。此后,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出现在《新青年》上,如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但与其时的无政府主义相比,数量和影响力均不占优势,直到五四运动的爆发才改变了这种局面。
五四运动之后的《新青年》
(一)从思想和理论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基础
科学社会主义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传入中国。1899年英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首次提到马克思及马克思的学说,此后,有不少中文书刊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介绍,但均未产生大的影响,也没有为时人所重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大体与五四运动同步,其标志是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即第6卷5号)。“专号”上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刘秉麟的《马克思主义传略》和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等,还刊载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时蔚为壮观。在众多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中,《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无疑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有助于国内进步知识分子理解马克思主义,被誉为“我国第一篇完整地、系统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历史文献”。④由此,各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上海的《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和广东《中华新报》等进步报刊随后跟进,马克思主义在神州大地迅速传播开来。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社会主义,《新青年》的办报方针随之作出调整。1919年12月中旬,《新青年》刊发《本志宣言》,称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造成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主张民众运动、社会改造,还提出要尊重劳动,打破经济上的旧思想等新观念。此后,《新青年》加强对军阀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抨击、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和俄国苏维埃政权表现出明显的同情。
从1920年2月起,陈独秀同李大钊开始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其时他的目光已由以青年学生为主转向以工农大众为主。同年5月1日,《新青年》第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在上海问世。该期全文刊登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及中国舆论界的反映,指明只有社会主义苏俄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中国,援助中国人民。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新的有力推动。对此,蔡和森指出,《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不过在过渡期间的文章,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了,杜威派的实验主义也是有的”,要到1920年《新青年》五一劳动节特刊“才完全把美国思想派赶跑了”。⑤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共上海发起组)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宣布成立,并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从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自第8卷1号始,《新青年》设立“俄罗斯研究”专栏,登载列宁著作、苏俄革命以及国际共运方面的情况。先后用6期“俄罗斯研究”来系统地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内容包括国家学说、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等。由于《新青年》的示范带头作用,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广东的《群报》等报刊纷纷宣传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逐渐成为有深远影响的思想潮流。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1920年夏至1921年春,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相继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了初步的组织基础。
(二)培育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中国社会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各式各样的理论涌入中国。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合作主义等观点在报刊上纷然杂陈。其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⑥。在此形势下,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李达等《新青年》编辑以该刊为战斗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同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展开激烈论战,培育出一批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组织条件。回忆这段历史,毛泽东指出:“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⑦
《新青年》在五四运动之后刊登的文章多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据统计,自第5卷5号起至1926年休刊期间,所发表文章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有200余篇⑧。这决定了它的受众必定是有一定文化水平和思想深度的先进分子。在当时,受《新青年》影响的受众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接受近代教育成长起来的进步青年,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另一类则是以董必武、林伯渠为代表的民主人士。
其时,《新青年》给进步青年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时,毛泽东就是《新青年》的热情读者。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期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阅读了大量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进步刊物,学习了许多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知识,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前进。在北京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后,1919年他回到湖南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湘江评论》是当时公认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内最有影响力、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1920年11月,受陈独秀委托,他和志同道合的友人成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学生领袖周恩来也是在迷茫中从《新青年》中获取新思想和新观点而豁然开朗,进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董必武和林伯渠都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在辛亥革命之后,眼看国家依然积弱,民族依然孱弱,中国出路究竟在何方?他们陷入苦闷和迷茫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他们分别在李大钊和李汉俊的帮助下,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仔细研读了《新青年》和马克思主义书籍,领悟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必待新兴势力之参与,徒知利用军阀无济于事”⑨,渐渐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董必武对这段历史回忆道,“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⑩
上述两类先进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以《新青年》为利器,在身边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党的发展壮大培养了一大批后备人才。如毛泽东在文化书社销售《新青年》杂志以传播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在私立武汉中学组织学生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撒播革命种子,培养出一大批革命骨干。据统计,武汉中学教师中有5位成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在1927年冬爆发的鄂东“黄麻起义”总指挥部的10名领导人中就有5人毕业于武汉中学。
(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大,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开始利用社会主义的旗号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产生了恶劣影响。为帮助那些爱国、进步的先进分子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划清界限,扩展马克思主义阵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为主要战斗堡垒,同这些人展开思想斗争。
1920年底,马克思主义者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起因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信徒张东荪主动发文倡导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并认为中国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
针对上述观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给予有力回击。他们深刻指出,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是可能的,明确了在中国创立共产党的必要性。其中影响较大的文章多刊于《新青年》上,如《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刊于第8卷4号)、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刊于第9卷1号)、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刊于第9卷3号)。
这场论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又开始另一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斗争。
1919年2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在《进化》月刊上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所谓“集体主义”加以攻击。1920年春,黄凌霜等人又写了《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强权,也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当时迷惑了一些不满社会现实、缺乏理论知识、正处于探索阶段的青年人。
其时,全国各地正在发展或创建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无政府主义者为了争夺青年、争夺宣传阵地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对组党工作危害极大。有鉴于此,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在《新青年》上相继发表《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和中国无产阶级》等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有力驳斥。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使国家消亡;并着重强调“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行不通的路。”⑪在遭受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批判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很快消散。
通过同这些政治思潮的论战,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进行了普遍宣传,还让各地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明确了建党的思想指导。《新青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论战的主要阵地,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界限,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早期党组织中的指导地位,为成立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