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务实本色
作者: 陈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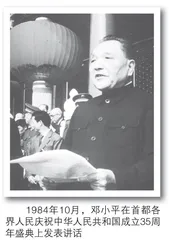
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我是实事求是派。
——邓小平
1980年,四川的一位画家曾经给邓小平画了一幅黄猫黑猫图,以此来表达对这位老人一生坚持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称赞。邓小平欣然接受了这片心意。
它的由来,缘于邓小平在1962年说的一句在全国家喻户晓的名言。那时,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经济形势非常紧张,人民生活很困难。安徽等省一些农村为了度过经济困难的日子,自发进行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各种形式的试验,这在党内引起了争论。
1962年7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邓小平针对当时的争议表态说:“现在是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因为这相当普遍。我们总要有答复。群众的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形式要多种多样。陈云同志也赞成多种多样。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5天后,他又来到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的会场,在向团中央的委员们介绍国内形势时,继续宣传他的观点:“农业要恢复和发展,要从生产关系上解决问题。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为了形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一句四川的俗语: “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句话不胫而走,传遍了全国。“文化大革命”中,这也成了邓小平的一个“罪状”。
像这样幽默简明而又寓意深刻的话,邓小平说过很多。 1978年2月,他在成都对四川省委的领导说:“我在广东听说,养3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5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
鸭子也好,猫也好,人们都能从这朴素的话语中,听出邓小平所要表达的实际含义,就是实事求是。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重要讲话,倡导恢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道: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习近平同志曾讲,“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邓小平同志果断从容处理了党和国家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邓小平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辉煌,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和回响。可人们印象最深的,总是他那谦虚的胸怀、求真的风骨、务实的本色。
即使在晚年获得巨大声誉的时候,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哪怕一些小事,他也会较真地坚持事实的真相。
曾有人回忆说,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一到法国,就“活泼机灵地跑在前面”,向前来迎接他们的法华教育会的代表报告说,船上的重庆学生已分成四组,可以按组上岸。
他知道这个说法后,笑着说:我是那批八十几个人里面最小的,连发言权都没有。
他反复告诉人们: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他又说:这几年来我有意识地减少工作,让别人多做,中国的现行政策并不仅仅体现在我一个人身上。中国的政策并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中国的现行政策是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广泛支持,得到广大干部的支持,干部和群众都要求改革。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
邓小平从不喜欢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
当孩子们问起他在太行山时期都做了些什么事,邓小平只回答两个字——“吃苦”。
在评价刘邓大军的辉煌战史的时候,他也只用两个字——“合格”。
1992年在南方,他依然用短促而掷地有声的话语来评价自己的作用——“我的作用就是不动摇”!
这就是邓小平的风格,这就是邓小平的智慧。几十载风云看淡,一生沉浮逝水无波。邓小平以其独特的方式,坚定地朝着心中的理想迈进。他雷厉风行,果敢沉毅,善于抓住问题核心,一语中的。大山般的缄默是他独特的语言,静水般的沉思是他卓越的思想。
1993年至1994年,三卷本《邓小平文选》出齐。邓小平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在这套三卷本的《邓小平文选》当中。其中的篇章,都经由邓小平校订过。除了少数重要会议上的正式讲话篇幅较长且显得有些凝重外,大量都是谈话记录,语言简单朴素,文风平白实在。
邓小平还给汉字的海洋里增添了许多鲜活睿智的词语: “两手抓”“三步走”“硬道理”“翻两番”“一国两制”“三个面向”“第一生产力”……
简洁明确的语言,传达着耐人寻味的深邃思想。这样的语言,更是充满了智慧和力量。如今,这些词语已经成为今天的中国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如其人。就在他看似轻松的点画中,却逐步展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时代画卷。
邓小平一生崇尚简朴,反对讲排场,反对烦琐哲学。
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指挥千军万马,他始终没有私人秘书。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他也只有一个秘书。
对邓小平来说,人不在多,有效率就行;话不在多,管用就行。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刚在主席台落座,工作人员就给他送上了会议要讨论的文件。他拿起来翻了翻,有些感叹地说:“稿子越讲越多,都70多页了。”
难怪邓小平发此感叹,在他的一生中,开会一般不作记录,平时也很少记笔记,发言时最多一个纸条记几个数字,但凡落笔都在文件上面。
1975年,邓小平负责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啊,“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还在继续,对各项工作的整顿正在邓小平的心中酝酿,极左路线和教条主义正在横行,“四人帮”的许多文章动辄引经据典,空话、废话、假话连篇累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说的话很多很多,要讲的道理很多很多。但是,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只有5100字,却把要讲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心意思表达得清清楚楚,也照顾到了方方面面。
这是邓小平唯一一次亲自负责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字数最少的政府工作报告。
不仅如此,处理文件邓小平也是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拿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的办公室确实干净简单,除了书籍以外,几乎看不到与他工作有关的东西。
说起来还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67年7月19日,一些造反派到邓小平住所抄家,他们在邓小平的办公室、会客室、卧室翻来翻去,希望找到一些“罪证”,可除了书籍外,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找到。极度失望的造反派悻悻地说: “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
不爱记笔记的邓小平,喜欢用数字说话。他不喜欢用形容词代替量词。谈论事情,他不喜欢模糊含混,吞吞吐吐,他做决策,干事情,总是追求“心中有数”。因为他是一位求实、务实、踏实的实干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就用90万、6000万和60万三个数字概括了西南地区的形势和任务。
1950年1月8日,第二野战军举行完进入成都的入城仪式后,邓小平就感到,部队的思想,主要是团以上干部的思想,有必要加以提高。部队打了胜仗,进了城,建立了政权,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尽情享受胜利果实了呢?邓小平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面临的任务不仅更多,而且更艰巨。他先是起草了《二野前委关于克服享乐思想迎接新任务给杜义德同志并川南区党委的信》,随后又在三兵团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向中高级干部耳提面命。会议一开始,他就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西南的仗打完了没有?”
干部们面面相觑,不知邓政委此问何意。西南已经解放,敌人已经被消灭,只剩下零零星星的若干土匪,难道政委是指这个仗还没完吗?在这些南征北战的军人们看来,对付这些土匪,等于牛刀杀鸡,不好意思说是什么打仗了。
就在干部们的思索中,邓小平分析道,西南现在面临着 90万、6000万和60万三大任务。90万,是指要把战争中投诚和俘虏的90万国民党部队改造成人民的军队;6000万,是指西南地区7000多万人口中,有6000多万是我们要依靠的人民群众,要组织他们实行土改,发展经济;60万,是指在西南的60万人民解放军,要把战斗队变为工作队,创造和建设一个新的大西南。面临着这样重大的任务,怎么能说仗打完了呢?
三个数字,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西南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给干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有些干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邓小平到基层调研,也特别喜爱打听数字。
1958年2月,邓小平到四川农村视察。在隆昌县新生高级农业合作社,当社长拿出笔记本和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准备汇报时,邓小平摆摆手说:“不用了,还是我问到哪里,你们就答到哪里吧。”
于是,在一片坪坝上总书记和农民开始了这样的问答。 问:“你全大乡有好多党员、好多团员、好多个党支部、好多个团支部、好多贫农、好多中农?” 答:“有500多党员、700多团员、19个党支部、19个团支部。”问:“你们的粮食亩产量有多少?” 答:“大多数亩产五六百斤,小面积可达七八百斤。”问:“社员一年能分多少斤粮食?” 答:“谷子分得到四五百斤,加上小春和杂粮,拉拢来算,一个社员平均分得600多斤。”
邓小平听到这里,说:“少了,一般来说要八九百斤,包括牲畜粮要千把斤才够。” 他接着问:“你们高级社有多少人口,多少土地?” 答:“全社有5600多人,1100多户,社里有5个管理区, 32个生产队,全社有土地5800多亩,人均1亩多地。”问:“社里喂了多少猪?” 答:“全社的公有猪、私有猪加起来共有5100多头,人均近0.9头。”
“看起来你们这几年养猪事业发展得还是不错的,但是还不算多,要争取发展到一人一头猪或是一头多一点。” 邓小平评论了几句,接着问:“你们社有好多堰塘,兴修了多少水利?” 答:“堰塘不多,新修的山湾堰塘比较多,全社有108个堰塘。” 邓小平批评说:“你们的植树造林搞得不好,没有什么树木,要下点功夫搞绿化。”
然后,邓小平提议进村里去看几家农户。在农民郭士元家,他问了能分多少粮食、两头猪一天能屙多少粪。在另一户农民家,他问了一个老大娘一天能绩多少麻、能有多少收入。他还问了高粱、花生、油菜的产量,问了鸡蛋的价格。
每一个问题都和数字有关,每一个数字都和人民的生活、生产有关。
在农村这样,在企业也如此。
1961年,邓小平到大庆视察工作。他在一口油井旁和工人聊起来。 问:“这口井每天产量多少?”答:“用12毫米油嘴每天产油120吨。”问:“用7毫米的油嘴每天产量多少?”答:“可以产50吨。” 邓小平说:“恐怕不止这个数,要有70吨到80吨。”他问油田领导:“职工生活如何?一个月吃多少钱?”还问:“去年盖了多少平方的房子?(指职工住房)今年准备盖多少?每平方多少钱?”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数字是冰冷的,枯燥的。但在邓小平的眼里,这些抽象的数字却是富有生命的,是实事求是的“实事”。了解了这个“实事”,才能做出正确的合乎实际的判断和决策。
邓小平不光问数字,还帮着地方的同志算数字。他算的账,十分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