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剧:用肢体创造幻象
作者: 张秀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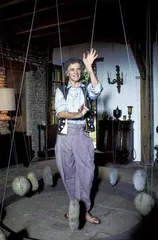


在学习即兴的第二年,我加入了号称中国唯一默剧社的拿大顶剧社。那是2014年,拿大顶剧社成立的第三年,而如今我们刚刚在望京的磁剧场度过了剧社14周年的生日,它已是国内知名的新喜剧创作与表演团队。
每次在剧场表演默剧时,我总会花些功夫去讲解。毕竟这个剧种相对小众,真正了解或看过的人并不多。默剧作为一种广泛的戏剧门类,虽然与喜剧有所交集,但二者并不完全重叠。这里,我更侧重讨论作为喜剧形式的默剧。
一股不可见的风
说到默剧,有些观影经历比较丰富的人会想到默片,尤其是卓别林的默片,因为他的电影也属于喜剧片的范畴。但如果你真的走进剧场看一次默剧,就会发现它和银幕上的默片有着本质的不同。默片是电影的艺术,尽管演员可能也不说话,做着一些夸张的表演,但他们很少与银幕上看不见的东西互动,毕竟最后还能靠摄影、美术、剪辑补足。但默剧不同,它发生在剧场中,没有后期制作和特效,没有场景切换,有时甚至没有道具。演员会通过无实物表演创造观众无法直接看到但能用想象力看到的东西,比如在王梓的作品《空手道高手》中,空手道选手举起了他的右手,同时发出了“CingLingLing”和“CangLanglang”这两个拟声词,通过自己的肢体控制,让观众仿佛看到他将手变成利刃,劈开了在舞台上并不存在的砖块,就连砖块上的裂痕,还有劈开砖块时发出的巨大声响仿佛观众也感受到了。默剧在英文中也叫Phantomime,是由Phantom(幻象)和mime(模仿)两个词构成的,以模仿的方式呈现幻象,是大家目前在新喜剧舞台上能看到的默剧的主要形式。


现代意义上的默剧大致起源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法国和意大利是西方肢体表演艺术的温床,尤其受到意大利假面喜剧(Commedia dell'Arte)、法国哑剧传统以及19世纪末“白脸小丑”形象的影响。到20世纪中叶,真正将现代默剧推向世界舞台的人是法国默剧大师马赛尔·马索(Marcel Marceau)。
马索曾在二战期间加入法国抵抗运动,战后进入巴黎戏剧学校学习,并深受传奇戏剧大师艾蒂安·德克鲁(Étienne Decroux)影响。1947年,他创造了著名的白脸人物“Bip”——一个穿海魂衫、戴破礼帽、身穿背带裤的形象,这一形象也成为默剧在大众心中的经典符号。这个角色既带有诗意的孤独,也带有荒诞的幽默,是小人物与世界对抗的象征。
在马索最广为人知的作品《顶风》(Walking Against the Wind)中,他仅靠肢体的控制力,让人看到了“风”的存在。他看似艰难地往前走,却不断被一股不可见的风吹着往后退。这种精准又夸张的身体控制,不只是视觉上的“魔法”,更是一种极具张力的叙事方式。据说,这段经典片段还启发了迈克尔·杰克逊发明太空步,他也曾在采访中称马索是他的偶像之一。
默剧作为一种独特的表演形式,肢体表演无疑是其核心。这既是对演员的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帮助。因为肢体语言是最直观的表达方式,它能突破语言的局限,直接触及人类情感的核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多时候靠的是肢体语言。一个眼神的交流,一次肢体的靠近,或是一丝不经意的表情变化,都能传递出语言无法表达的情感和意图。在一些戏剧研究者看来,话剧的灵魂在于剧作家的文字,而默剧的灵魂则完全寄托于演员本身。演员每一个细微的肢体表情,都凝聚着情感的传递,是默剧的语言。
默剧表演无法层层铺设文字包袱,也无法依赖谐音梗、爆笑梗和段子,但它通过精准的肢体动作来打破观众的预期,击中笑点。默剧中的幽默常常来自对日常生活中细微动作的放大,打破观众对于常规的预期,或是与无实物物品或者空间的互动,创造出充满想象力的场景。例如,被困于无法看见的墙壁(可见于马索的《牢笼》,之后被无数默剧同行、爱好者和练习者所模仿),当毽子来踢的摩托车(可见于拿大顶剧社《七年之痒》)。演员用肢体创造幻象,将观众从舞台带入到另一个空间中。这种幽默和想象力,往往更为直接,让观众在充满想象力的动作中获得笑声。
我在写此文的时候,恰好刚刚结束我的默剧和无实物表演工作坊,作为入门课程,最重要的是针对表演精准度和动作节奏的训练。创造幻象固然神奇,但幻象实际上是演员和观众间的密谋,无论哪一方稍加松懈可能就会导致魔法尽失,默剧的演出对演员和观众都有着较高的要求。
我最早学习默剧时,虽然在剧社的年纪最大,但表演能力是最差的。那时我已经有过数场即兴表演的演出经历,但对于默剧,还是不敢上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剧社演出的主持人到慢慢加入演出之中,受到了王梓和武六七地不停敦促,“你得练功啊,张兄!”默剧大概是我接触的所有喜剧类型中最需要身体技巧的,不像即兴表演,即便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素人也能在数小时内创造出一场还不错的演出,但默剧的门槛就高了。
高门槛的默剧
默剧最基本的技巧就是摸墙,它要求演员能够在自己的身体前创造一堵看不见但摸得着的墙。这需要演员的手等身体相应部位在碰触到墙体的一瞬间能够迅速紧张,呈现出发力的状态,让观众产生演员的身体真碰到墙的错觉。这种发力方式和机械舞(Popping)有一些相似之处。在拿大顶剧社里,王梓的默剧技巧和基本功最为扎实,时常会被观众问起是不是会跳机械舞。这种技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像运动员和舞蹈演员一样持续训练。大家常常鞭策我的一句话,也是传统曲艺行当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师傅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虽然这话有些夸张,但也侧面反映出默剧对演员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这也意味着更为枯燥。早年我们在一些社区性质的小剧场演出时,经常有观众觉得默剧好玩,想跟我们一起排练,没过多久就放弃了,主要原因之一是学习起来有些无聊。

对于观众来说,观看门槛同样也高,观看默剧需要集中注意力。由于默剧很多时候没有场景和道具,通过无实物来叙述故事,想要看得清晰明白,需要持续保持关注并且调用自己的想象力。观众哪怕走神几秒钟,就很有可能错过关键信息,导致一个段落都看不明白。为此,王梓和武六七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采用了不同的路径。王梓更加拼命地去锻炼和优化自己的基本功,让表演更加清晰,并且在剧作层面增加笑点的密集度,而武六七则开始手工制作各种各样的道具,辅助自己的演出,形成了不同的风格。
在创作层面,默剧的门槛更让人望而却步。虽然我已经在拿大顶剧社待了十年有余,经历了大大小小几百场演出,但我对于自己从事默剧表演的描述仍然是一只脚刚刚踏进门槛,另一只脚还留在门槛的外面。我在自己的默剧生涯里,创作了十余段作品,但真正能够沉淀下来重复演出的只有寥寥几个,剩下的称不上是合格的作品。我一直被困在如何只使用身体来讲述故事的维度,还没能找到自己在默剧上的风格和叙述语言,而我的情况在尝试默剧的演员中很常见。当我们被迫扔掉语言这个最熟悉的工具的时候,需要培养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思维模式或是默剧语汇。比如,来想象一个场景,我们喝到一杯很好喝的茶,想让别人试一下,在不打哑语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传递这个信息呢?

其实,每个喜剧形式的山峰都同样高耸,但上山的台阶有高有低,于我而言,小步拾阶可能更为适合。我在近几年开始更多尝试Sketch的作品,而对创作默剧作品仍然保持着敬畏之心。
默剧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哑剧。1983年,马索在中国演出后的第二年,王景愉在春晚表演了一个名叫《吃鸡》的喜剧小品,通过无实物表演出了他为吃下一块韧劲十足的鸡肉大费周章的情景。一开始,他从一个空空如也的盘子中揪出一块鸡肉,放在嘴里怎么嚼也嚼不烂,放在手里拽它拉它,手脚并用竟然也扯不断,像橡胶一样弹性十足。接着他用钉子将鸡肉固定在桌子上,绕着桌子足足一圈,才把这块鸡肉分开吃了下去,但又被噎在了喉咙里,最后像魔术一般,从自己的喉咙里掏出一个鸡毛掸子。整个作品只使用肢体的表演让情节不断推进。可能由于这个作品不说话的特性,渐渐被归于一个叫哑剧的类别中。
其实哑剧和默剧在英文中都是Phantomime,有些人会说它们并无区别,但我认为,哑剧逐渐被观众所预期的是小品形式的作品,而默剧包含的意义可能更为广泛。但无论是哑剧还是默剧,它们都可以和外国观众无障碍沟通,我想这也是默剧的魅力所在。
喜剧艺术是自由的
在拿大顶剧社实践默剧的过程中,我还把即兴表演带入其中,在经历了数次失败和挫折后,我们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喜剧形式“即兴说书人”——一人在台上即兴讲述故事,其他演员使用默剧表演形式和“说书人”进行调侃和配合。我仍然还记得当时在一个小剧场中,我们第一次成功将这个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整场笑声不断,故事结束时收获了绵长的掌声。我们也利用这个形式创作了默剧《七年之痒》,杀入了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的决赛中,这个作品也被王梓和武六七带到过《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舞台上。大家可能还在这个舞台上见到过演员潘越,她使用了自创的喜剧形式,类似于独角戏,但不幸发挥失常。然而她并没有因此气馁,反而将她这种独角戏的形式发扬光大,开办了自己的喜剧专场《她没问题》,受到观众热烈好评,现在正在全国巡演。

尽管我花了这么长的篇幅给大家介绍和定义这些新喜剧的形式,但喜剧艺术真正的意义可能在于如何打破这些形式的束缚。
新喜剧通过独特的方式为我们带来了欢笑,同时也让我们深刻反思社会和生活。借用电影《笑的大学》的理念,在美好的时候我们需要喜剧,在艰难的时候我们同样也需要喜剧。喜剧不仅是娱乐的工具,更是情感释放与思想启发的载体。它通过幽默与讽刺,揭示生活的荒谬与复杂,让我们更加开放地面对生活中的困境与挑战。新喜剧正是在不断创新和突破,既满足了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为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思考。
随着新喜剧的兴起,更多年轻的创作者和观众投身其中,不仅带来了欢乐,还重新定义了喜剧艺术的边界。喜剧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搞笑,而是成了社会交流的桥梁、文化反思的催化剂,甚至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
(责编:刘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