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获现实生活中的地方感
作者: 曹梦婉

20世纪的西方世界,科学实证主义所推崇的研究方法忽视了人类的经验与意识。20世纪60年代,地理学家意识到实证主义对于地理学研究的不足,如段义孚、雷尔夫等对实证主义地理学中机械式的数量关系提出批评。段义孚认为,现象学的方法给了地理学研究极大的启示:现象学关注本质,如何谓人、空间或经验的本质?地理学也应研究具体的人与世界,即对“在世界中的人”作出研究。1971年,他在《地理学、现象学与人的本质的研究》一文中首次全面地解释了自己关于现象学与地理学之间联系的思考。由此,地理学家段义孚、雷尔夫等在现象学及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倡导将地理研究回归到人本身,以人的经验世界为基础探讨“人地关系”这一问题。“人地关系”一方面体现在人对地方的爱恋之情,被段义孚称为“恋地情结”,它包括“短暂的视觉快乐、触觉快乐、对亲密熟悉之地的情结、对值得美好回忆的家之爱,对引发骄傲和自豪之感的地方之爱、看到健康和活力之物时的快活之情”(郭文《空间的生产与重塑:流动中的文化古镇》)。“人地关系”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地方感”的缺失,地方于个体而言包含着情感认同与身份认同,“地方感”的缺失则意味着人类情感附属的失焦。在雷尔夫看来,这是人对地方的深度象征意义缺乏关注,也对地方的认同缺乏体会,他将其称为地方的非本真态度,即“无地方感”(爱德华·雷尔夫著,刘苏、相欣奕译《地方与无地方》)。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性大,人们很难再重回故乡获得归属感,那不妨重建自己的“附近”,以此来重获地方依附。
一、“有土时代”对家园的依恋
“地方感与故乡情结”这一主题,历来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话题。笔者将以美国生态学家、小说家、诗人温德尔·贝瑞的《回忆》为例,对“人地关系”这一话题进行分析。这篇小说的篇幅不长,却集作者观点之大成,涉及人地关系、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安迪不幸失去了右手,从此一蹶不振,与家人及邻居的关系日渐疏离,他前往美国中西部参加农业会议,在旧金山目睹了大量的不和谐景象,经历了理性与感性的冲突,他再次归家,在回忆中与自己握手言和的故事。在“离去一归来”的途中对家的情感,连接起了他分离的身体与灵魂。家对人们意味着什么呢?
在段义孚看来,“家”的概念在特质上是最稳定、最完整、最小尺度特征的地方。家对于我们而言是最亲切、最真实,也是最永久的地方。家赋予每个个体独特的身份,是个体由家庭自我走向社会主体的首要场域。身在旧金山的安迪以为能够摆脱在家的困扰,却看到了现代化大城市在工具理性的侵袭下的种种弊端,这里的人们来往匆忙、互不关照,他觉得自己要和别人说话得穿过一个未知的世界。“他们是孤独的,沉重的,没有休息的。”这里有着高效率高标准的工业化生产,机器持续运作,寂静的傍晚也会传来低沉的嗡嗡声。而安迪记忆中的家乡是有生气的,在田间劳作时,热气紧紧地包围着他们,他们觉得必须踞起脚尖才能呼吸到足够的空气。他们会把汗湿的衣服挂在杨柳上晒干,然后钻进没过鼻子的凉水里。这样的手工劳作虽然辛苦,但人们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相较于在旧金山的冷漠与疏离,安迪怀念家乡威廉港的土地、家人与邻里乡亲。
正如现代的人们热衷于空间流动,大部分都有过背井离乡的体验,但其过程并非一个将自己转化为他乡之人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加强自己对故乡的归属感以至于涌现出新的自我意识。其实安迪也并非一开始就归乡从事家庭农业生产,大学毕业后的他在一家农业杂志社任职,在采访过两个性质完全相反的农场后,他看到企业农耕与家庭农耕的不同。“在那两千英亩的土地上,没有篱笆,没有动物,没有树林,没有树,没有花园。整个地方都种满了玉米,一直长到两三个还没有使用的谷仓的墙边。迈克尔伯格拥有一群机器。他的粮仓占地数英亩。他有一间像银行行长一样的办公室。”并且,迈克尔伯格为了更大的经济利益,负债累累,身体也是每况愈下。而特罗耶自给自足的小庄园在作者的笔下则是和谐温暖的,“那是一个家。它是许多生命的家园,有驯服的,也有野性的,特罗耶的生命只是其中之一”。在这里安迪感受到了亲切、愉快和欢乐,他写不出夸赞迈克尔伯格的报道,经历了此番采访,在特罗耶的身上,他看到了农人与土地间良好的关系,他开始明白了父辈对于土地的情感与羁绊。于是,安迪选择因此辞职返乡,抵制农业产业化,想要重振传统有机农业。在两次目睹了新兴工业文明的机器生产对原有的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后,笔者认为,安迪对于家乡的依恋之情被激发的同时,还隐藏着对家园丧失的焦虑,未被机器生产完全影响的家乡,还保留着和谐的生活状态。在依恋与担忧的双重影响下,安迪对于家乡、土地的感情得到了新的升华,这不仅仅是“思乡”之情,而是把自己完全当作土地的一部分。这和雷尔夫所言的“本真的地方感”不谋而合,雷尔夫从海德格尔的“此在”入手,认为本真的人能够为自身存在承担起责任,那么同样本真的地方感是人类能够充分认识到同地方间最根本的关系并为之付诸行动,笔者认为,这是“恋地情结”的又一诠释。
二、 “无土时代”的怀旧与逃避
地理学家怀特在《未知的土地:地理学中想象的地方》一文中做出了对于“地方”的定义,他认为“地方”是承载主观性的区域。借由此,段义孚与雷尔夫将“地方”这一概念重新引入人文主义地理学,将“人地关系”中的“地”延伸到了“地方”,探讨人的经验以及经验在构建地方感中的作用。从人的经验出发,若能建构起一个地方,这就需要人们与之产生情感联结。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日渐分离,个体也从社群中脱嵌出来。人们的生活环境不同于前现代的“熟人社会”,在极大的流动性中离开熟悉的环境,前往陌生的地方求学供职,对地方的陌生与疏离感也是现代人常有的一种体验。
《回忆》中的安迪并未在他乡感受到温情与关怀,作为一名记者,他在城市中始终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生活。笔者认为,此时的安迪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归属感的缺失,因为安迪的父亲惠勒大学毕业后婉拒了老师推荐的芝加哥大型包装公司的法律工作,而是选择归乡从事农业生产。周围的人纷纷表示不解,而惠勒认为建立良好、持久的社区是他自己的责任。当时的安迪显然和大多人的想法一样,认为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远离务农生活,便是一条成功且平坦的人生之路。安迪真正感到“地方感”的缺失源自在旧金山的经历一右手不幸被收割机所伤。他整日对家人邻里冷淡,并在家中感到了束缚与不安,于是借开会之名逃离。段义孚以经验的视角将空间与地方对立,他认为地方意味着安全,空间意味着自由;他认为地方是具有既定价值的安全中心,它大小不一,故乡则是中等程度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在此基础上,笔者试着将充满回忆与温情的故乡看作“地方”,将充满自由与未知的他乡看作“空间”。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家”给人归属感与安全感的同时,也在另一方面象征着束缚。这种束缚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安分守己,特别是当所处环境周围的人都远走他乡时,留在家乡的人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被拴住的羞耻感。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wxji20251473.pd原版全文
段义孚认为,乡村的年轻人会离开他们小小的故乡,去往大都市的中心的一个原因在于:故乡缺乏空间。经济领域的机会匮乏和社会领域的自由匮乏使孤立的乡村显得狭窄有限。安迪便是因为这样一种空间的匮乏选择前往旧金山,到了目的地之后,作者温德尔·贝瑞利用光线与时间对安迪的内心有了这样一番描述:“天很黑。他不知道他在哪儿。慢慢地,他看见了渗过窗帘,来自街上的微弱的光线,这光线不足以让人看清东西,反显得黑暗越发清晰。”紧接着,安迪做了一个噩梦,梦中他曾经的家乡被毁,找不到任何关于过去的东西。金衡山在《回忆与愈合一当代美国作家贝瑞及其小说<回忆〉》中认为,此时的安迪正在经历一种认同危机。他处在一个被黑暗笼罩的房间里,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儿。安迪此梦的真正含义是揭示了他孤独的心理状态。他不是没有家,而是自己离开了家,到了一个自己不知道在哪儿,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的地方。可以说,这是一种自我放逐的行为。他参加了一个纸上谈兵的研讨会,除他以外,其他专家均没有农耕的经验,也正是这次会议,给了安迪一个恢复自我意识的契机,在这样一种“空间”中,安迪意识到了空间自由之外的另一面一—威胁与不安。他从主动与“家”分离,到真正感受到了“地方感”的缺失,进而开始思考“家”的真正意义。
他忆起了自己的童年、恋爱、家人与好友,曾经的温暖记忆渐渐治愈了他心灵的创伤,他结束了自我流放,拾起了自己曾丢弃的右手钩子,踏上了归乡之路。
温德尔·贝瑞通过安迪一方面表现出农耕文化的救赎功效,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工具理性下当代社会的危机。在此基础上,段义孚的观点影响深广,一度令家乡和郊区乡镇成了抚平人们心灵创伤的避风港。而现象学强调从个体经验出发,本就存在一些排他性和怀旧性,因此这也让个体对家园与故乡的理解蒙上了理想主义的面纱。但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或许不能和《回忆》中的安迪一样幸运,因为离家早已成为一种常态,在外漂泊时,少了家的关怀和依靠,人们也产生一种“无根感”。在现代社会中,漂泊的生活成了“恋地情结”的源头,出走和乡愁在现代社会是一体两面的。对故乡的依恋是人类的一种共同情感。但我们不难发现,返乡后的家好像也和想象中的不大一样,因为现实的家与我们的内在精神发生了错位,在外漂泊的压力培养并催生出了人们对家的情感,将家乡理想化、浪漫化。由此可见,因离家而产生的“无根感”并不能通过物理意义上的回归得以改善,这一漂浮的“根”是要经历新的生长之后才能再次扎根的。家乡永恒的温情与安逸或许在传统的古老社会中局部地存在过,但现代人也必须有勇气承认,这样一种乌托邦早已不复存在。
三、与所居之地的持续相遇 一重建身边的 “附近”
宋秀葵在其著作《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一书中提到段义孚观点,“当人将意义投注于局部空间,然后以某种方式(如命名)附加其上,空间就成了地方”。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从主体经验出发,对所处的空间付诸实践、投入情感,也可以在家园以外获得新的归属感。人类学家项彪针对功能性过剩、生态性不足的城市生活,提出了“最初500米”的倡议,以此来重建消失的“附近”。在《“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人类学家项飙访谈》一文中,项飙认为,“附近”的概念受到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旨在发展一种“生活的人类学”,希望能使个体在无法改变整体性环境的条件下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而“附近”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现实的、小的突破口。笔者认为,这一概念也可以缓解人们对于“地方感”的缺失造成的负面影响。如今随着数字化媒介的发展,人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脱离实体空间与地方与他人取得广泛联系,或许这使人们忽视了身边具体的空间。“最初500米”是一个人通往外部世界的第一步。这是从每一个个体出发,使“小”的附近与更“大”的世界得以连接。在《回忆》中,安迪在旧金山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路上的行人们均是孤身一人,彼此相距甚远,面无表情地低头赶路,因此安迪在旧金山的体验也是机械的、冰冷的,这呼应了格奥尔格·西美尔在《大都市和精神生活》中所言的“矜持人格”—大都市的人们对彼此的心理态度可以被正式指定为一种保留。可见,这样一种保留态度并不能认识身边的“附近”,更难以获得在地的归属感。
或许重建“附近”已经为获取地方认同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法论,从“最初500米”开始,人们可以通过交互与了解,与周围建立新的联系,独立的个体之间凭借语言、文化喜好相互沟通交流。正如段义孚所说,在人们真正相互关注和交流的时候,亲切感就会流露出来。倘若能向多个方向扩展500米,覆盖个体所处的这一空间,个体会收获新的情感体验与价值立场,构建出新的共同体,这一空间就有了形成新的“地方”的可能。人们在新的“地方”产生归属感,进而形成对此地的依附,那么反过来,人们得以依附的地方也会给人们关怀。雷尔夫认为,这是人对一个地方的全然委身。这一概念与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有所相似,“栖居”是人类得以存在的本质,也是存在的基本性质。海德格尔将人们对于“存在”的遗忘,视为现代人无家可归的根源。不少学者认为,海德格尔的这一观点过于悲观,这在根本上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因为人拥有探寻安全稳定的容身之所的能力,离家的人,依旧可以建立一个新的“附近”,将个体经验投掷其中,形成新的地方依附。正如“此心安处是吾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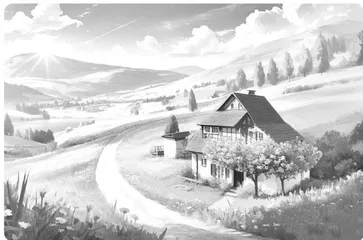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wxji20251473.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