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人才培养:内涵建构与教育应对
作者: 陈婧 张羽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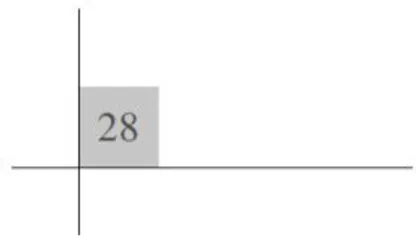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G642;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5)03-0027 -11
DOI:10. 15958/j. cnki. jywhlt. 2025. 03. 003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颠覆性技术重塑产业形态,加速了传统技能淘汰。传统产业的衰落伴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传统岗位的饱和催生了新兴岗位的需求,进而驱动世界对新质人才的需求。202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重要论述,强调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1]。《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措施,要求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前沿领域推进教育改革布局[2]。在此背景下,新质人才作为适应新质生产力的主体成为理论焦点,其内涵及培养路径等问题逐渐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教育领域探索的新议题。在内涵探索上,有研究指出新质人才需掌握数字技术、具备自我意识、开拓创新及伦理和社会责任,以推动行业发展和社会进步[3];在培养路径上,有学者认为教育体系需要从传统的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强化问题导向与项目导向,整合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构建全面、系统的融创教育体系培养人才的创新性与跨界融合能力[4]。以上前沿探索说明新质人才的培养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同时,新质人才的内涵完整性有待丰富,如责任伦理等维度的具体素质尚需进一步探讨。其培养路径的转型问题虽已引发关注,但具体举措背后的教育目的观重塑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基于此,本文从全面剖析新质人才的内涵出发,分析我国新质人才培养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困境,据此提出教育应对策略。这不仅有助于丰富教育理论研究,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实践指导,对于构建面向未来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新质人才的内涵建构
新质人才是在新一代科技革命背景下提出的,其核心是通过动态适应技术迭代与社会变革以应对复杂问题并驱动可持续发展。在学术视阈下,新质人才的提出并不是要全面否定既有的人才观和培养实践,而是要实现人才的迭代升级。相较而言,新质人才与传统人才在价值导向、能力结构、技术操作、学习模式和责任伦理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一)创新型价值导向
当前,全球正经历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迭代周期从“十年一代"缩短至“按月更新”,传统线性增长模式被颠覆,技术“创造性破坏”成为常态。若仅依赖既有知识储备,难以适应技术快速更迭的职业场景。唯有以创新驱动为内核,才能主动应对而非被动适应变革。在此背景下,个体发展的底层逻辑被重构。麦肯锡研究显示:到2030年,全球30% 的职业活动可能被自动化取代,但对卫生专业人员和其他STEM相关专业人员等创新型职业的需求将增长 17% 至 30% [5]。传统“技能本位”的竞争力逐渐失效,个体价值越来越取决于提出新问题的能力而非解决旧问题的效率。例如:在智能制造领域,操作工人可能被机器人替代,但能够设计新型人机协作流程的工程师将成为核心资产。创新驱动能力由此成为人才抵御职业风险、实现自我迭代的“护城河”。
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将创新驱动纳人国家战略核心。美国的《无尽前沿法案》提出斥资千亿美元强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关键领域创新能力;欧盟“地平线计划”明确要求研发项目必须包含跨学科创新模块。中国“十四五”规划更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支点。2022年全社会研发投人强度达2.55% ,但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仍较高[。这一矛盾凸显了培养创新型驱动人才的紧迫性—唯有通过人才的“创造性破坏”,才能突破“卡脖子”困局,实现产业链价值跃迁。
“创新型驱动力量”是新质人才发展与行动的源动力,是其区别于传统劳动力的本质特征。在价值导向方面,传统人才的培养模式更加关注个人职业的成功,因此其价值导向更多是任务驱动,即完成既定目标和任务,注重效率和稳定性。新质人才则更注重创新驱动以追求突破性成果,强调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平衡。这种价值驱动力既是应对技术洪流的生存技能,更是引领文明进步的变革动能。它并非个体偶然的灵感进发,而是融合知识、思维、实践的三维能力体系。具备创新型驱动力量的新质人才在知识基座上,掌握跨学科知识图谱;在思维范式上,具备批判性思维、设计思维、系统性思维;在行动机制上,于资源整合、风险决策、快速试错等环节展现出将创意转化为价值的实践能力。综合来看,创新型驱动力量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增加创新力量,即优化现有技术路径的力量;第二,架构创新力量,即重组技术模块创造新价值的力量;第三,范式创新力量,即颠覆行业底层逻辑的力量。新质人才的创新驱动能力需覆盖全链条,既能在既有框架内持续改进,又能突破边界开创新范式。
(二)复合型能力结构
新一轮工业革命推动知识的边界模糊化,带来技术融合的加速趋势,单一学科已难以应对技术迭代的复合需求。从知识生产模式上看,传统工业时代的学科细分逐渐被应用导向的跨界整合所取代。从现实需求上看,现代实践问题具有综合性与系统性。当今社会的核心挑战(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伦理、新能源研发等)无法通过单一学科视角解决。例如:应对气候变化,需整合环境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伦理涉及计算机科学、哲学、法学等领域的交叉融合;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不仅依赖工程学,还需经济学分析成本效益、社会学评估公众接受度、生态学衡量环境风险。
为此,新质人才在能力结构上更加注重跨界性。传统人才的能力结构通常以单一领域的专业知识为核心,强调深度而非广度。例如:传统工程师可能专注于机械设计或电气工程,但在跨领域协作或解决复杂系统问题时能力有限。相比之下,新质人才的能力结构更加复合化,强调跨学科知识的整合与应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指出: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将更加倾向于具备跨学科能力的人才,这类人才能够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解决复杂问题[7]。这种复合型能力结构使新质人才有望打破认知边界、激发创新潜能、增强适应能力,使人才在技术迭代和社会变迁中保持竞争力,能在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中游刃有余。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jywh20250303.pd原版全文
(三)数字型协作素养
全球产业正经历“数字优先”的深度变革,要求形成技术工具与人类协作的共生关系。未来,大量的专业服务将由“数字游民”通过云端协作完成。传统面对面协作模式被打破,跨地域、跨时区的虚拟团队成为常态。新质人才若缺乏人机协作的数字型素养,将无法融入这一“无边界工作场域”,甚至成为组织效率的瓶颈。故此,传统科层制下的协作经验彻底失效,新质人才需在无层级、无实体的组织中,通过数字契约与共识算法驱动价值创造。
数字型协作素养即形成“人机协同”新型交互逻辑并妥善处理与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协作主体关系的能力。它超越了工具使用技巧,本质上是数字文明中人类集体智慧的新型组织方式,是新质人才在“比特与原子融合”时代的生存护照。相较于传统人才,具备数字型协作素养的新质人才不仅是工具使用者,而且是技术开发者与批判性慎思者。从工具使用者角度来看,新质人才具备工具驾驭力,能够精通异步协作工具、数据可视化平台、虚拟现实会议系统等,并能根据任务需求动态组合技术栈。从技术开发者角度来看,新质人才具备规则重构力,能在数字化流程中建立新协作契约。从批判慎思者角度来看,新质人才能够理解数字原住民(如Z世代)与数字移民(传统从业者)的行为差异,在多元文化中构建协作共识。概而言之,只有具备了数字型协作素养,新质人才方能驾驭虚实交织的协作网络,使其成为数字化生态的价值枢纽。
(四)终身型学习模式
人工智能领域的大模型技术、量子计算的算力突破周期持续缩短(如GPT-4到GPT-5的演进仅间隔10个月),知识半衰期从工业时代的30年骤降至数字化时代的2—3年,这使得传统“一次性教育一终身就业”模式彻底失效,终身学习成为维持职业竞争力的唯一路径。同时,全球产业链正经历“技能解绑一重组”的深度变革,传统职业边界模糊化催生“斜杠型人才”需求,个体需在职业生涯中多次跨越领域。劳动者只有进人终身学习模式方可构建可迁移能力,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不确定环境中实现无摩擦转型。
就学习模式而言,传统人才的培养模式往往只注重阶段性学历教育,即在完成学校教育后进入职场,依赖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参加工作。新质人才则形成了终身型学习模式,具备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这是学习者自我持续发展的重要能力。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发布的《2023年未来就业报告》(TheFutureofJobsReport2023)强调:终身学习能力是未来从业者需要掌握的核心技能,具备快速学习和适应能力的人才将更具竞争力8。朱永新在第五届世界教育前沿论坛中指出:人才培养模式正在从连续性的阶段式学习转向间隔性的终身化学习[9]。终身学习理论由来已久,元学习意识与策略、成长型新质模式与社会化学习网络仍然是新质人才需要具备的。此外,面对浩瀚且更新迅速的信息世界,新质人才还需要具备自我导航能力,具有明确学习目标的定位能力,能自主规划学习路径(如选择在线课程或实践项目)并定期评估学习效果;习得批判性过滤系统,能够在海量信息中构建“信息筛选-价值判断-深度加工”的三级处理机制,避免认知过载。这些能力将构成动态闭环:自我导航驱动学习进程,批判性思维确保学习质量,元学习优化方法论,成长型思维维系学习动力,社会化网络拓展认知边界。
(五)人文型责任伦理
在技术加速迭代与价值多元碰撞的背景下,人类将面临更多、更复杂的伦理问题,所以新质人才的责任伦理尤为重要。作为技术革命与社会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新质人才的责任伦理不仅关乎个体行为的道德边界,更涉及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命题。
相较于传统人才,新质人才的伦理责任必须包括对工具理性的价值校准,以人文主义技术观警惕技术异化对人类主体性的侵蚀,谨记技术应揭示真理而非遮蔽人性。一方面,保留人类最终决策权,避免将生命权完全交由机器判断;另一方面,设立“数字清醒模式”,防止虚拟世界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掠夺性消耗。在此基础上,新质人才需坚持社会正义原则,推动创新成果的普惠分配,主动消弭技术鸿沟,自觉承担数字平权责任,维护数据正义;履行生态契约,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建立生物圈伦理观;建立共同体意识,保持文化敏感性,努力做好文明冲突中的调和者。从本质上说,新质人才的责任伦理是技术文明时代的人类精神“免疫系统”。它要求人才在追求创新的同时,始终以“行星边界”(PlanetaryBoundaries)为约束、以人类福祉为导向、以文明延续为使命。
二、新质人才培养的教育困境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新质人才培养已成为各国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然而,当前教育体系在转向新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仍面临教育目的错位、教育内容滞后、评价机制僵化、教师素质不足等深层矛盾。这些困境不仅制约着人才培养质量,更可能引发社会创新动能衰减的连锁反应。
(一)教育目的困境: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失衡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张力实际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人才培养上的交锋。在人才培养目标上,科学主义以“技术问题解决者”为培养目标,以实用为追求,注重培养人才质量规格的可量化指标。人文主义则主张坚持将人培养为“完整的人”,发展其批判思维、伦理判断与审美能力。这一分歧造成了二者在培养模式上的二元对立。在知识结构上,科学主义强调垂直深化学习,例如深度学习及算法优化;人文主义则要求课程横向拓展,例如博览历史经典。在教学方法上,科学主义采用虚拟仿真实验并进行精准知识推送;人文主义课程则利用苏格拉底式对话法,鼓励跨文化研讨。在评价标准上,科学主义以竞赛排名为评价准则;人文主义则注重提出伦理困境解决方案,采纳社会影响评估报告进行评价。
诚然,在理论上讨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难免陷入二元对立的哲学桎梏,但在实践中科学主义确实占据上风。现代社会被工具理性所主导,追求效率与可计算性,很可能导致价值理性的式微。这表现为:教育目的从“培养完整的人”异化为“人力资源生产”,单纯依赖市场信号来评价人的价值,片面依据教育的经济价值来论断教育的价值。需要警惕的是,教育体系深陷“就业率锦标赛”的泥淖。当学校以“专业对口率”作为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指标,则难免使得教育目标过度聚焦岗位技能培训。这种工具理性导向,使得人工智能专业沦为编程技能训练营,而忽视算法伦理、社会影响等维度培养,新质人才的人文型责任伦理培养成为一大难题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jywh20250303.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