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夏,要解决的谜题还有很多
作者:肖楚舟 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中心地带,基本保留了沙皇时期的城市格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下文简称“东方所”)就在冬宫隔壁新米哈伊洛夫宫的侧翼中。那是一栋临河的建筑,风格古典大气。这里收藏着百余年前科兹洛夫(Kozlov)从黑水城带回的西夏文献。
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中心地带,基本保留了沙皇时期的城市格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下文简称“东方所”)就在冬宫隔壁新米哈伊洛夫宫的侧翼中。那是一栋临河的建筑,风格古典大气。这里收藏着百余年前科兹洛夫(Kozlov)从黑水城带回的西夏文献。不止一位前往圣彼得堡查阅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中国学者提到,他们曾在这栋楼的阅览室度过漫长的时光。调阅资料、释读残卷的间隙,从东方所巨大的玻璃窗看出去,便能见到浩荡的涅瓦河,河对岸彼得保罗要塞的尖顶近在咫尺。
东方所的前身是1818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下令设立的“亚洲博物馆”,它的成立标志着俄罗斯帝国对东方的兴趣增长,而黑水城的发现无疑是俄国充满野心的东方探索中最不容忽视的篇章。
1930年,苏联政府将亚洲博物馆改组为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个部门,专门负责东方语言、手稿、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37年,随着几位重要的苏联西夏学研究者陷入政治迫害,西夏文献也陷入了无人问津的处境。俄罗斯西夏学大家克恰诺夫(Kychanov)曾回忆: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所有来自西夏的文物都被存放在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的东方文献研究所。所幸在敌军的狂轰滥炸中,这座图书馆幸免于难。1950年代,东方文献研究所迁往莫斯科,在彼得堡留下分所,黑水城文献也留在了涅瓦河畔。
黑水城发现的这批文献,内容极其丰富。俄罗斯之所以能成为西夏学最早的研究中心,基本上要归功于它们。从西夏文的字典、律令、佛经,到历法、医术这类实用读物,再到西夏人原创的典籍,几乎涵盖了西夏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俄罗斯汉学家伊凤阁(Ivanovich)和科特维奇(Kotwicz)等人最早发现了解读西夏文的钥匙《番汉合时掌中珠》,也将它的片段透露给中日学者。此后两到三代俄罗斯学者花费数十年整理文献编目,厘清文献内容。这些看似基础的工作,为我们认识西夏奠定了最初的可能性。
如今,黑水城文献的面貌越来越完整地展露在学者们面前,可研究的细节也越来越丰富。东方所现任所长伊琳娜·波波娃(Irina Popova)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介绍了俄罗斯西夏学研究的历史、现在和可能的未来。 三联生活周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东方学者眼中,西夏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为什么俄罗斯东方学者对西夏文明如此感兴趣?
三联生活周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东方学者眼中,西夏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为什么俄罗斯东方学者对西夏文明如此感兴趣?
波波娃: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东方学家,主要依据中国历代正史的视角研究这个地区的历史。我们知道西夏国的存在。它在公元10世纪建立,1227年左右被蒙古人灭国。但在这段时间内,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包括自己的书面文字。
1908年科兹洛夫在黑水城的发现,提供了新的历史细节,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国西北地区在特定时期的历史的认识,使得我们可以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原、西夏和藏民族之间的关系。西夏和北宋之间连年战争,但西夏人也向宋朝学习、借鉴了许多知识。借助黑水城文献,俄罗斯学者们得以对过去的认识做一些修整,比方认识到西夏统治者的重要性,了解到西夏人的历史观,获得更多的历史细节等等。这些材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为我们了解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人看到西夏文字,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俄罗斯学者第一次看到这些文字是什么感觉?您是如何学习西夏文的,它们让您产生什么样的联想?
波波娃:我是在克恰诺夫教授的指导下学过西夏文,他给我讲解了西夏文语法、读法,以及怎么在他的字典里查字,这样我就能自己借助索弗罗诺夫(Safronov)的语法书和克恰诺夫的字典自学。
俄国的东方学家们第一次看到这种文字,首先断定这是一门未知的语言,但在科兹洛夫发现黑水城之前,法国人德维利亚(Devéria)和布歇尔(Bushell)等人就已经发现过西夏文碎片,并大致描述过它们的特征。所以不能说这种语言是完全神秘的,但它能被破译,是因为俄国学者从黑水城文献中发现的字典。
西夏文确实非常美丽,它是党项人在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明的文字。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下令创造了这种文字,又组织人员大规模将佛经翻译成西夏语。可以说,当时西夏整个国家都高度重视这种独特文字的创造。我自己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会联想到哥特体——一种古老的德文字体,非常优美有趣。西夏文绝对是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创造的,所以非常漂亮有趣。如果熟悉汉语,自然能把它们和汉字联想到一起。
三联生活周刊:俄罗斯西夏学的前辈们,提出了哪些解读西夏文的基本方法和思路?有哪些沿用至今,哪些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弯路”?
波波娃: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我们非常尊敬这些前辈,不会说他们的方法有错。毕竟他们是第一批开始做西夏文解读工作的人。当然,后来西夏文的释读进入了新的阶段,更多文献被引入研究领域,所以也出现了一些修正。这就好像在建筑基础上加一些装饰元素,而基础是聂历山(Nikolai Nevsky)和克恰诺夫打下的。
聂历山理清了西夏文的语言结构,克恰诺夫和索弗罗诺夫则一起研究了西夏文的词汇注释。俄国学者写了最早的西夏文解读专著,后来中国学者聂鸿音和日本学者荒川慎太郎(Shintaro Arakawa)也陆续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但基本还是沿着前人的路径来走的。
三联生活周刊:不同国家的学者,在解读西夏文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方法或者思维方式吗?
波波娃:会有不同,但基本相似,因为大家都是基于同一批基础材料进行研究工作的,只能在可能的框架内工作。日本也好、中国的研究者也好,都借鉴了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当然我们也关注日本和中国学者取得的进展,尤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之后,大家就可以借助不同的文本,开始进行细化的研究工作了。
三联生活周刊:俄罗斯西夏学的两位先驱,伊凤阁与聂历山都死于1937年的苏联肃反运动。如何理解那一代俄罗斯东方学者的命运?俄罗斯的西夏学是如何在此之后恢复发展的?
波波娃:伊凤阁是西夏学研究的开拓者,他和同校的科特维奇教授是第一批研究科兹洛夫带回的西夏文文献的人。据推测,也是伊凤阁发现了《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本汉夏对照词典,成为后续研究的基础。而根据伊凤阁本人的回忆,他自己编过一本词典,在科学院出版社压了很久,在他被捕期间稿件被没收了,就那样丢失了。
聂历山是伊凤阁的学生,他在中国时,从伊凤阁那里见到了西夏文献的照片。他也是因此从日本回到苏联的。他研究西夏语的同时,也在大学教授日语,是位非常出色的教师。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苏联国内四处抓捕间谍,他被指控为日本效力的间谍,被枪决了。于是他花费七年心血做的西夏文献编目工作停滞了十年。只有龙果夫(Dragunov)一直在做编目工作,也有些东方学者做了些零散工作。
但真正系统性地恢复俄罗斯西夏学研究的人,还是克恰诺夫。他在西夏学家卓娅·戈尔巴乔娃(Golbachova)的支持下,完成了最早的文献整理和编目工作,主要是夏译汉文文献。后来他才开始钻研西夏文写的佛经和西夏本土文献。他最出色的成果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译本,也就是天盛年间的西夏法律。克恰诺夫翻译它花了多年时间。总而言之,这确实是部里程碑式的杰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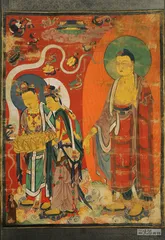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研究状况如何?可以说学者们基本已经掌握它们的全貌了吗?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研究状况如何?可以说学者们基本已经掌握它们的全貌了吗?
波波娃:聂历山是第一个比较全面地描述了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人。他的遗著《西夏语文学》在1960年代才出版,他本人在1962年被追授了列宁勋章,这是当时苏联的最高国家奖项。1950年代,东方所建立了西夏学小组,基本上黑水城文献中最重要的大部头作品,都得到了甄别,收进了目录。当然,还有一些极其重要的文献亟待处理。主要是西夏草书写成的文献,现在能读懂它们的西夏学家并不多。这类文书,中国学者史金波等已经将它们引入了学术研究。它们反映的是当时西夏的社会结构。
得益于国际学者的合作,现在很多工作已经开展:有的学者关注西夏法律,有的专攻佛教典籍,有人研究社会文书等等。这些工作,不仅让我们认识了西夏,也看清了当时整个中亚地区的局势。
不过还有一些零散的文书被陆续发现,它们需要和那些已经整理出来的文献进行整合,其中关键就是通过考察文书的笔迹、行距、纸张类型、纸张特性等外部特征,分辨它们是否和其他碎片有关系。比如残片1和残片2是不是属于同一文献。这些小小的碎片,还需要继续拼合和修复。修复说到底是个永恒的工程。
在我们研究所修复文件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献碎片。西夏人也会对书籍进行修补,会把写过字的纸二次利用。现在,我们那些小心谨慎的修复师仍在继续这项工作,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距离黑水城文献的发现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现在这些文献的保存是否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黑水城与圣彼得堡的气候完全不同,它们需要特殊的保护措施吗?
波波娃:就像所有来自远古的文献一样,它们需要呵护。需要始终存放在特定的湿度下,这些文献的保存都有特定的国际通行技术,不管在中国、欧洲还是俄罗斯都是通用的,我们也同样遵守。而且有监管机制,会有工作人员定期来检查我们这边文献保存的情况。总的来说,这些文献处于稳定的状态中。
大体上,我们需要保持房间干燥,温度不能过高,总之多少要符合它们被发现时的“舒适环境”。毕竟文献出土时的环境,即墓葬里的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我们的修复师、学者,都为了防止它们的损毁做了大量工作。有时候也需要“保护处理”,如展平文献,清除上面附着的木屑、泥土。这些主要工作已经完成了,但还得持续监控文献保存的状况。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介绍一件您个人最喜欢的西夏文献?
波波娃: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贞观政要》。西夏文《贞观政要》是现存最古版本的《贞观政要》,也是目前所知唯一的少数民族文字译本。俄藏版本的《贞观政要》先是随着科兹洛夫找到的文献一起来到俄国,后来移交给我们研究所的前身亚洲博物馆。直到来到亚洲博物馆,它才得到了专业学者的研究。它被翻译成西夏语,表明这部经典不仅在中国广为流传,在与中国接壤的民族中也广泛传播。
三联生活周刊:和上世纪相比,如今西夏学研究的国际合作情况如何?
波波娃:据我观察,现在出版的西夏学英文专著很多,也都是基于俄罗斯前辈的研究。不过在学术著作的出版语言上,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作为一种学术语言,俄语越来越弱势。我现在正在亚美尼亚的埃里温开会,但基本上学者们使用的是英语或亚美尼亚语,只有少数和我同龄的亚美尼亚研究者能使用俄语。这让我有点伤感,因为前人曾用俄语做出过伟大的研究,而他们的研究还未被充分地介绍到英语的主流学术圈,或者中文学术圈。我觉得还得等待时机。
国际合作当然存在。这门学科本身较为冷门,因此离不开国际合作。最主要的西夏文物仍然在俄罗斯,合作会继续,学者们会继续交流。在这方面,中国学者起到了重要的整合与推动作用。如北京的聂鸿音教授、银川的杜建录教授、西安的韩小忙教授——他们培养了许多学生,建立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在欧洲,大约也有10到15名西夏学者,不过他们不一定都懂西夏文。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西夏研究中,最令人好奇或者神秘的谜题是什么?我们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解决它们吗?
波波娃: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但很难回答。毕竟西夏确实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它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融合了中原的传统,和更为南方的文化传统,尤其在佛教方面。破解西夏谜题的关键就在此处,这是一个巨大的谜团。而由于党项民族本身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文物和文字保存下来,那终究不是活的语言。
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我个人非常好奇:西夏的行政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因为它常年与周边的国家交战,这是一套带有半军事化特征的行政体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和人文传统,人文文化在西夏的运作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当然,这是未来的研究者的任务了,这要求学者博学多才,既有语言功底,又要懂各民族文化,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实习生罗清如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