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与惩
作者:卜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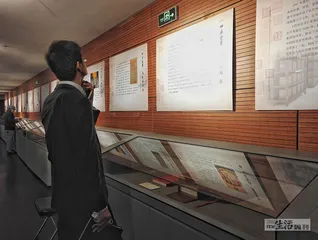 京畿三阁的重校,在文津阁本发现讹误后即行展开,乾隆挑选随行卿贰等员在避暑山庄校改,同时命留守京师的四库馆臣组织人员详校文渊、文源二阁全书。二阁各由学问卓著的馆臣领衔,各带124名详校官办理,自与核校文津阁本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不同。看过京城发来的办书章程,乾隆对文津阁本又不踏实了,遂决定先以重点核查和提出疑问为主,待回京后命纪昀带领出错的原纂校人员,再来山庄修订。
京畿三阁的重校,在文津阁本发现讹误后即行展开,乾隆挑选随行卿贰等员在避暑山庄校改,同时命留守京师的四库馆臣组织人员详校文渊、文源二阁全书。二阁各由学问卓著的馆臣领衔,各带124名详校官办理,自与核校文津阁本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不同。看过京城发来的办书章程,乾隆对文津阁本又不踏实了,遂决定先以重点核查和提出疑问为主,待回京后命纪昀带领出错的原纂校人员,再来山庄修订。校对是编纂每一部大书、自也是兴修四库全书的重要环节。汉刘向论校雠之“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宋朱翌《题校书图》所吟“我闻校书如扫尘,尘随帚去辄随有”;晚明李维桢称“校书犹扫落叶,随扫随有”,皆亲历者之深切体会。清代档案文献中对此用词不一,为避免阅读时发生误解,兹将四库的校对稍作梳理,并对几个语词略加辨析:
开馆后即设校对,规范说法是分校,分别校勘之意也;
曾设复校,负责复核分校完成的文稿,不久即以人手不够裁撤;
上面有总校,陆费墀先被重奖后被严罚,皆因他是唯一的总校官;
有总阅官,人数较多,似乎是荣誉大于实际作用。
而此时北四阁成书入藏皆已数年,弘历命再次选调人员校对,所发谕旨为“再行详加校阅改正”,相关措辞多据此衍生,如校阅、校改、详校等。永瑢等在章程中称参与人员为详校官,后来奏报多用“详校”一词。而“重校”出自纪昀的奏折,准确且不易产生混乱,故加采用。
五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乾隆结束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回到圆明园,五日后还宫。此时两阁的重校基本完竣,不管是在园在宫,主事馆臣都会向皇上奏报办理情况和存在问题,也会拿一些夹着签条的书册呈递御览,以作为重校之必要和重要之证。弘历颇感满意和放心,降旨表彰重校中“签出违碍错误之详校官”(注意,此处应专指发现了政治问题),有胡高望、吉梦熊、阮葵生、祝堃等四人,俱交吏部记录一次。前三人皆位至卿贰京堂,随皇上至热河,参加了文津阁本的校改,“签出《尚书古文疏证》《松阳讲义》二书并有违碍字句”,已为弘历所了解;而祝堃位阶较低,为翰林院编修,参与校阅文源阁本,则出于永瑢等在京馆臣的特别奏报。祝堃,乾隆四十一年(1776)补内阁中书,四十六年二甲进士,改庶吉士,进入四库馆,“历经派办《总目》及《简明目录》,行走亦属勤奋”,次年七月提前约两年授予编修。这次祝堃“签出周亮工《读画录》、吴其贞《书画记》内有违碍猥亵之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二三九),经审核予以撤改。特旨点名表彰者,两阁详校官仅祝堃一人。
同一天,因三通馆承办《皇朝文献通考》被签出错讹较多,弘历传旨将校阅陈万全、总裁刘墉罚俸半年,三通馆副总裁王杰、彭元瑞也受到薄惩。而乾隆帝深谙驭下之道,不到半个月,就传谕嘉奖分掌两阁详校质量的刘墉、彭元瑞,各赏缎两匹,“余各赏缎一匹”。余,乃指两阁详校人员中“从未曾充当四库馆总阅、总纂、总校、分校等官及校对清文者”,馆臣提交了一份详细名单,共177员,纪昀自不在其中。其实他才是两阁重校的领头羊,最懂皇上此举是要着重查违碍,态度格外认真,出力也最多。
老纪是明白人,不光对获赏没抱希望,还早早就表示认罚,甚至提出自罚。所提在两阁重校后再看一遍的建议,应该没被采纳和实施,四库纂校一向绷紧这根弦,留下的政治问题极少,详校官也都唯此为大,细细过筛子,已无必要由纪昀个人再看。而弘历看了两阁呈上的错讹清单,即命做统计,很快查明犯错的人员和错误数,决定由纪昀带领前往承德重校文津阁本。
御史莫瞻菉再次上言,说这批重校人员名单中有些已经升职,有的即将升职,实在不妥,奏请将所有出错纂校中拟升者概行注销,已升之员分别酌罚廉俸。弘历阅后即行传谕:
从前办理四库全书时,朕因卷帙浩繁,编纂不易,原曾谕于敏中“凡兴作大事,不能不徼幸数人”。但朕此旨原指纂修详核雠校无讹而言,是以不靳恩施,优加录叙。今文渊等阁所贮四库全书,偶经披阅,草率讹谬,比比皆是,因令诸皇子及在廷诸臣复加详校,签出错误之处累牍连篇,不可枚举。是办理此书并不实心校阅,竟以稽古右文之举为若辈邀恩牟利之快捷方式,大负朕意。此事发端于于敏中,承办于陆费墀,其条款章程俱系伊二人酌定。今所缮书籍荒谬至此,使于敏中尚在,必当重治其罪,因伊业经身故,是以从宽,止撤出贤良祠,不复追论,保全终始。陆费墀现已革职,亦不深究。所有业经议叙纂校各员,其已经升用应行议罚廉俸,及未经升用将议叙注销之处,着该部核议具奏。(《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二五五)
于敏中曾是弘历兴办四库最得力的助手,此次再被谴责;陆费墀则是助手的助手,命运更为悲摧。莫瞻菉作为资深四库纂修,对这些不会不知道,却也是揣摩皇上的心思,措辞严苛细密,两次上奏皆引起皇上的肯定,虽不免受到同僚腹诽,也迎来了一段仕途上的小高潮。
根据弘历的旨意,和珅很快查明所有出错人员的情形,提请分类予以处罚:
在各省担任学政者,有刘权之、翁方纲、郑际唐、潘曾起、张焘、关槐6人,待任满后,由陆锡熊带领前赴盛京罚校文溯阁本;
现任道府及同知、知州、通判等官者,有季学锦、王家宾等13人,“每错误一处,各罚本任养廉半年”;丁忧告假回籍者,有吴舒帷、张九镡、张培等19人,“于补官之日,每错误一次,京官罚俸一年,外官罚养廉半年”;范鏊出错两处,现出差,“罚俸二年”。清单中详细开列了每人的出错数,多为一二处,三处者较少,却也有一位缪琪竟然有12处。缪琪,江阴人,为乾隆四十年(1775)二甲进士,一个很不错的诗人,曾在缮书处参与黄签考证,不知为何错得如此离谱?
至于那些降革、休致、病故人员,有旨一律“免议”。
和珅拟出一份罚往热河的出错在京纂校名单,命其“同纪昀校勘文津阁书籍”,共有王燕绪、何思钧、仓圣脉、潘有为等34员。清单中没有个人的错误数,应是已罚校改,就不再罚银了。颇为有趣的是,最后一名为莫瞻菉。
十月十五日上奏时,瞻菉声称看到“派往热河看书之原校错谬诸员”的清单,请求从严,应知原来的名单上没有他。为此,该奏所附清单上特别注明:“莫瞻菉系原纂官,《松阳讲义》引吕留良语,未经删削,应罚令同校对错误各员前赴热河看书。”(《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二五六)吕留良为清初杰出思想家,拒斥新朝,雍正间被发棺锉尸,引录他的话,当然要受处罚。
嘿嘿,谁举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