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居伦敦:流动的社区和另类人生

2020年,电影《无依之地》将当代美国房车族的生活搬上了银幕。出于经济困境或是离经叛道的自主选择,这些美国人放弃追求稳定的住房和工作,开上房车,选择了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游牧人生。广阔的自由、刻骨的孤独伴随着维持生计的艰辛,打动了无数观众。
如果说《无依之地》映射出美国广阔平原上的游牧文化以及当代中西部铁锈带的社会现实,那么在大西洋另一端,英国的船居者则体现着这个国家的河运文化,以及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
在船上漂流的人类学者
在英国纵横交错的内陆河道上,正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陆地上的固定住房,选择过一种依河而生的船居生活。2021年的数据统计,有将近9000英国人将船作为自己的住所。英国人类学家本杰明·O.L. 布罗泽(Benjamin O.L. Bowles)就曾是其中一位。
布罗泽18岁时,坐着朋友的船在英国内陆运河上旅行两个星期,那是他第一次接触船居生活。那两个星期“不能洗澡,没有手机,没有Facebook,最后都屈从于水道的节奏”。从此,布罗泽对这种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将船居者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题目。2012年,他加入船居者群体,花2万英镑买了一艘11米长的“窄船”(narrowboat,一种专为从前英国狭窄河道设计制造的渡船)。之后的6年里,他都住在这艘船上,在伦敦和英国东南部的各条河道上漂流、生活,同时展开自己的田野调查。在2024年,布罗泽的著作《伦敦的船居者——水道上的另类生活》(Boaters of London:Alternative Living on Water)出版。

在沉浸式田野调查中,布罗泽深度采访了18位船居者,以及运河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他发现这些船主选择这一生活方式的原因五花八门。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降低在伦敦生活成本的途径,他们可以逃避房租或房贷,辞去不喜欢的工作,而在船上经营小生意;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与大自然重新建立联系的方式;对另一些人来说,能够一直旅行而不被“困”在一个地方非常重要,他们渴望脱离网格化的生活秩序,但同时能与想法相似的其他人建立联系。布罗泽提到,在他的调查笔记中,他用各种颜色的贴纸标记不同关键词的位置,最后发现,标注“社区(community)”一词的贴纸很快就用光了。几乎所有受访者,或积极或悲观,或富裕或贫困,都会提到关于“社区”的体验和思考。因此,“社区”成了布罗泽在这项研究中的焦点。除了身体力行的观察与访谈,他查阅历史档案,梳理相关文献,借助福柯的“异托邦(heterotopia)”理论、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政治学理论,以及杰拉德·德兰蒂(Gerard Delanty)的社区理论,对船居者们进行了富有洞见的分析与阐释。通过呈现这一群体的故事,布罗泽希望为读者提供一种视角去理解当代伦敦以及世界其他大城市的社会生活、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边缘流动人口的生存与创造。
一种超越空间限制的后现代社区
英国内河航运兴起于18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来临,政府修建运河,将煤炭和其他矿产运往各地的工厂。船运因安全性和载货量繁荣一时。然而,随着公路和铁路的不断发展,河运被逐步替代,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衰落。1946年,英国民间成立内河航道协会,主张修复被破坏的运河,作为传统英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他们的努力下,河道被修复,并主要用于休闲观光。20世纪80年代,全球新自由主义兴起,英国社会福利减少,房价飙升,越来越多城市贫困人口无法支付日渐高昂的生活费用。或是寻找替代方案,于是一些人开始回到运河上,过起了船居生活。

当布罗泽第一次踏上他的窄船时,对各种机械设备和改造工程一无所知。附近热心的船居老手纷纷前来帮他修整。一个名叫Tim的邻居,帮他安装完第一节灯管后,很不客气地让布罗泽上来跟着自己学习这项技能。后来作者发现了这一群体的等级秩序。拥有熟练技能是一种地位,甚至是一种内在的文化资本,而那些不熟练的新手往往会处于一种边缘地位参与并学习。这些共同的任务和目标导致了内部社会结构的形成,这一结构推崇特定的价值观和做事方式。船居者们围绕这些共同任务和目标(比如提升技能)形成身份认同,进而形成“实践共同体”。

船居生活每年的开支主要包括船只的牌照费、停泊费、保险费、柴油、发电机用的汽油、煤气罐及生活垃圾处理费。就布罗泽自己的船来说,每年支出约1400英镑,“在伦敦只相当于一个月的房租”。因此水上生活对于许多低收入群体充满诱惑。然而,这种生活并非毫无经济风险。船只会出现故障,需要维修保养。河道管理局规定,船只在同一停泊点不能超过两个星期,否则就会被吊销执照,船只则被扣押。有些船居者因此失去了自己的船,最终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船居者维持生计的方式多种多样。因为城市河道的停泊费昂贵,所以极少人有岸上的固定工作。他们或者做水上贸易,比如将自己的船同时用作二手书店、酒吧、药店,甚至还有人开展占星塔罗业务,或者做船舶本身的生意,买卖二手船,帮其他人维修改造船只等。布罗泽认为,在维持生计方面,船居者体现出新自由主义背景下“零工经济”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存策略。
作者指出,在英国更广泛的语境中,“社区”一词,要么大致等同于“地区”或“邻里”,要么是指某个特定族裔群体。然而,在水道上,“社区”是一个动词。它意味着你要亲手实践,而且必须和其他人一起实践。在水道的背景下,社区不再是一个稳固的地理空间,而是一种脆弱的沟通纽带。互助是维持这一纽带的关键。船民们在应对水道生活所带来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挑战时,必须通过明确的修辞和表演努力构建和强化互助的价值观。如此一来,船居者的河域空间便成了一个基于行动和依赖的社区场所。这种地理上的流动和价值上的稳固,体现了德兰蒂的“流动(flux)”的概念——一种超越空间限制的后现代社区。正如一位船居者所言,对他来说,“‘社区’就是帮助明天会遇上的其他船居者劈柴。”

异托邦(heterotopia):
异托邦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1967年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可以粗略理解为“他者空间”,指的是那些真实存在且得到制度认可的空间,它们打破了常规的空间规范,同时映射、颠倒或质疑文化中的其他空间。在本书中,布罗泽通过异托邦的概念强调船居者社区的边缘属性:他们脱离社会主流的空间,从边缘的位置以多种方式来探索和试验自己的身份。
政府与船居者的关系并非仅是统治与被统治那么简单。船民将自己的船只暴露在政府的监视之下,同时也是寻求庇护的一种方式。这一监视与合作的辩证关系,来自船民与岸上居民的对立。有些岸上居民对于船居者充满好奇。船居者时常受到人们的围观、拍照,甚至有人未经邀请就上船参观。他们将船民社区看作一种怀旧性表演、一种区别性独特情调。另一类岸上居民则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尤其是偷盗者。为此船居者们自发组织起来,发放口哨,在危机时刻呼叫彼此,形成一种相互守卫的网络。
在全球加速的今天,伦敦的船居者们进行了一次“减速”的尝试。他们从不断加快的城市节奏中,退回到缓慢流动的河道。介于城市与乡村、自然与人工、永恒与短暂之间,船居社区深受水域空间的流动性和过渡性塑造。作为一个“另类”群体,他们既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又是其抵抗者。这一流动的社区在大城市中打造出边缘空间,在当代英国紧缩政策和住房危机的历史背景下,正孕育出新的可能。
(责编:刘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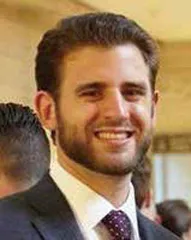
全书8个章节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梳理了英国河运兴衰史。第二部分包含第二到第四章,呈现了船居者的生活经历,以及船居者必须掌握的各种技能、水上社区的守则和礼仪等。第五章既是过渡也是全书的理论核心——在这一章中,作者探究了“社区”这一概念的起源和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流动社区的定义。第三部分为第六章到第八章,作者将关注点扩展至更为广泛的社会与政治议题,通过船居者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呈现了这一群体如何受到国家机构的政治干预、所遭受的安全威胁,以及船居者如何组织起来应对这些干预和威胁。从个体船居者到社区再到整个国家,布罗泽希望展示这样一种事实——船居生活并非浪漫想象中的遗世独立,而是置身于整个英国社会,甚至世界潮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