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与以色列矛盾升级的根源
作者: 田文林
2025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全面冲突,并由此引发世界各国高度关注。伊朗与以色列并非天生就是对手,双方矛盾日趋升温,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意识形态根源:伊朗革命型外交导致伊以关系恶化
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伊朗的巴列维王朝是个生存型政权,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巩固和增加自身利益。由此出发,伊朗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待与以色列关系,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然而,巴列维王朝垮台后,取而代之的伊斯兰政权是个典型的革命型政权,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就是颠覆现行秩序。伊朗将世界分为相互对立的“强者与弱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并以被压迫者和挑战者自居。霍梅尼曾呼吁,“全世界的逆来顺受者啊,奋起吧,把你们自己从恶毒的压迫者的魔爪下拯救出来吧。全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啊,从你们那无所顾忌的沉睡中苏醒吧,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从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吧”。1979年伊斯兰革命不仅是反抗君主制,也是反对美国及其在中东的代理人。由于不认可现行国际秩序,伊朗屡屡做出挑战现行秩序的惊人之举:1979年公开占领美国驻伊使馆,劫持人质444天,1983年参与制造美国驻贝鲁特兵营爆炸,1989年判处侮辱先知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等。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概括了伊朗的革命性国际秩序观:现代国际关系以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为基础,该原则的基础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国家间关系应以宗教为基础”,而不是遵循国家利益的原则;20世纪的中东版图是“帝国主义”的错误产物,“专制利己统治者”人为地将伊斯兰社会分裂、创造出独立国家;中东及其他地区,所有当代政治制度都是非法的,因其“没有建立在神法基础上”;伊朗从未将国家视为合法实体,而是将其当作工具,以开展更广泛的宗教斗争;认同库特卜描绘的“伊斯兰将重建秩序并最终主宰世界的图景”,所有穆斯林将组建一个国家;伊朗有责任为所有穆斯林的团结和友善制定总体规划,引领伊斯兰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团结。
否认以色列存在合法性,则是伊朗树立中东秩序革命者形象的重要抓手。伊朗是波斯/什叶派国家,并实行教士治国,在中东属于少数派。同时,伊朗谋求变革现行国际和地区秩序,但自身势单力孤,无力与美国及其中东盟友公开对抗。为变被动为主动,伊朗特别注重抢占道义、法理、舆论制高点,设法动员和团结整个伊斯兰世界民众。而反对以色列、维护巴勒斯坦正当权益,无疑是伊朗最能激发穆斯林世界同仇敌忾的政治口号。

在霍梅尼的《伊斯兰政府》一书中,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其理论核心之一。霍梅尼认为,正是由于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妥协与勾结,才诞生了以色列这个给伊斯兰世界带来问题的国家。霍梅尼相信,伊朗是全球穆斯林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而以色列处在伊斯兰世界心脏地带,是建立穆斯林共同体的主要障碍。伊朗主要任务就是“解放耶路撒冷”,“历史性地战胜犹太复国主义”。在推翻巴列维的革命过程中,霍梅尼将美、以、巴列维称为三个“大撒旦”,认为巴列维王朝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以色列则是巴列维及其反动专制王朝的帮凶,是美帝国主义在中东的代理人。在这种语境下,伊朗公开将以色列定位为“伊斯兰的敌人”,并在建国后宣布不再承认以色列,切断与以色列的一切官方联系。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继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继续坚定反以,将以色列视为“伊斯兰世界心脏地带的肿瘤”。在巴列维时期,哈梅内伊曾受到伊朗情报机构萨瓦克的残酷折磨,而该组织正是受训于美国中情局和以色列摩萨德,因此对美国和以色列恨之入骨。他谴责以色列“通过杀婴、嗜杀、暴力和铁拳等手段”实现自身目标,认为阻止“以色列犯罪”的惟一办法就是消灭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这种政治话语下,伊朗与以色列关系近乎打成死结。
地缘政治根源:伊朗与以色列的地缘目标日趋冲突
伊朗素有大国之志。历史上波斯帝国的辉煌历史,激发起伊朗人“再创辉煌”的信念和奋斗目标。伊朗人深信,他们的国家将会重新确立为地区大国。早在巴列维时期,伊朗就以“海湾宪兵”自居。巴列维还自视为居鲁士衣钵传人,并在1976年修改历法,废除伊斯兰教历,以居鲁士缔造波斯帝国为元年,试图建立“第三波斯帝国”。其多次表示:“我要将伊朗建设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的世界第五强国,同时我们的军队也将发展壮大成世界第五大军事力量。”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转而通过“输出革命”重塑地区秩序,借以实现大国目标。
伊朗革命领导人霍梅尼自称“伊斯兰世界和受压迫人民的领袖”,暗示它将跨越疆界,推动伊斯兰世界的联合。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其官方网站直言,他更愿意“作为穆斯林世界的最高领袖,而不是伊朗最高领袖”。
从现实政治看,伊朗近几十年地缘环境日趋改善。1991苏联解体帮助伊朗消除了北部最大威胁,同时中亚出现的数个穆斯林国家,如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为伊朗北部安全提供“缓冲带”。美国2001年和2003年分别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帮助伊朗清除了两大夙敌,同时,伊拉克什叶派上台使中东隐然形成“什叶派新月地带”。2011年中东剧变后,阿拉伯世界整体衰落,伊朗“相对崛起”态势明显:2014年“伊斯兰国”兴起,使伊朗由“防扩散”中的防范重点,变成“反恐”议题中的合作对象;2015年7月美伊达成核协议,使伊朗长期被压制的潜力得以释放;伊朗在叙利亚危机中帮助巴沙尔政权稳住阵脚,使地区力量对比向有利于伊朗方向发展。
伊朗从“地缘支轴国家”演变为“地缘战略棋手”,使其地区大国意识更加强烈。从实践看,伊朗借阿拉伯世界动荡之际,加紧地区扩张步伐。在叙利亚,伊朗力挺巴沙尔政权。据伊朗外交官估算,伊朗在叙利亚至少投入300亿美元军事和经济援助。有学者称,伊朗每年向叙利亚投入就达150亿美元,总额达1050亿美元。在伊拉克,伊朗借反恐为名,资助什叶派民兵“人民动员力量”,并派出革命卫队圣城旅参战,在伊拉克军事存在大增。在也门,伊朗积极扶植什叶派背景的胡塞武装。在黎巴嫩,伊朗大力扶植真主党。在巴勒斯坦,伊朗加紧支持巴勒斯坦激进派哈马斯。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伊朗创造出一个从伊朗到伊拉克、再从叙利亚到黎巴嫩,直通地中海的“什叶派新月带”。
在以色列看来,伊朗谋求成为地区霸主,直接威胁以色列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安全。以色列长期生活在阿拉伯世界敌对包围中,一直渴望改变不利局面,其战略选择有二:一种办法是“土地换和平”,实现巴以和平相处;另一种办法是促使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巴尔干化”,使其无力反抗以色列。种种迹象表明,以色列日趋放弃“土地换和平”战略,通过搅乱阿拉伯世界,增加以色列的安全感。在以色列看来,伊朗在中东建立“抵抗走廊”的战略目标,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对其构成巨大威胁:军事上,伊朗将更方便向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在叙军事基地运送足以“改变游戏”的武装装备,威胁以色列安全;政治上,这将妨碍以色列与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建立反伊联盟。伊朗的地区扩张政策令以色列寝食难安。

叙利亚危机是伊以矛盾激化的导火索,也是两国博弈的战场。伊朗从维护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大力支持巴沙尔政府。而以色列则认为,推翻巴沙尔政权可以打破伊朗“抵抗链条的金环(哈梅内伊语)”,割断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的地理纽带,打破对以色列的包围。伊朗及其代理人在叙利亚扩大军事存在,令以色列寝食难安。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多次强调,不能容忍伊朗把叙利亚变成对抗以色列的前沿阵地,伊朗必须从叙利亚全境撤军,并宣称将采取行动打击伊朗在叙利亚“任何地方”的军事存在。以国防部长利伯曼警告说:“我们不会允许在叙利亚形成一个什叶派轴心,这有可能被作为威胁以色列安全的活动的基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频频打击叙境内的伊朗军事目标,两国由此到了爆发全面战争的边缘。
以色列与伊朗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中东基本上处在政治秩序碎片化的状态。在国际体系中,安全问题(即生存问题)始终是国家的首要考虑。对伊朗与以色列这对死敌来说,“安全两难”(一国加强军备引发另一国恐慌,并相应增加军备)问题尤为突出。伊朗自1979年以来一直被美国视为敌对国家,并至今仍遭受美国制裁,美国还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和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屡屡扬言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在此背景下,伊朗不安全感强烈,高度重视提升军力水平。从1992年开始,伊朗实施武器国产化计划,目前已建立起伊斯兰世界最全面的军工体系,能够生产新型主战坦克、导弹快艇、常规火炮、轻型舰艇、小型潜艇、战斗机,并能够生产近、中、远程和洲际导弹,具备自主发射卫星能力。尤其在导弹研发领域,伊朗已经拥有流星、胜利者、泥石、波斯湾等多种型号的导弹。
近年来,伊朗还大力提升核能力。伊朗核研发始于巴列维时期。到1979年巴列维王朝倒台前,伊朗已签署建立4座核反应堆,其中布什尔核电站已经完成80%。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暂停了全部核研发活动。从20世纪90年代,伊朗重启核活动,2003年伊核计划曝光后,伊朗不顾西方阻拦,最终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核循环体系。伊朗执意发展核能力,一是“拥核自保”。伊朗认定,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抵御美国对伊朗的核讹诈和武力威胁。二是拥核自强。伊朗高层将“拥核”看作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伊斯兰政权凝聚力,以及确立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的必由之路,将掌握核能力视为提升自豪感、挤入大国行列的“通行证”。伊朗前总统哈塔米表示:“我们想变得强大,强大就意味着拥有先进的技术,而核技术则是所有技术中最先进的。”哈梅内伊称核工程是伊朗的“必需品”。
然而,伊朗矢志提升军力水平,特别是提升核能力,与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的军事战略尖锐对立。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当前其实际控制范围仅22072平方千米。同时,以色列地形狭长,缺乏战略纵深,在现代战争中稍有不慎,就可能被灭国。这种严峻现实促使以色列形成了追求“绝对安全”的战略文化。为确保自身安全,以色列必须确保绝对军事优势,绝不允许其他中东国家军力水平达到乃至赶超以色列。为此,以色列宁愿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也不愿坐等事发后进行危机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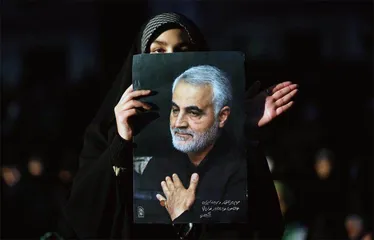
以色列尤其不容任何地区国家挑战其核垄断地位。以色列长期奉行“核模糊政策”,其拥有核武器是公开的秘密。有消息称,以色列至少拥有两百枚核弹头。为确保核垄断优势,以色列绝不允许中东其他国家发展核能力。20世纪80年代,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称:“我们的决心是,防止敌对国家获得核武器。对以色列来说,这不是恐怖平衡问题,而是生存问题。”1981年6月7日,以色列出动空军,摧毁了伊拉克即将建成的奥西拉克(Osirak)核反应堆。这是世界上首例通过先发制人打击,摧毁对手核能力的案例。以色列领导人将空袭伊拉克核反应堆视为“自卫”行动,声称不能允许以色列民众冒另一次“大屠杀”的风险。